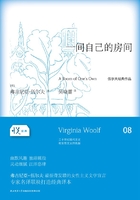身坐在狭小的废弃教室,被包围在胡乱堆砌的桌椅之中,你不禁觉得这里就像个监狱。教室里除了我和老哥之外就只有那些盖满灰尘的单人桌椅了。我想起了古代科举时赶考的秀才待的那种单人间。
从进门到现在,我唯一做的就是盯着站在讲台上的他。他弓着身子,桌上的宣纸泛着古旧的银白的光。他动笔随意写着,我就坐在他面前最近的那张桌子,看着他。他丝毫没有跟我提起关于书法社题字的事。
古代的富家公子经常在考室里偷吃烤鸡。通常这些东西都是考官呈给他们的,还有写着答案的卷子。
看着毛笔尖在纸上划过的痕迹,那飘逸的风格和悠然的动作让我心情平静了下来,感到满足和兴奋。
“你想写什么?”我问。
“随便写。”他说。
眼前这个高二学生看起来对门外的事毫不关心。
他写道“随便写”,然后把那张宣纸揉成一团扔掉。
他写道“随心所欲”,然后把那张宣纸揉成一团扔掉。
他写道“欲”。完了心满意足地看着这个字,右边嘴角露出满意的微笑。
我写“想”。然后把那张宣纸揉成一团扔掉。
从两个多小时前的铃声响起开始算的话,现在差不多考试就要结束了。最近期末,高年级们的都准备得有些手忙脚乱。“叮”一声然后广播响了起来,“离考试结束还有15分钟。”接着是没有关掉麦克风的嘈杂电波声持续了大概5秒。
我才想起来现在是高二年级的语文期末考试。
老哥他就读高二,现在。
“等等?你没去考试?”我好奇地问他。
“是的。”他像平常在家里写字那样平静,“我正在准备留级。”
“等等。老兄,你的意思是……”在我把话说出来之前,我就已经知道大概的情况了。要是他这么说了,那他一定就是在为留级做准备了。
我不能说一句废话或者问一个蠢问题,在任何时候,不然我就不是他眼中的好士兵了。
然后我就说了:“收到。”
我开始发觉原来自己有时候根本不需要说话。
站在E字楼的废弃教室里我开始跟着他悠然地笔走龙蛇。
落第。我写道。
“你怎么做的?”我要“简明扼要”地了解情况。
“我移交了班务,跟班主任提出了申请,第三项我正在实施。”他看着他那正在推划的手说道。
“意义?”
“这只是在我的成就和成绩之间找个平衡。”
左右,他写道,然后把那张宣纸揉成了一团扔掉。
“你什么时候开始需要成绩了?”
“我不需要,我的班主任需要我需要,但我想避免一些麻烦。”
定。他落下秋毫,悄无声息。完了满意地看着这张作品。用双手轻轻地拿起,
放到一旁,抚平,卷起,藏到那张讲桌下的柜子里。
我写了一个亡字头然后把那张宣纸揉成一团扔掉。我心烦意乱地故作镇定,就像我班上那些女生来了月经。
他面无表情,纹丝不动,龙飞凤舞。就像第一高级中学二年级上学期的语文期末考试与他毫不相关,就像他说的那样。他从不知哪里扯出来一张大宣纸,五六尺宽,跟文具店里从来都摆着的那些未经过裁切的差不多。我知道一般那些大家都用这来做大手笔,誊写《兰亭序》、《滕王阁序》、《隆中对》之类的或者题几个大字。
洋洋洒洒,行文壮阔,针砭时弊。然后把它裱起来或者匾起来,挂于厅堂。
这非常古典。
在这间第三世界的四线城市的二环路外的三流学校的闲置教室里的讲台上,这位超脱先生行云流水地写下一行草书——“世外桃源”。
瞧那一点。行话叫苍劲。
他今天就是叫我来见证他为自己的书法社题字的。我的年级正在进行期末复习,老师很少在教室里监督,所以我就偷偷跑过来了。然后他说他准备裱起这张书法社题字,再将它堂而皇之地挂在面向东边的那道墙上。
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汲取历史教训。所以在学校里无论你想做什么你都需要请示,从上到下,或者是从下到上依次批准。二字以蔽,就是繁琐。
如果想在自己学校创立一个书法社,那必须先得获得校长的允许。只要他不准,你做再多的准备都是白搭,而只要他允许,那一切就都好说了。从老哥第一次找校长商量失败过后,他的长征就开始了。校长先生很忙,你在学校里经常是见不到校长先生的。所以老哥得抓住这样稍纵即逝的机会。
“这没什么技术含量,你就一边找他商量,一边做好书法社的准备工作就行了。”他说。在他与校长的第134次会面上,校长终于提出了条件。他就是这么让不准变为允许的。除去假期,再除去校长的假期,从老哥的整个高一到高二上期的现在,12个半月的岁月就这么被挥霍一空。这是一段漫长而无聊却又富有历史意义的时期。
按照程序,他交上去了创建书法社所需的文件后又等待了两周校长才给他批复。校长先生很忙。不过老哥有的是耐心。
“你得抓住机会,不然就算是校长,”他写了个“逃”字不紧不慢地说,“也会跑掉。”
“嗯。”
“你这一年多就用来跟他拔河?”我问。
“我本来想的是如果有必要,那这三年就这样耗这儿了也无所谓。”他说。
“你不是最恨浪费时间的吗?”我问。
“恒心和浪费没有关系,老弟。”他说着,走到了窗子边上,“我有为自己斗争的义务。”
他在窗边看着学校侧门外寂静的街道。我听到他使劲闻着手的声音。
正觉得奇怪,我就看到了烟雾……
他转过身来,那是一根粗又长的、通体是深深的咖啡色的——“巧克力棒”。
在光照下散发着暗光。
那是根雪茄。
“我想起了徐志摩。”他说。
他靠在窗边,我看着他在午阳下的前影。他发出两道急促的吹吸声,然后是缥缈的烟雾。在学校,有些地方仿佛不存在校规。
他咳了两声,然后说:“这玩意真难抽。”
这是他第一次抽雪茄。为此他还特地在网上做了预习。但这不是重点。我找不到容忍他吸烟的理由。
“这是老早之前从我们爹的抽屉里找出来的。”他随口又补充道,看着外边儿。于是我就没有多说了。
所以这也是我第一次抽烟。因为我爹也这样干过,那这顶多只能算作是遗传吧。
我来了一口,结果被呛得呼吸困难,之后他才建议我不要进肺。我想起了我去年第一次学酒的屌样。才开始你还觉得有害或者是厌恶,但等你接触之后才不一会儿就都无所谓了。完了我在一旁写下了个歪七扭八的“静”。
之后我们慢条斯理地打扫了书法社一遍。把那一堆破铜烂铁般的旧桌椅一个挤一个地摆放到教室的后面,废纸一堆裹一堆地扔进垃圾桶,讲桌摆正,笔墨纸砚收拾规整。这些一卷一卷被整齐而小心地堆在讲桌的柜子里的我看不上眼的书法作品一再地提醒我这就是我老哥整个高中生涯的三分之一。我不禁觉得任何人的一生都可能因为一些小瑕疵而变成一坨狗屎。不论他们之前是多么的伟大。
所谓风险。
叮咚一声铃响,广播里传来一句用标准普通话说的“考试结束”。
他看起来还想再写一会儿字,丝毫没有要去教室集合的意思。我猜他又一次不声不响地违反了班主任的指令。书法社,他的书法社,毕竟这更重要。
他从来不舍本逐末。他自己说的。
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静”字。歪七扭八的,也许那就是我的心。
从那间废弃教室回去之后,我发现了班主任和无数同学的眼神正在教室里等着我。结果我没能从我的隐蔽行动中全身而退。在期末期间,年级上的班主任们都会去监考,所以在每场考试结束之后的15分钟之内,我的班主任有50%的几率不会来巡查。不过这次我的班主任他碰巧处在了另一半。
班主任对我提出严正交涉。在办公室里我被年级上的各位班主任注视,我感觉自己像是被批斗了一样。
对于这次行动,我发出声明由我自己负责。
但他说“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娃儿,能为自己负什么责?”
设问句。我不能回答。我低着头,两眼下视黄泉。很明显我的班主任是看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现在我百口莫辩。教师办公室里充满着快活的空气,这些是我们年级上著名的四大金刚。由他们的组成的初三年级教育体系一直有板有眼。虽然我毛还没长齐,但我也不能跟他争辩,老师在服从他的道理。虽然我也有我的道理,但老师他是不会听的。然后是强烈谴责。前面的我忘了,我只记得他最后说“死猪不怕开水烫”。中午我跟老哥在学校外面的餐馆吃完午饭之后就又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教室,开始准备迎接又一个下午的开始。在两点半之前,我会把抽屉里的马克杯拿出来,泡一杯我们这里的土产雀舌,等待上课铃。这种没什么名气、一克两三毛钱、两三克就能泡一杯的茶已经算得上我们这地方的上品。虽然严格上来说它也只是下品茶,叶散而乱、味浓意淡,回甘不力。我的意思是,其实这是下品茶中的上品茶,因为它实惠。在考试之前的复习期间,我就一边喝茶一边做卷子。把这几颗茶叶冲泡十多遍,直到它们变得索然无味,再做两三套卷子,一下午就过去了。这就是按部就班的效率。完成任务的我无事可做,每天到了这个时候我就开始盼自己年级的最后一道下课铃,就像自己只为这个在过日子一样。大家也乐在其中,打铃之前他们还如同三脚病驴,铃一响就有一半跑成了种马。
放学之后我会拿着杯子去洗手间那边准备洗干净,顺便撒泡尿。在你累得不行的时候你就不想跟一个又一个与你擦肩而过的人打招呼了。大家都是,要是同学们在厕所里遇上了,我们就只互相低着头看一眼对方的小弟弟,然后点个头以示问候。
等我回到教室,没事干的同学们都已经走光了,最多剩下几个打扫卫生的值日生。由于我要等老哥,所以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离开,负责锁门。到第四节下课铃打响了,我就会在教室门口等他,他们高二的下午要比我们初三的多一节课。平常十五分钟之内他就会过来,然后我们一起回家。要是平常,他就已经到了。
我稍息站在教室的门口,看了看手中的儿童电子表。这是块五块钱都值不到、只能显示当前时间的表。这是在很早之前小学里的一堆准备捐献给希望工程的废品中找到的。我已经等了他8分钟,虽然在15分钟之内我们都约定俗成为守时,但换做是今天之前任何一天的他现在都应该已经到了。
有些不对,我感觉到。某种时候,他应该在哪个角落伸出皮鞋,然后是他的黑色袖口,他的整个人就从前面楼道的拐弯处钻出来了。那种由即视感构成的碎片能够拼出来他接下来的一整套动作。本来他应该已经出现了,但是现在没有。最后我才反应过来早上他在书法社那里随口一提从今往后我们就改在校门口集合了。
我一时间没习惯过来,只觉得自己怪怪的。一瞬之间,我保持了两年多的初中习惯就被取缔了,等我回过神来,才意识到自己从前的日子就这么过去了,突然觉得这毫无知觉的五个学期真是一场令人愉悦的浪费。穷人就只有过去。
去年的时候,老哥说初中一毕业他就已经把学到的一半东西给忘了。而他的高中化学老师在第一堂课上就讲清楚了:你们初中所学的可以与现在无关,你照样可以重新开始。后来他发现语文老师也这么说,物理也是,生物也是;政治、地理、音乐都是。我还以为他真的信了。他说他只是受到了启发。那时作为一名初二学生的我便开始怀疑自己这三年来是不是跟他说的一样什么都学不到。我说真是可悲。
他说可鸡巴悲,大浪淘沙。于是我开始注意自己无意间的每一句废话。
于是那时刚进高中不久的老哥对高中学业的要求一下子就降到了只要毕业就行。
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一场考试里有许多偷分技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学会取舍,老师们教过我们这种分数权衡。比这更重要的是能力,因为取舍依附在能力之上,有的题质量就摆在那里,如果你没那能力,你就连选择取舍的资格都没有。
但对于老哥来说,比这还更重要的是就业形势,他说他所做的一切其实只是为了高中一毕业就能找到一份月薪两千的工作。但要想找个工作,首先他得成年,在学校里还可以顺便多拿一张毕业证书。
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打算把时间花在操心分数上面。所以在学校里他一天无所事事又身居晏如。在他高中的第一个学期的某个周一我偶然地跟他在办公楼里相遇了。当时他刚从校长办公室里出来,我看着他若无其事的扑克脸,开始想他是不是又有任务要交给我。反正他才刚进高中的时候就因为校服的事差点去跟校长拼个鱼死网破。那时候他叫我做好扮演记者的准备,B级安排。一空二荡的楼道上就剩下了我们两个,其他同学正赶往操场准备做广播体操。他跟我笑笑,腾不出手来的我只有跟他眨了个眼然后吹了个口哨当做招呼。那是我第一次在那里撞见老哥。我问他,他说他才从校长办公室出来。我看他没有使唤我的意思,于是就叫他帮我把本子抱到三楼的数学办公室去,我再折转去抱另外一摞。
我是体育委员。班级的苦力,人民的公仆。整个班上由我负责把作业押运到办公室去。每天早上第一节课前,大家拼死忙活地把作业交到我这里,第一节课后我把它们整理好,第二节课后开始把这些搬到办公室去,这些时间我都会精确到分钟。
我从来没有因为那些没完成作业的同学耽搁过,所以在班上大家都比较不喜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