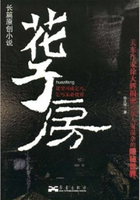马修·卡思伯特驾着马车不慌不忙地向布赖特河驶去,路程约为八英里。这是一条风景秀丽的道路,行进在密集的农庄间,时而穿过一片香脂杉树林,时而越过一个山谷,山谷中的野李子树上挂着朵朵轻薄透明的花苞。大片的苹果园和绿地向远方延伸,消失在地平线附近的珠灰及紫色的薄雾中,空气由于它们散发出的芬芳气息而变得香甜起来;而
“小鸟在歌唱仿佛这是
一年中夏季里的一天。”
这样的驾车旅行与马修的风格一致,他一路很愉快,除了在途中会遇到女人并不得不向她们打招呼的那些时刻——在爱德华岛你必须向在路上遇到的每个人打招呼,不管你是否认识他们。
马修惧怕所有的女人,除了马瑞拉和雷切尔太太;他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总觉得这些神秘、不可思议的女人在偷偷地嘲笑他。他这样想也许是对的,因为他是一个长相古怪的人,有着笨拙难看的体形,铁灰色长发垂至佝偻的肩部,从二十岁就开始蓄起柔软的棕色大胡子。实际上,他二十岁时看上去就已经和六十岁非常相像,只不过少了一些灰色。
当他到达布赖特河的时候,那里没有任何火车的踪影;他想自己来得太早了,所以先把马车拴在布赖特站小旅馆的院子里,然后径直向车站休息室走去。长长的站台上空荡荡的;唯一看得见的人,是一个坐在站台尽头一堆鹅卵石上的女孩。马修刚发现那是一个女孩,便立刻迅速地、瞧也没瞧地侧身从她身边走开。如果他看一眼的话,就一定会注意到她紧张僵硬却充满期待的姿态和神情。她坐在那儿,等着什么,而她那时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坐在那里等待,所以她竭尽全力地坐着,等待着。
马修遇到了正在锁售票处的门、准备回家吃晚饭的站长,便问他五点半的火车是否快进站了。
“五点半的火车已经进站,半小时前就开走了,”站长轻快地答道,“但是有一个旅客被留了下来交给你——一个小女孩。她正坐在外面的鹅卵石上。我让她去女士候车室,但是她很认真地告诉我她更愿意待在外面。她说:‘那儿有更多想象的空间。’我得说,她是怪女孩。”
“我要接的不是一个女孩。”马修一脸茫然地说,“我到这儿是来接一个男孩的。他应该在这儿。亚力山大·斯潘塞太太会从新斯科舍省把他带过来给我。”
站长吹了声口哨。
“我猜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他说,“斯潘塞太太和那个女孩一起下的火车,她把女孩交给我,说你和你妹妹从孤儿院收养了她,你很快就会到这里来接她。这是我所知道的一切——我可没在附近藏匿了其他孤儿。”
“我难以理解。”马修茫然不知所措地说道,真希望马瑞拉就在身边,帮他应付这个问题。
“那么,你最好去问那个女孩。”站长心不在焉地说,“我敢说她一定能够解释清楚——她自己有嘴,这点很肯定。也许那儿没有你要的那种类型的男孩了。”
他实在太饿,便急匆匆地跑走了,留下了不幸的马修来做这件对于他来说比在太岁爷头上动土更困难的事——走近一个女孩——一个陌生的女孩——一个无父无母的女孩,而且还要向她询问为什么她不是一个男孩。马修心里暗暗呻吟,转身顺着站台慢吞吞地、轻手轻脚地向她走去。
从马修经过她身边的那刻起,她就一直在看着他,现在她专注地盯着马修。马修没有看她,就算看了,也不会注意到她究竟长得什么样,但是一个普通的观察者也能看到这些:十一岁左右的孩子,穿着一件很短、很紧、很难看的黄灰色棉绒裙,戴着一顶褪色的棕色水手帽,帽子下一直拖到后背的是两条粗粗的红发辫子。她的脸又小、又白、又瘦,布满雀斑;嘴巴很大,眼睛也是;一双眼睛在某些眼神和状态下看上去是绿色的,而在另外一些眼神和状态下又是灰色的。
这是一个普通的观察者所能看到的一切;更加细心的人或许还会注意到她的下巴长得很尖、很凸出,大大的眼睛中充满锐气与活力,可爱恬美的嘴唇极富于表情,前额宽大而饱满。简而言之,有眼力的观察者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害羞的马修·卡思伯特荒唐地害怕着的这一个举目无亲的小女孩,绝不是什么普通的家伙。
然而,马修面临着一个严峻考验——先开口说话,因为当她推定他正向她走来,便立刻站了起来,瘦瘦的、被晒黑了的双手一手握住一只破旧的老式毯制手提包包把,另一只手伸向了他。
“我猜你就是绿山墙的马修·卡思伯特先生吧?”她以一种独特的清晰甜美的声音说,“非常高兴见到你。我正担心你不来接我了,我想象了所有可能发生的导致你不来的事情。我已经决定如果今晚你不来接我的话,我就沿铁轨走到转弯处的那棵大洋樱桃树下,爬上去,钻进树里,今晚就待在那儿。我一点都不会害怕,月光下,睡在一棵开满白花的洋樱桃树中,将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啊。你觉得呢?你可以想象成正躺在一座大理石建成的城堡里,不是吗?而且我确信你早晨一定会来接我,如果你今晚不来的话。”
马修笨手笨脚地握住那只骨瘦如柴的小手;当即他就决定了该怎么做。他不能告诉面前这个忽闪着大眼睛的孩子,这是一个错误;他要把她带回家,让马瑞拉告诉她。不管是发生了怎样的错误,她都不能被丢在布赖特河,因此所有的问题和解释也都会被推迟到他安全返回绿山墙后再进行。
“对不起,我来迟了,”马修羞涩地说,“快跟我来。马就在那边的院子里。把包给我。”
“哦,我能拎,”孩子兴高采烈地答道,“它不重。我的全部家当都装在里面了,但是不重。而且,这包不用一定方法拎的话,包把柄会脱落的——所以最好还是让我来拎,因为我知道里面的诀窍。这是一只非常旧的毯制手提包。哦,我真高兴你来了,虽然睡在一棵洋樱桃树里也很好。我们得走好长一段路,是吗?斯潘塞太太说有八英里。我高兴是因为我喜欢驾车。哦,这简直太美妙了,我就要和你们住在一起,属于你们。我从来没有属于过任何人——没有。但孤儿院是最糟的。我在那里只待了四个月,但已经足够了。我猜你从前不是孤儿院的孤儿,所以你不可能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它比任何你能想象到的事都糟。斯潘塞太太说我这样议论它太刻毒,但我不是有意的。如果不是有意的,很容易变得恶毒,不是吗?他们不错,你知道——孤儿院里的人。但是在孤儿院里几乎没有想象的空间——只能想象一下其他的孤儿。想象一些关于他们的事情非常有趣——假想那个坐在你旁边的女孩可能真的就是一位披着绶带的伯爵的女儿,在还是婴儿的时候,被一个残忍的护士从父母身边偷走,而那个护士还没来得及说出真相就离开人世了。我常常晚上醒着躺在那里,想象这些事情,因为我白天没有时间。我猜这就是我为什么长得这么瘦的原因——我太瘦了,是吗?我身上一点肉都没有。我真的喜欢想象自己长得漂漂亮亮、胖乎乎的,胳膊肘浅浅地凹下去。”
正说着,马修的这位同伴停了下来,因为她开始有些喘气,而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已来到了马车前。直到他们离开村庄,开始向陡峭的小山驶去,她都没有再说一个字。路面一部分深深地陷入松软的泥土中,路边的田埂高出他们好几尺,种满开着花的洋樱桃树和修长的白桦。
孩子伸出手,折下一节擦过马车的野李子树枝。
“这真漂亮,不是吗?那棵缀满白花、从田埂上斜垂出的树让你想到了什么?”她问道。
“嗯,我不知道。”马修说。
“哎呀,一位新娘,当然啦——一位戴着美丽面纱的白衣新娘。我从来没有见过新娘,但是我能想象得出她的模样。我不指望自己会成为新娘。我长得这么普通,没有人会愿意娶我的——除非那可能是一个外国传教士。我猜外国传教士也许不太挑剔。但是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能拥有一条白裙子,那是我所能想到的最高的理想。我真的喜欢漂亮衣服。我这一生还从来没有过一条我能记住的漂亮裙子——但这更加令人向往,不是吗?我会想象自己穿着华丽的衣裳。今天早晨,我离开孤儿院的时候,感到特别羞愧,因为我不得不穿上这件难看的旧棉绒裙。孤儿院的所有小孩都得穿它,你知道。去年冬天霍普顿的一个商人向孤儿院捐赠了三百码棉绒布。有人说那是因为他卖不掉了,但是我宁可相信那是他大发善心,你觉得呢?我们登上火车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每个人都在盯着我,同情我。然后我就开始想象自己正穿着一条最漂亮的淡蓝色真丝裙——当你想象的时候,可能也会想到其他一些东西——戴着一顶缀满鲜花和弯弯羽毛的大帽子,一块金表,小山羊皮手套和靴子。立刻我就觉得浑身振奋,开始尽情享受我的小岛旅行。在船上我一点都没晕船。斯潘塞太太也没有,虽然她经常晕船。她说她一直在看着我,防止我从船上失足掉到海里,所以根本没时间晕船。她说她从没见过像我这样喜欢到处瞎逛的人。可是如果这能让她不晕船,那我到处逛逛也算件好事,难道不是这样吗?我想看所有那些在船上可以看到的东西,因为不知道我是不是还会再有机会。噢,这儿有更多开花的洋樱桃树!这座小岛简直是开花最多的地方。我已经爱上它了,而且我很高兴将住在这里。我常常听人说爱德华岛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我过去也常想象自己住在这里,但是从来没真的指望能住在这儿。当想象变成现实的时候,太令人愉快了,不是吗?但是那些红色的路显得那么可笑。我们在夏洛特镇上火车后,红色的路开始从眼前掠过。我问斯潘塞太太是什么让它们变得那么红的,她说她不知道,而且请我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再问她任何问题了。她说我肯定已经问了她一千个问题。我也这样想,但是如果你不问的话,怎么能找出答案呢?是什么让这些路变得这么红?”
“嗯,我不知道。”马修说。
“那么,这事以后会找到答案。想到还要给许多事情找出答案,我就激动,难道不是吗?这让我感到活着真好——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世界。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所有问题的答案,那世界就失去了一半的乐趣,不是吗?那样的话就没有想象的空间了,不是吗?我是不是话说得太多?人们常常说我话太多。你是不是希望我别再说话?如果你这样说,我马上就停下来。虽然这很难,但如果我下定决心的话,我能停住。”
马修听得很愉快,这让他自己很吃惊。像绝大多数安静的家伙一样,他喜欢健谈的人。他们自己很愿意说话,也不指望他会接话茬。但是他从没料到会与一个小女孩相处得这么愉快。女人当然很糟糕,但小女孩更糟。他讨厌她们斜着眼、羞怯地从他身边偷偷侧行而过的方式,仿佛如果她们敢说一个字,他会一口吃了她们。那是亚芬里有良好教养的女孩的典型。然而这个满脸雀斑的女孩却不一样,尽管他发现自己反应迟钝的脑子很难跟得上她跳跃的思维过程,但觉得还是很“喜欢她那喋喋不休的谈话”。所以他像平时一样羞涩地说:
“噢,你喜欢说就说吧。我不介意。”
“啊,我太高兴了。我知道你和我会相处得很好。这多么令人舒畅,想说就说,不会被大人提醒小孩只应该被看见,不应该被听见。我已经被人家那样说过一百万回了。人们总是嘲笑我,因为我使用大字眼。但是如果你有大思想的话,就必须用大字眼表达,是不是这样呢?”
“嗯,好像挺有道理。”马修说。
“斯潘塞太太说我的舌头一定是悬在中间的,但这不对——它的一端明明牢牢地固定在嘴里。斯潘塞太太说你住的地方叫绿山墙。我问她为什么,她说那里周围全是树。我更高兴了。我真的很喜欢树。孤儿院周围根本没有树,外面只有些瘦瘦的小树苗,周围围了些刷成白色的、像笼子一样的东西。它们本身看上去就像孤儿,那些小树苗。看着它们常让我想哭。我过去常常对它们说:‘噢,你们这些可怜的小东西!如果你们和别的树一起长在大树林里,苔藓和六月钟冠花爬满根部,一条小溪就在不远处,小鸟在枝头鸣唱,那么你们一定能长大,但在这里,你们却不能。我真的了解你们的感受,小树苗。’今天早晨要离开它们的时候,我特别难过。你肯定也会舍不得那样的东西。绿山墙附近有小溪吗?我忘了问斯潘塞太太了。”
“嗯,是的,屋子正南边有一条。”
“真没想到!住在小溪边一直是我的梦想。虽然我从来没指望自己真的会。梦想并不一定都会成真的,如果梦想能变成真的,不是太好了吗?现在我感觉差不多非常快乐。我不能感到完全快乐是因为——嘿,你叫这个什么颜色?”
她突然从自己瘦弱的肩膀上抽出一条长长的、极有光泽的辫子,举到马修眼前。虽然马修不习惯辨别女子发辫的色彩,但是对眼前这条辫子的颜色却没有太多疑惑。
“红色,是吗?”他说。
女孩将辫子垂放至原处,叹了一口气,这声仿佛来自于她内心最深处的叹气似乎正向外发出她积压许久的忧伤。
“是的,是红色,”她无可奈何地说道,“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能非常快乐了。任何一个长着红头发的人都不能。我不怎么在乎其他东西——雀斑、绿眼睛和我的皮包骨。我可以想象它们都不存在。我可以想象自己拥有美丽的、玫瑰花瓣似的皮肤和漂亮的、闪闪发光的紫色眼睛。但是我无法想象红发不存在。我试了所有的办法。我对自己说:‘现在你的头发是乌亮的黑色,黑得像渡鸦的翅膀。’但是我始终知道它分明就是红色,这让我的心都碎了。它将是我的终身遗憾。我曾在一本小说里读到过一个有着终身遗憾的女孩,但是她遗憾的不是红发。她有着金色的波浪鬈发,从雪花石膏般的额头一直长到脑后。什么是雪花石膏般的额头?我没能找到答案。你能告诉我吗?”
“嗯,我想我不能。”马修说,他已经有些晕头转向了。他觉得就像回到了莽撞的少年时代那次在野营中被别的男生怂恿爬上旋转木马时的感觉。
“啊,不管那是什么,它肯定是种美好的东西,因为她美若天仙。你想象过美若天仙时会有的感觉吗?”
“嗯,不,我没有。”马修老老实实地承认。
“我有,经常有。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你会选哪个——美若天仙、智慧非凡还是像天使般善良?”
“嗯,我——我实在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从来都没法决定选哪个。但是这对我来说没有太多的不同,因为我好像哪个也成不了。这点很确定,我永远不可能像天使般善良。斯潘塞太太说——哎呀,卡思伯特先生!哎呀,卡思伯特先生!!哎呀,卡思伯特先生!!!”
那当然不是斯潘塞太太说的;这孩子也没有从马车上摔下来,马修更没做什么惊人的事情。他们只不过在路上拐了个弯,进入了“林荫大道”。
这条被新不里奇人称做“林荫大道”的马路向前延伸四五百米长,被两旁高大的苹果树所形成的拱形完全遮蔽。延绵成林的苹果树是很多年前一位古怪的老农场主种的。向上望去,洁白芬芳的花朵形成一片长长的顶棚似的树荫。粗大的树枝下面,充满了绯红的暮色余晖,远方依稀可见的落日中的天空仿佛被着了色,一闪一闪的好像教堂走廊尽头的一扇玫瑰色的窗户。
它的美丽好像深深吸引了这个孩子,她一言不发,倚靠在马车上,瘦弱的小手紧握着放在胸前,如痴如醉地抬头望着头顶上那一片雪白壮丽的美景。甚至当他们离开了大道,顺着长长的斜坡向新不里奇驶去时,她都没有动一下或开口说一个字。她依旧神情痴迷地凝望着远方的西下斜阳,双眼注视着一幕幕壮丽的景色掠过发着红光的天空。他们经过新不里奇,那是一座喧闹的小村庄,小狗向他们发出声声吠叫,小男孩喊着,好奇的人们透过窗户盯着他们,他们仍旧沉默地行驶着。又走了三里路,这孩子还是没有说话。很显然,她能保持沉默,就像她能滔滔不绝地说话一样。
“我想你又累又饿了吧。”终于,马修大胆地问道,这是他能想到的为什么她沉默许久的唯一原因,“没多远我们就要到了——还有一英里路。”
她从出神的遐思中惊醒过来,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用游离许久的蒙!目光看着他。
“噢,卡思伯特先生,”她轻语道,“我们刚才经过的那个地方——那个一片洁白的地方——叫什么?”
“嗯,你一定是说林荫大道,”马修沉吟了片刻说道,“那是一个漂亮的地方。”
“漂亮?噢,用漂亮这个词似乎不准确。美丽也不准确。它们远远不够。噢,它太奇妙了——奇妙。这是我所见过的第一个比想象的事情更好的东西。它让我这里感到满足。”她将一只手放到胸前。“它让我有一种奇怪的心痛,但却是一种愉快的心痛。你有过这样的心痛感觉吗,卡思伯特先生?”
“嗯,我记不起来了。”
“我有过很多次——每当我见到极其美丽的东西的时候。可是他们不应该把这么美妙的地方叫做林荫大道。那样的名字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应该称它为——让我想想——喜悦的洁白之路。这难道不是一个好听的富有想象力的名字吗?如果我不喜欢一个地方或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给他们起个新名字,而且总觉得他们就是那样的。我们孤儿院里有个女生,她的名字叫荷普兹巴·詹金斯,但我总把她想象成叫罗莎莉·德弗罗。其他人也许叫那个地方林荫大道,但是我会永远称它为喜悦的洁白之路。我们真的还只有一英里路就到了吗?我又高兴又难过。我难过是因为这次旅行是这么的愉快,而每当愉快的事情结束时我总会感到难过。也许更愉快的事情会跟着来到,但是你永远无法肯定。事实上,好多次跟着发生的事并没有使人更快乐。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经验。但是想到快到家了,我就很高兴。你看,从我能记事起,我就没有真正的家。想到我快要有一个真正的家,我又有那种愉快的心痛。噢,这太好了!”
他们驾着马车向山顶驶去。下面是一个池塘,幽长曲折如一条河。一座小桥横跨中央,琥珀色的沙丘地带环绕四周,一直延绵至远处藏蓝色的海湾,塘中池水交替变换着色泽,形成一幅幅壮美的景观——橘黄色,玫瑰色,淡绿色,以及一些难以捉摸、不知名的颜色。桥的上游,池水一直流入那片种着冷杉和红枫的小树林,幽暗清澈地被笼罩在它们摇曳的婆娑身影中。零零星星的野梅子树从岸边斜伸出来,就像一位白衣少女正踮着脚向水中凝视自己的倒影。池塘源头的那片沼泽地里传出阵阵清脆、凄厉悦耳的青蛙叫声。远处小山坡上的白色苹果园旁坐落着一幢灰色的小房子,尽管天色还未完全暗下来,但是屋子的一扇窗户里已经出现了闪动着的灯光。
“那是巴里的池塘。”马修说。
“哦,我也不喜欢这个名字。我会称它为——让我想想——闪光之湖。是的,这才是它合适的名字。我知道因为我感到了一阵震颤。每当我找到最合适的名字时,总会感到一阵震颤。有没有什么事情给过你这种震颤?”
马修默默地想了一会儿。
“嗯,是的。一看到那些讨厌的白色蛆虫爬在黄瓜地里,我就会有一种震颤。我讨厌见到它们。”
“噢,我想那不是真正的震颤感觉。你觉得它能吗?蛆虫和闪光之湖之间看上去并没有太多的联系,为什么人们叫它巴里的池塘?”
“我估计是因为巴里先生就住在那边的房子里。他住的地方叫果园坡。如果不是因为它后面的那片灌木丛,从这儿你可以看到绿山墙。现在我们得过桥,绕过那条路,所以还有半英里路。”
“巴里先生有小女儿吗?嗯,不是太小的——和我差不多大。”
“他有一个十一岁左右的女儿。名字叫戴安娜。”
“哦!”她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多么动听可爱的名字!”
“嗯,我不知道。我好像觉得这名字里有些可怕粗野的东西。我更加喜欢简、玛丽或是其他一些朴素的名字。戴安娜出生的时候,有位男校长寄宿在她家,她父母让他给这孩子起名,于是他就叫她戴安娜。”
“真希望我出生的时候,也有位像他那样的校长在身边。哦,现在我们在桥上了。我要把眼睛紧紧闭上。我总是害怕过桥。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象或许当我们刚好走到桥中间的时候,它突然断了,像折刀一样把我们夹断,所以我得闭上眼睛。但是当我觉得走得快靠近中间的时候,我又总会睁开眼睛。因为,你看,如果桥真的突然崩断了,我还真的想亲眼看到它断开。那将会是多么巨大的轰隆声啊!我喜欢断开时的轰隆声。世界上有这么多可以喜欢的东西,真是太美妙壮观了。啊,我们过来了。现在,我要回头看看。晚安,亲爱的闪光之湖。我总会对那些我喜欢的东西道晚安,就像对人们道晚安一样,我想它们会喜欢的。那潭池水看上去就像在向我微笑。”
他们继续在山上驶着,快到一个弯角的时候,马修说:
“我们快到家了。那边就是绿山墙……”
“噢,别告诉我,”她气喘吁吁地打断他的话,一边试图抓住马修举向半空的胳膊,一边闭上眼睛,不去看他的手势,“让我猜猜。我肯定猜得很准。”
她张开双眼,环视四周。他们登上了山顶。太阳已西下,但是在柔和的落日余晖中,美丽的景色依旧清晰可见。西边,逐渐阴暗下来的教堂尖顶浮现在天空中。山下是一个小山谷,远方是一座平缓延绵的山坡,若隐若现的农庄散布其间。孩子急切地转动着眼睛,从一个地方看到另一个地方,目光中充满了渴望与依恋。最后,他们在左边一座远离马路的农庄前停下,四周被树林所环抱,屋前的树开着花,农庄在树影婆娑的暮色中隐隐约约地显出些白色。向上看去,无瑕的西南边天空中一颗大大的、水晶般透亮的星星眨着眼,好像一盏充满希望的指引之灯。
“就是它,是吗?”她指着问道。
马修高兴地拍了一下马后背上的缰绳。
“嗯,你猜对了!可是,我估计斯潘塞太太已经向你描述了它,所以你能辨得出它。”
“不,她没有——真的,她没有。她所说的好像是其他的房子。我一点都不知道它看上去会是什么样。但是,当我一看到它,我就感觉那是我的家。噢,我像是在梦中。你知道吗,我胳膊肘以上一定青一块、紫一块了,因为今天我捏了自己好多次。每隔一小会儿,我就会有一种可怕的、毛骨悚然的感觉,真担心它是一场梦。然后,我就掐自己,看看是不是真的——直到我突然想起来,就算那只是一个梦,只要我可以,我就最好接着做下去,所以,我就停下来不再掐了。但是,这是真的,我们就要到家了。”
随着一声欢呼,她重又陷入了沉默。马修不安地动了一下。他暗自庆幸,将由马瑞拉而不是他去告诉面前这个孩子,她期望已久的家根本不属于她。他们驶过林德的山谷,天色已经很暗了,但是还没有暗得使林德太太无法看见他们,从她那占据有利位置的窗户,林德太太看着他们上了山,走进绿山墙的小路。当他们来到家门口时,马修以一种他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力量向后退缩,回避那即将被揭示的真相。他想的不是这场错误可能会给马瑞拉或自己带来什么麻烦,而是这孩子的失望。当他一想到欣喜若狂的光芒就要从她眼中熄灭,他就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就好像他将参与一场残杀——这种感觉和他杀小羊、小牛或者其他什么无辜小动物时的感觉异常相似。
当他们进去的时候,院子里已经非常黑了,周围杨树上的叶子在沙沙作响。
“听,树儿在梦中说话。”当马修抱她下车的时候,她轻声低语,“它们一定在做着美丽的梦!”
接着,紧紧挎着那只装着“她全部家当”的手提包,她跟着他进了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