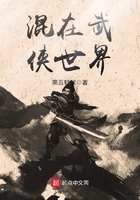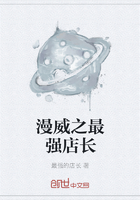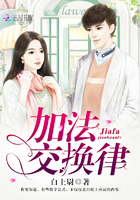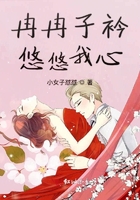相对于朴野、和平、明丽、宁静的乡村世界,是黯淡、矫饰、鄙俗、喧嚣的都市世界;相对于女性、老人和儿童温柔、慈爱、稚拙无机心的世界,是成人、男性虚伪、暴戾、冷漠的尔虞我诈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有自作聪明的市民、故作姿态的体面绅士、高深莫测的教授、怯懦庸碌的官僚、俗不可耐的太太和矫揉造作的小姐,京派以讽刺的笔调描绘着都市没有色彩、失去个性的人生、生命锈蚀的斑斓。
从对两种世界的艺术展示中,我们能够十分清晰明了地发现京派两种相辅相成的情感方式和审美态度并对文体产生的影响:乡村抒情体和都市讽喻体。对乡村抒情体小说我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使用“田园牧歌”、“东方情调”、“民俗风情”、“古典浪漫抒情”、“原始生命力”等词语来把握艺术形象、艺术境界的意态与基调,而在都市讽喻体小说中,则让我们感受对现代文明的某种抵触情绪,对人性扭曲异化的忧虑。从这一对立与对比中,某些精神心理分析可能为我们提供有关创作主体的作为“乡下人”的优越感、对都市人鄙夷并以此来加固在都市生存的自信这样的纯属个人性的资料一类的东西。同时,关于京派作家的文化性格、文化心理结构也会在对立与对比中引起关注。京派作家在对古典与现代、传统文化与西方话语于取舍迎拒中呈现出怎样的一种错综复杂的文化心态?在怀恋过去、追慕古风、眷依乡土的民族认同之中尚未坠入保守自囿,依然对现代、对西方文化保持着谨慎的开放、接纳、进入的姿态,这仅仅是一种文化尴尬窘态的征象,还是一种经过整合或者说趋向整合的现代文化精神的显现?“这派作家高雅和谐的心态无法与商品化的文明相调适,他们只好到清疏的乡野、蛮荒的边地、远离世浊的桃花源、或未浸染的童心中,寻找灵魂的归宿,寻找健全人性和血性道义的源泉。”[35]或者他们真的是一群现代中国的堂吉诃德?显然他们也不是林纾、刘师培、辜鸿铭、章士钊、梅光迪。在我们指出京派文学“和谐、圆融、节制、恰当、冲淡”的审美特点时,我们是在使用传统的美学概念来概括京派文学给予我们的审美感受,用传统的美学尺度来丈量京派的艺术世界。的确,京派文学事实上不缺少这些。我们在使用传统的美学尺度时是因为我们以为或者发现传统的东西——情感的、美学的、甚至人格方面的(文化心理、个人性格气质)在京派作家和作品占据上风。对来自西方文学、文化的影响,我们更多倾向从形式、技法(象征手法、心理描写)上、趣味(对工业文明批判、回归自然)上考虑。这趣味的偏好迎合了京派的需要。对京派这方面的看重,启发了这样的思路:由于京派文学深情脉脉地注目着正在消逝的过去,忸怩不安地打量着现代工业文明,京派带有明显的规避现实、远离时代的倾向,于历史大开大合、吸纳吐吞、急遽起伏的时期,超然于政治斗争、现实功利之上。从这个思路获得的关于京派的印象便只能是:文学上的虔诚主义者,和政治上的高蹈派。
京派是否与时代错位?是否与社会历史进程发生脱节?所谓时代、政治到底是什么?文学与时代、政治应该是一个什么关系?文学如欲获得时代性,是否就应与先进的阶级及其政党的利益相联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直纠缠着中国现代和当代作家以及文学研究者,这是一个宜于深入讨论却从未深入讨论的问题,简便的办法是执行双重标准。实际上,这的确不是一个过于复杂的疑难问题,倘若将“文学的政治”和“社会(实践)的政治”区别开来的话。
目前文学史研究中很少再出现“主流文学”、“非主流文学”的提法,这多少反映了史学观念上的变迁。京派文学(及其他类似的文学现象)在文学史中的升位,不能只看作是研究兴趣向这里转移,而是研究中历史理性的复位。京派文学曾经是历史的一个环节,而这个环节在已往的历史叙述中被截掉了。因此必须将它重新焊接起来。然而,如何焊接——显然又在向历史叙事方式提出问题了。
“对话时代的叙事话语”,这个题目意在概括论文的思路。作为文学叙事的京派文学,我们必须确立它的话语地位,这一点看起来是没有疑问的。但事实上却仍存在着疑问。今天除了研究者外,也许很少有人去看《短裤党》甚至《林家铺子》,而不难从普通阅读者手中发现周作人、林语堂的散文和沈从文、汪曾祺的小说,但是在观念中,在历史叙述中,两者的话语地位依然是一个不等式。我们有必要将所有的话语放回到它们共生语境中,去理解它们言说了什么和怎样言说的,它们要求的是话语的权利还是话语的权力。我们在试图这样做的时候,需要有个预设的前提,即他们共生的语境、那个被称之为时代的“现在”,正行进在探索真理的路途中。正因为如此,它得承认所有的话语在它的拥抱中都具有权利。承认话语的权利,也就是说,话语之间是一种对话的关系。“这种对话关系存在于话语领域之中,因为话语就其本质来说便具有对话的性质。”[36]对探求真理的使命而言时代提供着对话的命题、对话的历史空间。特别在近代以后尤其是五四以后,传统话语分崩离析,西方话语蜂拥而入,新的历史话题出现的现代,无可争辩地使时代成为对话的时代。这样,话语是否体现了话语本质——具有对话性质成为衡量话语是否是时代的话语的一个尺度。某些历史地丧失对话能力的话语不是时代话语,如“为文言或拟古”,“遵守过去的权威”[37]的业已僵死的权力话语。未成为权力话语之前,就历史话题发言,则应视为具有探索真理权利的话语。在上述意义的出发点上,我们将京派文学理解为“对话时代的叙事话语”。这个问题将在第一章中作进一步讨论。
对研究者来说,京派文学是研究的对象,是作为客体而存在的。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象、客体并不能如在自然科学研究中那样保持它的客观性。科学研究在其过程中也并不排除主观的介入,但在具有成效的结果里面,则必须是淘去了主观推测的成分的。两个异地的相互隔绝的科学家对同一问题进行研究,可以得出相同的正确的结论,当结论不同时可能两个都错,但不能两个都对。作为价值科学的文化社会科学,却无法不“从现在的视野中构造过去”,也就不可能“客观地、科学地复原过去”,“客观性”是这个领域中一个永远的神话。
然而这不等于说社会科学研究只能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中无力自拔。在历史研究、文学批评中,包含事实与评价两部分,应让视野所及的范围内的事实呈现出来,同时,使研究的对象不是一个漠然的无动于衷的物性客体,而是一个有着自己声音的主体,这个主体能够随时起来为自己辩护与研究者驳难——这正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而且这也似乎是历史科学中的“特殊的客观性”——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由此成为可能。基于这样的考虑,在主观上,也企望对于京派的研究与批评成为主体间的一种对话(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
注释:
[1]黄修已:《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327页。
[2]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3]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二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5]李俊国:《都市的漩流与京城的风度》、吴福辉:《乡村到都市的哀歇与幻梦》,《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比较分析》,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李另有《“京派”、“海派”文学比较研究论纲》发表于1988年第9期《学术月刊》,与此文异题同文。
[6]吴福辉:《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带着枷锁的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李俊国:《三十年代“京派”文学思想辨析》,《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7]杨义:《京派小说的形态和命运》,《江淮论坛》1991年第3期;李德:《论京派抒情小说的民族特征》,《中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2期;刘锋杰:《论京派批评观》,《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张鸿声:《与乡村对照中的都市》,《郑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周海波、杨爱琴:《黄昏里的生命独语》,《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
[8]京派与海派之争,是由一向以温和、不介入文坛争斗的沈从文挑起的,沈从文自1928年去上海后,对上海文坛的商业气息有深切的体会,因而对海派文学深恶痛绝,撰写了《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关于海派》等一系列批评海派的文章。杜衡(苏汶)作《文人在上海》予以反驳。鲁迅、姚雪垠、胡风、徐懋庸、曹聚仁等也参加了这场论争。鲁迅以“‘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的评语,将京派与海派各打了五十大板。
[9]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二卷),第586页。
[10]李俊国:《都市的漩流与京城的风度》。
[11]刘锋杰:《论京派批评观》。
[12]鲁迅:《“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第432页。
[13]刘锋杰:《论京派批评观》。
[14]沈从文:《论“海派”》,《沈从文文集》第12卷,第160页。
[15]吴福辉:《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
[16]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205页。
[17]《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319页。
[18]吴福辉:《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
[19]李俊国:《三十年代“京派”文学思想辨析》。
[20]周作人:《〈语丝〉发刊词》。
[21]同上。
[22]冯至:《〈骆驼草〉影印本序》。
[23]卞之琳:《〈李广田散文选〉序》。
[24]卞之琳:《〈冯文炳选集〉序》。
[25]李广田:《自己的事情》。
[26]《文学季刊》编辑除郑振铎、靳以、巴金外,还有冰心、李健吾、杨震文、李长之。在《发刊词》中即已表明不以“游戏的态度去写作”,“以忠实恳挚的态度为新文学的建设而努力”的严肃文学立场。其特约撰稿人108人,来源极为广泛。《文学季刊》出至第2卷第4期,于1935年12月停刊。《水星》的作者基本上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队伍,主要有巴金、卞之琳、何其芳、沈从文、李健吾、李广田、李溶华、南星、梁宗岱、靳以、废名、周作人、郑振铎、臧克家、萧乾、程鹤西、蹇先艾、张天翼、林庚、李威深,茅盾、老舍、冰心、吴伯箫、艾芜、丘东平、陈荒煤、万迪鹤等,亦在此刊物上撰文。《水星》抗战爆发后停刊。《文学杂志》创刊后不久即遭逢卢沟桥事变。1947年复出。前期作家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杨振声、林徽因、俞平伯、卞之琳、萧乾、钱锺书、杨绛、何其芳、林庚、梁宗岱、冯至、陆志苇、朱自清、胡适、林语堂、老舍、陈西滢、戴望舒、施蛰存等,后期作家有较大的变化。
[27]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二卷),第599页。
[28]1936年10月25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批评“文章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差不多”,这种创作上的“一元现象”。1937年2月21日又于《大公报》上发表《一封信》,认为:“一个政治组织固不妨利用文学作它争夺政治的工具,但是一个作家却不必跟着一个政治家似的奔跑。”“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向各方面滋长、繁荣,拘束越少,可试验的路越多。”朱光潜《我对于本刊的希望》呼应了这一观点。《大公报》同时组织起关于“差不多”的讨论,孙伏园、吴蔷、彭昭义、光寿、杨刚、茅盾等为此撰文。杨刚《关于“差不多”》,赞同沈从文的观点,称赞作者“清醒而勇敢”(《大公报·文艺》1937年2月24日)。光寿的《谈“差不多”并说到目前文学上的任务》(1937年《光明》第2卷第7期)对“差不多”于不满中又有所回护。茅盾的《新文学前途有危机么》(《文学》第9卷第1期)、《关于“差不多”》(《中流》第2卷第8期)两文,对沈从文提出了较严厉的批评。1937年8月沈从文于《文学杂志》(第1卷第4期)上发表了《再谈差不多》,坚持自己的观点。
[29]李健吾:《读〈里门拾记〉》。
[30]《文学杂志》第1卷第2期《编辑后记》。
[31]《中国文艺往哪里走?》,1947年5月5日《大公报》社评。《自由主义者的信念——辟妥协骑墙中间路线》,1948年2月2日《大公报》社评。
[32]除刘锋杰《论京派批评观》外,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也分别论述了周作人、李健吾、朱光潜、沈从文、梁宗岱、李长之诸家的批评思想。
[33]《沈从文小说习作·代序》
[34]鲁迅:《七论“文人相轻”——两伤》,《鲁迅全集》第6卷,第403页。
[35]杨义:《京派小说的形态和命运》。
[36]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第252页。
[37]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