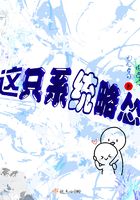有人开枪。警察中弹?说不好。
怕得就是没头绪。
偏偏这会儿一丁点儿也没有。
路上全是深深浅浅的车辙,弗兰克·利特菲尔德警官一路颠簸,心疼地糟践着自己的爱车。附近几个县的同僚们开的不是悍马就是重磅SUV[1],但是利特菲尔德局里的经费紧巴巴的,部门预算投到别的地方去了——县里新建了一所监狱,法院那边又加强了安保。法官们似乎不太喜欢隔三差五地出现疯子当庭开枪的场面,这无疑是给他们自己判了死刑,只不过用来拍板的,不是冷酷的法槌,而是滚烫的枪口。何况,利特菲尔德也有自知之明,他就该拣最破烂、最皮实的车开。这辆已经让他蹂躏到体无完肤的大“别克”离进垃圾场也不远了。
其实,有些人会说大“别克”的主人离进垃圾场也不远了。利特菲尔德在最近一次选举中比对手只多了12票当选为警长。就这,还是重新点票后的结果。自上世纪70年代起,皮克特县就一直不接受民主党人来做警长,可是政治波动的影响最终还是渗进了这个南方最偏远最保守的地区[2]。人们依旧悄悄议论着红教堂,议论着他死去的弟弟以及昔日的副手。麻烦总是和利特菲尔德如影相随,在他这一行来说,这些都绝非好事。
利特菲尔德从不提往事,因为往事不堪回首。换成个没那么“自信”的人早就撂挑子不干了,至少不会还干劲十足地争取岗位竞选。如今的警察工作大多只需敲敲键盘,不用冲锋陷阵。于是,在47岁的利特菲尔德看来,还有几年好日子在等着他。除了当警察,他没别的选择,悲惨就悲惨在这里,而那些“重获新生”的机会宛如挂在钓钩上的耶稣,总在他面前晃悠。
也许,机会又来了。在收到“有人开枪”的报告后,利特菲尔德的心已经顶到了扁桃体,尤其他的两位副警长都牵涉其中。莫顿和佩里埃特都是局里的新人,两人均为刑事司法专业毕业,周六下午的班正好给他俩热热身。虽说警察的家常便饭是处理家暴求助和酒驾,可这里是皮克特县,以利特菲尔德的丰富阅历来说,任何常态都有可能瞬间变态,尤其在穆拉托山一带。
对讲机里噼里啪啦的声音已经持续了两分多钟,利特菲尔德还没搞清自己身在何处。和大多数本地男人一样,年轻的时候,他也到山上打过猎,只是后来这里又发生了变化:阔叶林变得愈发茂密,岩石碎成一块块分散各处,从前为伐木开辟的小道也渐渐回归了原生态。现在,树叶敲打着他的挡风玻璃,后视镜也被一根树杈撞断,滚到底盘下,压得粉碎,别克车的前轮陷进了沟里。利特菲尔德决定步行走完余下的行程。
他给局里打去电话,命令其他当值警察前去山脚下盯梢。如果真有漏网的枪手,那怎么也不能让他窜到镇上去。穆拉托山为左右两条道路环抱,只不过稍有点常识的人都会从森林里跑路,免得被人看见。利特菲尔德这么做的目的只是将镇民们隔离到射程之外,他自以为这是一记高招。
问题在于,这招还有那么点小小的不如意,就是一旦事情突生诡异,连个目击证人都没有。
利特菲尔德一路步行,凭感觉辨着方向。就在这时,传来了第三声枪响。他左边什么地方传出一声叫喊,估计得有百来尺[3]远。一定是他的两位副手一路把疑犯追进了树林,此时双方正在山梁上对峙。
善与恶,是与非,明与暗,千百年来,它们在道德与法律的灰色地带,拼得血流成河。也正因此,像利特菲尔德这样的人才有了当警察的冲动,和成为警察的机会。利特菲尔德默默地吐着脏字儿,搞不懂自己到底算哪头的,他慢慢地走在林间,猫着腰,一步一挪。
那俩家伙怎么不用对讲机呢?
他们最后一次回复是报告自己的位置,那会儿两人正处理一宗入店行窃的报警。考虑到在店里偷东西的人逃离后很少有被逮到的,也许他们只是想演一出急速追凶的好戏来哄哄店主罢了。不过,现在怎么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让每个人都能安然无恙地下山。
“这儿!”是莫顿在喊。
利特菲尔德拔出格洛克手枪,几个月来,这还是他头一回掏家伙。他冒着暴露行踪的危险答腔:“你们没事吧?”
“佩里埃特有事。”
“中枪了?”
“差不多。”莫顿大声喊道。
利特菲尔德穿过林子,爬上斜坡,胸口有点憋闷,重重喘着气——他可没想到自己的身体这么不中用。他慢慢绕过一块大岩石,苔藓飘进领子,弄得人丝丝发痒。
“要么中,要么没中。什么叫差不多?”
“他受伤倒下了,可实际上又没中枪。反正我是没瞧出来。”
此时,利特菲尔德已离得很近了,用不着大声嚷嚷,只是那两位副手还遮在一丛万年青后面,看不见身影。“开枪的人呢?”
“怪就怪在这里。我一个人都没看见。”紧接着,就听莫顿小声说道,“挺住,兄弟,没事的。”
利特菲尔德从一片低矮的雪松林后面绕过,手里紧紧握着他的格洛克。自从亚彻·麦克福尔[4]事件后,他有些年头没朝人开过枪了,而麦克福尔到底算不算是个“人”,他始终也没搞清楚。这至今是一件悬案。如果被你亲手结果的人突然又从地下爬了上来,顺河漂走,徒留一个干土堆在地上,你定会十分诧异:我到底杀没杀他呢?
利特菲尔德靠在一棵橡树上喘着气,树皮刮擦着他的脸庞。以目前的有利地形,一低头便可看见两位副手蹲在一堆犬牙交错的岩石后面。这些大石头拔地而起,好像巨人的一口豁牙。莫顿年纪最小,因为胡子刮得太猛,脸颊有些发红。这会儿他正往山坡上利特菲尔德的左方看。利特菲尔德查看了周边的树木,毫无动静。
“喂。”利特菲尔德小声叫莫顿,他知道想要出其不意地抓到人已经不太可能。远处的警笛声很明显是在提醒枪手,大部队就要来了,再说,下山的路也就那么几条。
“看那儿,警长。”莫顿说着,冲着山顶挥了挥自己的手枪。
“看什么?”
“有点小动静,不过也没什么。大概就是只小鹿。”
“佩里埃特什么情况?”
“诡异。”
诡异?他妈的什么情况叫‘诡异’?
利特菲尔德朝森林瞟了一眼,林木盘根错节,遮天蔽日,腐殖土下沉睡着年代久远的物事。“他开过枪?”
“三枪。最后一枪,我就在旁边,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朝谁开枪?”
“该死。”利特菲尔德嘟囔道,“第一枪不中就没戏了。”
利特菲尔德走近山梁,慢慢探出身子,既要能看见枪手,又不至于会被对方一枪干掉。如果那三枪是佩里埃特开的,那这人可能不止是枪手这么简单了,正确的提法应该叫“疑犯”。可是当时除了佩里埃特,并无其他目击证人,这种情况佩里埃特变成他们常说的“涉案相关人员”。每当警察不清楚具体状况时,就会用上这个委婉的词儿。而他,对于谁是肇事者已经了然于心,叮铛洞就不是个让人省心的家伙。
“家伙。”妈的,我又把个东西当人看了。我头一回看见一坨说着话,形状变来变去的脏东西时就该去疯人院检查检查。要是那样,断不至于有那么多人倒霉,或许其中一些还能保住性命。
利特菲尔德低下头,发现自己握枪的手正在发抖,很有路易斯·拉莫[5]小说人物的感觉。对利特菲尔德来说,唯一想着好过点的是叮铛洞在山的另一头,离山梁和佩里埃特的目击对象足有几百码之遥。
“掩护我。”利特菲尔德对莫顿说道。这小子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还有些泪汪汪的样子,就像两颗奶油橄榄,不过,他还是憋出一股自信劲儿,点了点头。警长考察下属的时候很少会把他们置于生死听天由命的地步,不过利特菲尔德倒是希望莫顿对得起自己简历上那些牛逼哄哄的词儿。利特菲尔德向下三步,不料踩在滑溜溜的叶子上,一屁股摔到了地上。他一挣扎,顿时挣出个屁来。
利特菲尔德暗暗骂了一句娘,用手和膝盖撑着跪起来,放低重心,朝莫顿和佩里埃特的方向快速跑去。佩里埃特目大无神,直勾勾望着天空,仿佛是在高高的云朵中寻觅天使。这位倒在地上的警官是伊战老兵,在完成刑事司法专业培训之前,曾先后两次随国民警卫队出征海外。虽说北卡罗来纳山区没有黄沙大漠,没有摇摇欲坠的清真寺,更没有路边炸弹,可也许正是迟发的创伤性后遗症令他经受着压力失调的折磨,让自己幻想出一些怪异的场景。
“你没事吧J.R?”小字辈儿的副警长们在执勤的时候,多是以名字首字母来称呼彼此,这一恼人的习惯是从高速巡警那儿学来的。利特菲尔德心里还是比较喜欢叫他“吉米”,这听上去更有人情味儿。副警长看样子是想用上所有人类能用的交流手段,但他无声地翕动着嘴唇,眼皮直跳,目光失焦。
“开第三枪后,他就这个样子了。”莫顿说道。
“他朝谁开枪你没看见?”
“没看见,我就听见他喊了声‘看见没?’接着就一下子瘫掉了。我看着他扔掉手枪,然后蜷成一团,一直到这会儿。”
利特菲尔德伸出两指,搭在佩里埃特的颈动脉上。佩里埃特的脉搏搏动快速有力,身上也不见外伤。不过,内心最深处的创伤往往隐而不见,心灵得受尽折磨,伤口才能结痂。
“我们正在追那几个小孩儿,”莫顿说,“J.R.追的是最快的那个,一直追到山梁边上。”
“你们靠近过那个洞没?”
莫顿眯着眼,摩挲着自己刮了胡子皮肤还有点发炎的脖子。“倒是能瞧见,就是没进去。您是说有人躲在里面?比方说是逃犯,看到警察后吓着了?”
“放完头两枪后他有没有说过什么话?”利特菲尔德凝视着山脊线,却什么都没发现。连乌鸦都受了惊吓,陷入沉默中。
那儿看上去就像恐龙的脊梁骨,从这头到那头,满是巨石和笔直高耸的大树,终年的大风摧折了树枝。阿巴拉契亚山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山脉,虽然历经沧桑,却仍然有一部分在天长日久中存留下来,仿佛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庇佑它。穆拉托山也是如此,利特菲尔德敢说,这大山是有心跳的。他看了看表,发现从下车后,就没走过字。于是,他摇了摇左手腕,又用枪柄敲敲表盘,但是闪出的红色的数字始终是5:53,好像在嘲笑这表已经完蛋了。
“我赶上他的时候,他好像说了句‘他脚不沾地’。您觉得这是什么意思?”
对利特菲尔德而言,这句话该是书上或电影里才有的,可佩里埃特却并非文艺青年。他基本上算是那种喜欢吃炸猪皮的轮滑竞赛爱好者。当然,副警长对电子游戏也十分着迷,他特别喜欢玩那种大开杀戒的游戏。那种游戏里,无所谓好人坏人,只管按杀人的多少计分。佩里埃特是民主党的注册党员[6],这一点从他工作的谈吐中很难看出来,他还去参加了位于松涛路上一家新落成的大教堂里举办的浸信会[7]。利特菲尔德不是那种喜欢管手下私事的人,除非他们的行为给局里带来了麻烦。
眼下,佩里埃特的问题远比什么党派政治和有个疯子女友还严重,利特菲尔德不知道要怎么蒙混过关,让自己副手的档案里不留下污点。但凡有执勤警员开枪射击,州调查局就会插上一脚,这个时候,就看谁先干净利索地写出报告,报告要摆出种种理由,尽可能地长。若是平常,佩里埃特大可以为自己开枪作出辩护。不过这回,没有大场面不说,连个嫌犯都没有。
换句话说,这一回只能靠利特菲尔德替他摆平了。利特菲尔德也吃不准能否三言两语就让佩里埃特忘掉刚才发生的事。刚才这两分钟,佩里埃特居然连眼都没眨一下。
“他没朝小孩儿开枪吧。”利特菲尔德问道。
“没有,警长。我追上来的时候,那小子早没影儿了。”
“你见到这孩子长什么样了吗?”
“那些小孩全一个样。就是群玩滑板的朋克族。还有两个在山那头,不过我们听见枪响的时候,他们都溜了。”
“你们?”
“对啊,还有那个什么阿玛纳西亚,是小店老板。”
“这么说还有一个目击者要应付啰。”利特菲尔德心里也犯嘀咕,既然什么都没看到,算哪门子“目击”呢?
“未必。他比那俩孩子跑得都快,叫得跟克雷·艾肯[8]演唱会上的小姑娘似的。”
利特菲尔德沿着山坡往下看,一片寂静,连风吹树叶的沙沙声都听不见。此时,他很庆幸自己已经派人去盯着主干道。至少在他把故事编圆之前,越少人知道越好。
相比佩里埃特,他要操心的可多了去了。鹿桥置业那帮人把宝都押在了穆拉托山,一旦这山上修起一栋栋价值百万的度假别墅,大把大把的税收便会滚滚而来,县里那些长官一个个准乐得尿失禁。但只需一点负面新闻,这项目就会受到影响。而且,有三位官员已经准备参加连任选举了,他们不能要挟炒掉他,却会缠着他不放,使出浑身解数,求他别张扬这件事情。
“咱俩把他扶起来。”利特菲尔德说着,指了指杂草丛生的伐木通道,“我的车比你们的近,就在一百码开外。”
佩里埃特摇摇晃晃,像个喝醉的水手,不过好歹站了起来,随即一头栽倒在莫顿肩上。利特菲尔德把他俩扶正,调整两人朝着正确的方向。
“要叫救护车么?”莫顿问道。
“不必,去局里再说。你们先去,我去山梁那儿看看就来。你一个人搞得定吧?”
“搞得定,好些和我出去的女人醉得比这离谱,照样把她们搞上床。”
“好吧,你可别动手动脚。”
莫顿想挤出个笑容来,脸上的表情却显然是紧张不安,“您觉得他在朝什么开枪?”
“别着急,我们会找到答案的。熊,疯狗,妈的搞不好还有野生食人羊。怪事全跑到这破山头来了。”
佩里埃特跟着莫顿一路跌跌撞撞地经过了树桩、倒地的大树、嶙峋的岩石。他脚上的那双漆皮鞋在地上拖出一道长长的黑泥印。与此同时,利特菲尔德爬了最后一百尺上到山梁上。穆拉托山顶上的松树、橡树、榉树被酸雨侵蚀得泛了白,树枝在狂风和暴雪的摧残下体无完肤。不过,下面的都还长得不错,一眼望去,立刻会联想到里面生活着可爱的花鼠和纯洁的小鹿。巍峨粗犷的山梁上则巨石林立,悬崖峭壁遍布四周。
利特菲尔德站在距离谷底大约一千英尺的山顶上来了个360度全景俯视。泰特斯维尔小镇布局散乱,崎岖的地势让这里的街道都拧巴到了一块。主干道是一条四车道的林荫大道,和美国其他地方的林荫道没什么分别,那儿也有沃尔玛、西北牛[9]、塔克钟[10]、汉堡王、车地带,还有大大小小的银行,皮克特县一半的房产都经他们的手贷款。利特菲尔德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整个小镇只有一家汽车旅馆,一家杂货店,还有一家附带加油站的灰狗巴士终点站。如今,泰特斯维尔已是相邻三县中最大的小镇,成了一个商业中心。房产中介商、贷款机构、律师全都涌到此地,等着从别墅主人的身上分一杯羹,好比一群贪吃的猪猡,挤在同一个食槽下等着泔水流出。
然而,并非事事都像这些白色混凝土、玻璃和钢材一样新鲜光洁。穆拉托山一直看着这一切,关于它的传说已经渗进了泥土,就像春天消融的冰雪,奔涌而出,在山谷间流淌。一百年前的过度砍伐,令这片森林在如今的开发商眼里不过只是一块块绿地。可它依旧保持着原始的味道,仿佛已经绝迹的掠食者随时都会从暗处扑出来,露出饥饿的獠牙。镇子离穆拉托山不过徒步一个小时的距离,却好似离这个荒野的世界有千里之遥。
利特菲尔德沿着山梁慢慢走,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留下了新的踪迹。他发现一堆动物的粪便,看上去像是鹿留下的,非常干,一摸就成了粉,所以不可能是佩里埃特看见的东西留下的。
“他脚不沾地。”
听起来也不像鹿。在皮克特县,死人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死人也能站起来走路,当然了,很少有人记得最近一次发生这事是什么时候。那些记得的,也希望把它们长埋心底。
正当利特菲尔德决定放弃,下山去找警车的时候,无意间发现地上有几道长长的印子。看上去,这像是一个人拖着鞋跟走路,一边走,一边还带起了脚边的树叶。印子从几棵倒下的大树旁一直延伸到一片爬满蕨草的岩石堆。利特菲尔德握着枪,循着痕迹走去,他走到石堆那儿,却只看到一个小土丘。痕迹也突然中断了。再没有另一双脚。也没有另一张脸,另一副躯壳,或者,另一个灵魂。
利特菲尔德跪在地上,捏着冰凉的黑土。到了这一步,还能拿什么来对抗这座大山和它背后神圣却又令人作呕的秘密呢?
注释:
[1]SUV:运动型越野车。
[2]政治波动的影响最终还是渗进了这个南方最偏远最保守的地区:水门事件后,共和党人名誉扫地,民主党重新掌权,整个七十年代,全美选民都处于对政党政治不信任的状态。
[3]尺:后文中的尺,皆指英尺。
[4]亚彻·麦克福尔:本书作者另一本书《红教堂》中的主要人物。
[5]路易斯·拉莫(1908-1988):美国著名小说家,作品主要是西部小说,历史小说,科幻小说,诗歌和短篇小说集。
[6]注册党员:美国人入党就像去吃自助烤肉,只要在人家给你的单子上打勾就行。
[7]浸信会:基督教新教宗派之一。因反对婴儿受洗,主张只对理解受洗意义的信徒施洗;洗礼采用全身浸入水中,不用点水于额的方式,故名。
[8]克雷·艾肯:首届《美国偶像》比赛冠军,后出唱片。
[9]西北牛:美国常见的家庭餐馆。
[10]塔克钟:美国快餐连锁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