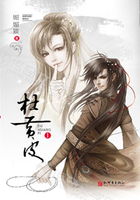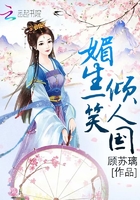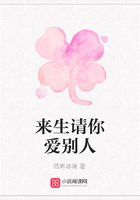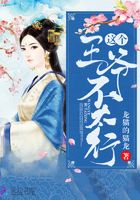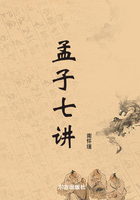董乐山
冯内古特的作品介绍到国内来,《囚鸟》已不是第一部了。但是对冯内古特作品的分析,似乎还莫衷一是。
有人说他是科幻作家,有人说他是黑色幽默作家。读了《囚鸟》以后,我想中国读者不难自己得出结论来。他既不是科幻作家,也不是黑色幽默作家。
不错,冯内古特利用过科幻小说这一文学体裁。但是不论从他的初作《自动钢琴》,还是已译成中文的《猫的摇篮》都可以看出,他写科幻小说,不是为科学而幻想,而是有他更深刻的用意:借科幻以讽今。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写文章总是得有个借题发挥的因头。”同样,他的有些作品看似游戏笔墨,可以归为黑色幽默,但是亦岂仅幽默而已!
其实,一个作家用什么形式来表达他的思想是次要的,重要的事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思想。这当然并不是说形式在文艺创作中不重要,他还是很重要的。但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也是为内容所决定的。对形式的选择和追求,都是为了最好地表达内容。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必因为冯内古特究竟是科幻作家还是黑色幽默作家而争论不休了,也没有必要在文学争论中把作家贴标签分类了。文学评论家毕竟不是图书馆学家。如果要分类的话,唯一的类别恐怕是,某个作家是严肃作家,还是流行作家。但是有的时候,甚至严肃作家也写流行作品,流行作家也有严肃的主题。
但是文艺评论似乎脱不了贴标签的痼习,什么浪漫主义,什么现实主义,名目不可谓不多,但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就不得而知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对人类的贡献和由此而发出的光芒,并不因后人给他们贴什么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标签而有所增减。相反,在百年千年之后,他们的作品仍像丰碑一样屹立,而标签却没有不因风雨的侵蚀而剥落的。因此,文艺评论家最好还是多谈谈作品的本身,它的形式与内容,比较近似地探索了一下作者的用意,而不是简单地贴些标签。
我用“比较近似”一词,是因为我不相信文艺评论家有这么大的能耐,可以自称能够完全正确地理解作家写某一部作品的用意。他们多半是根据个人的理解对作品作主观的解释。至于这种解释在多大的程度上符合作家的原意,只有作家心里最有数。但作家多半对此保持缄默。他似乎没有这种闲工夫。不然他就不是个作家而是文艺评论家了。何况有些作家都已作古,即使他们愿意,要请他们出来写一篇“我为什么写XX”也办不到了。
话扯得远了,还是回过头来谈谈《囚鸟》。
《囚鸟》是一部与冯内古特其他作品迥然不同的作品,它既不是科幻小说,也不是黑色幽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但它又不是作家本人的自传,而是整整一代人的自传。这话从何谈起,且让我慢慢道来。
《囚鸟》写的时间跨度是从19世纪初到尼克松下台,它所穿插的历史插曲,从萨柯与樊才蒂事件起,经过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希斯和钱伯斯事件,朝鲜战争,一直到“水门事件”。它的主人公与其说是主人公本人,不如说是整整的一代美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它揭示了美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激进转向保守,并最终沦为“水门事件”中一个不光彩的丑角的堕落过程。
冯内古特就像中国的捏面人一样,把这整整一代人的历史当作素材,左捏右捏,捏出了一个个看似面目俱非,却又特别逼真的人物来。《囚鸟》仿佛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那面镜子,历史在这里究竟是遭到了歪曲,还是归璞返真,只有过来人心里才明白。但是这是一部多么心酸的历史!只有冯内古特那样的大师才能把它颠过来倒过去,而仍不失它本来面目。
对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来说,读《囚鸟》也许觉得有些费劲,对于其中一些历史事实也许觉得有些生疏。但是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读《囚鸟》仿佛是重温旧梦,我相信不少过来人会一边读一边点头,会有似曾相识或者逝者如斯夫的感叹。
就怕我也是个摸象的瞎子。
1984年12月14日于病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