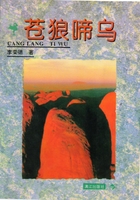这样,我就坐在监狱外面的长凳上等班车,佐治亚的烈日炙烤着我。一辆卡迪拉克[1]牌豪华轿车,车窗遮着浅蓝色的窗帘,行驶在这条通向空军基地总部去的车道上,到了中央线的那一边缓缓地放慢了速度。我只能看到司机,那是个黑人,他带着疑惑的表情望着监狱。那地方显然不像是个监狱。旗杆脚下有块不起眼的牌子上面只写着:“F.M.S.A.C.F[2].,外人请勿入内。”汽车继续往前开,一直开到四分之一英里外的一个跨道,才转过弯来,在我的面前停下,它的晶晶发亮的车前挡板就在我的鼻子下面。我在锃亮的挡板上又看到了那个斯拉夫血统的看门老头儿。后来弄清楚,就是这辆豪华的轿车引起了刚才维吉尔·格雷特豪斯到达的一场虚惊。它来来回回地寻找监狱已有一些时候了。
司机下了车,问我这是不是监狱。
这样我就有必要说做自由人后的第一句话了。“是的。”我说。
司机是个个子高大,颇有长者风度的中年人,穿着一身棕色马裤呢制服,黑色皮绑腿,他打开后门,对黑黝黝的车厢说话。“先生们,”他恰如其分地带着又悲哀又尊敬的口气说,“我们已到达了目的地。”他的胸口口袋上用红丝线绣的字说明了他的老板是谁。这几个字是:拉姆杰克。
我后来才了解:格雷特豪斯的老朋友们为他和他的律师提供了迅速、秘密的交通工具,把他们从家里送到监狱,免了他当众蒙羞。百事可乐公司的一辆豪华轿车天亮以前在曼哈顿他作公寓的华道夫酒店塔楼[3]的后门把他接走,送到拉瓜地亚机场隔壁的陆战队航空站。汽车一直开到跑道上,那里有一架国际旅游公司的喷气机等着他,把他送到亚特兰大,又是一辆遮了窗帘的豪华轿车在跑道上等他,这辆汽车是由拉姆杰克集团的东南区办事处提供的。
维吉尔·格雷特豪斯从汽车中钻出来,他的穿戴几乎与我一模一样,一套灰色的条子衣服、白衬衣、军团斜条领带。我们所属军团不同。他是冷流近卫军团。他像惯常那样吮着烟斗。他扫了我一眼,时间极短。
接着从车里钻出来两个油腔滑调的律师——一个年轻,一个年老。
司机到车后去取囚犯的行李,这时格雷特豪斯就和两个律师打量那所监狱,好像这是他们想买的一块地产似的,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格雷特豪斯目光炯炯,烟斗学着鸟叫。他很可能以为自己是个硬汉子。我后来从他的律师那里得知,他一知道自己真的要下狱以后,便学了拳击、柔术、空手等卫身手段。
我听了后就对自己说:“那个监狱里可没有什么人想同他打架,不过他的脊梁骨还是要给打断的。无论谁头一次蹲监牢,脊梁骨都会被打断的,过一阵子就会好的,但总是与以前不同了。维吉尔·格雷特豪斯再硬,走路和感觉也不会如从前了。”
维吉尔·格雷特豪斯没有认出我来。我坐在那里很可能就像泥地里或战场上的一具死尸,而他则是个将军,在战火稍息的当儿前来观察一下前线的大体情况。
我并不感到奇怪。不过我觉得他一定能听得出监狱里传出来的声音,这声音我们在外面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这是他在“水门事件”中最亲密的合谋者爱弥尔·拉金的声音,他这会儿正拉开嗓门在唱黑人赞美诗“有时候我觉得像个没有母亲的孤儿”。
格雷特豪斯还没有对这声音反应过来,附近跑道尽头就有一架战斗机凌空而起,在空中呼啸而过。以前没有听到过这声音的人听起来,这声音真叫人胆战心惊。它突如其来,毫无预告,头顶上总是发出一种世界末日般的爆炸声。
格雷特豪斯、两个律师,还有那个司机都马上趴在地上。待发现是怎么一回事后,他们就爬了起来,一边掸土,一边骂着、笑着。格雷特豪斯估计——也的确如此——有人在见不到的地方看到他出洋相,就做了几个拳击的动作,抬头看着天空,仿佛开玩笑地说:“再来啊,老子这回有准备了。”不过这一行人并没有朝监狱走去,站在车边像是在等欢迎的人似的。我揣想,格雷特豪斯大概是想在中立地带得到对他的社会地位的最后一次承认,就像南军在阿波马托克斯[4]投降那样,这次是监狱长当修斯·S·格兰特,他当罗伯特·E·李。
但是监狱长压根儿不在佐治亚州。要是他早得到通知,知道这一次格雷特豪斯要来投案,他就会到场的。但是他如今在亚特兰大市,出席美国假释官员协会的年会,并要在会上发言。因此由与卡特总统长得一模一样的克莱德负责这件事。克莱德从大门口出来几步,挥手叫他们过去。
克莱德笑容可掬地说:“请你们都进来。”
他们就进去了,司机走在最后,提着两只皮箱和与之相配的盥洗包。克莱德在门口把他手中的箱子接过去,很客气地请他回到车上去。
“这儿没有你的事了。”克莱德说。
于是司机回到汽车里。他的名字叫克利夫兰·劳伊斯,同我毁了的那个人的姓名莱兰·克留斯很难分辨。他只受过小学教育,但在车上等人时一天能看完五本书,要等的人大多数是拉姆杰克集团的巨头,或者是该公司的主顾。他在朝鲜战争中曾被中国人俘虏,还真的到过中国,在黄海的近海船上做过水手,因此中国话说的相当流畅。
克利夫兰·劳伊斯如今在看《古拉格群岛》,这是另一个蹲过监牢的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津对苏联监狱制度的一本记述。
这样就留下我独个儿坐在长凳上,不知身在何处了。我又犯了紧张症[5]——直瞪瞪地看着正前方,过一阵子就举起我苍老的手连击三下。
后来克利夫兰·劳伊斯告诉我,要不是那三击掌,他是不会注意到我的。
是我的三击掌引起了他的好奇,他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他问我能把三击掌的原因告诉他吗?不。这话说起来太长,听起来太无聊。我只告诉他我在对过去做白日梦,凡是记起过去特别高兴的事,我就举手拍三下。
他表示愿意让我搭车去亚特兰大。
于是我获得自由才半小时就坐上了一辆豪华轿车的前座。这个开头还挺顺利。
要是克利夫兰·劳伊斯不请我坐他的车子去亚特兰大,他就永远当不了今天的拉姆杰克集团交通部的人事主任。交通部掌管着遍布自由世界豪华长轿车业务,出租车队,租车代理和停车场。你甚至可以从交通部租家具。有人就这样做。
我问他,他的客人对我搭车去亚特兰大会不会有意见。
他说他以前并不认识他们,以后也不想再见到他们,他们不是拉姆杰克集团的人。他还调皮地加了一句,他到了这里才知道主要乘客是维吉尔·格雷特豪斯。在这以前,格雷特豪斯用了假胡须。
我弯过脖子想看一下后座,假胡须就在那里,一只耳套挂在车门把上。
克利夫兰讲笑话说,格雷特豪斯的两位律师恐怕不一定会出来。“瞧他们打量那监狱的样子,”他说,“我觉得他们仿佛是在试尺寸。”
他问我以前坐过这样的高级轿车没有。为了省得麻烦,我说“没有”。我小时候当然常常坐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麦康的各种高级轿车前座我父亲的身边。年轻的时候,我还没有上哈佛,已坐在后座麦康先生的身边,有玻璃把我和前座的父亲隔开。当时我并不觉得这样隔开有什么奇怪或者暗示着什么。
在纽伦堡的时候,我又是那辆默塞德斯轿车的主人。不过那是一辆敞篷车,即使车后盖和后窗上没有弹孔也已够邪气的了。在巴伐利亚人的眼中,这辆车给我的社会身份同海盗一样——暂时占有着一件一定会一再易手的赃物的主人。不过,在监狱外面坐进高级轿车中以后,我忽然想起我已有快四十五年没有坐这种车子了!尽管我在政府中地位升迁很快,可从来没有专用车,在三次升迁中自己从来没有购置过一辆,甚至偶尔用一次也没有过。我也没有讨得上司如此欢心,使他对我说,“年轻人——这个问题我还想同你谈一谈,上我的车吧。”
而莱兰·克留斯虽然没有自己的车,却常常坐在对他表示青睐的老头儿的车里。
没关系。
要心平气和。
克利夫兰·劳伊斯说,他觉得我说话像个受过教育的人。
我承认上过哈佛大学。
他告诉我他在朝鲜当过中共的俘虏,因为主管他所在俘虏营的中国少校也是哈佛大学出身。那位少校大概与我同样年龄,甚至可能与我同一届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同中国同学交过朋友,据劳伊斯说,他念的是物理和数学,因此我是不可能认识他的。
这个哈佛大学出身的中国人同克利夫兰·劳伊斯交了朋友,战争结束后劝他去中国,别回佐治亚。劳伊斯小的时候,他的一个表哥曾经被一批暴民活活烧死,他的父亲有一天晚上被三K党[6]拉出去用鞭子抽打,他本人因两次去投票站登记而挨了揍,那是被征当兵之前。因此他很想过那种和平安宁的生活。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他在黄海上当了两年水手。他说他爱过几次人,但没有人爱他。
“那么是什么把你送回来的?”我问。
他说是教堂音乐,不是别的。“那里没有人同你一起唱。”他说。
“还有吃的东西。”他说。
“吃的不好?”我说。
“吃的不坏,”他说,“可是说起来没劲。”
“怎么?”我说。
“你不能光吃,”他说,“你还得说说吃的,你得同懂得那样吃的人说说吃的。”
我祝贺他学会了中国话,他答道他现在绝不会再这么做了。“我现在懂了,”他说,“我当时太无知,不懂得学中国话有多难。我以为是像学小鸟唱歌一样。你知道,你听到一只小鸟吱地一叫,你就学它的叫声,看你蒙得过它蒙不过它。”
他决心要回国时,中国人并没有难为他。他们很喜欢他,他们还想办法通过迂回的外交途径打听他回国后会受到什么对待。当时美国在中国没有代表,它的一些盟国也没有。信息是通过莫斯科转达的,当时它还同中国保持友好。
是啊,这个黑人前一等兵在军事上的专长不过是为重迫击炮搬炮架,结果却惊动了最高级的外交官为他进行谈判。美国人要把他弄回来,目的是要惩罚他。中国人说惩罚是可以的,但时间要短,仅仅是象征性的。马上要让他恢复普通平民生活,否则他们就不让他回国。
美国人说,要求劳伊斯作某种公开的解释,说明他为什么回国。然后要对他进行军事审判,处以三年以下的徒刑,开除军籍,取消一切积欠薪饷和补贴。中国人说,劳伊斯已保证决不发表任何不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言论,因为中国待他很好。要是强迫他违反保证,他们就不让他回国。他们还坚持不能判他任何期限的徒刑,他在当俘虏期间积欠的薪饷都要发还给他。美国人答称,得关他一阵子,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不能让逃兵不受惩罚。他们可以在审前关押他,判以他同做俘虏相等时间的徒刑,然后这次判刑的时间与他被俘虏的服刑时间相抵,最后放他回家。发还积欠薪饷是谈不上的。
谈判结果就是这样。
“你知道,他们要我回国,”他对我说,“因为他们很尴尬。哪怕只有一个美国人,哪怕他是黑人,哪怕他有一分钟认为美国也许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他们也不允许。”
我问他有没有听说过鲍伯·范德医生的事,那位医生在朝鲜战争中被判叛国罪,如今就在监狱里面为维吉尔·格雷特豪斯量身材,好发囚衣给他。
“没有,”他说,“我从来不管别人的事。我从来不认为这种事像上什么俱乐部似的。”
我问他有没有见过神话般的人物,拉姆杰克集团最大的股东小杰克·格拉汉姆太太。
“这等于是问我见过上帝没有。”他说。
那时格拉汉姆寡妇已有五年不公开露面了。她最近一次露面是在纽约市的一个法庭上,因为有一批股东控告拉姆杰克集团,要它证明她仍活着。我记得报上的内容让我妻子感到很有意思。“这就是我喜欢的美国,”她说,“为什么不能一直是这样?”
格拉汉姆太太没有带律师就上了法庭,却带了八个穿制服的保镖,那是她从拉姆杰克一家子公司平克顿侦探事务所要来的。其中一个手上拿着一只话筒和扩音器。格拉汉姆太太披了一件宽敞的大黑袍,头上蒙了头罩,前面用别针别住,这样她可以从里面看外面,别人却不能从外面看进去。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有她的手。另外一个平克顿侦探带着印台、纸张,还有从联邦调查局取来的她的指纹样。一千九百五十二年她丈夫死后不久,她因在肯塔基州佛兰克福[7]酒醉开车被捕,就留下了指纹样,送到了联邦调查局。当时她暂时释放,以观后效。我自己当时也刚被政府辞退。
扩音器给按上了,话筒塞进了她的头罩,这样大家就可以听见她说些什么。她当场按了手印,让他们把她的手印同联邦调查局的指纹样核对,证明她就是她自称的那一个人。然后她经过宣誓声称自己身心健康,能够统辖公司的高级负责人,但从来不是面对面的。她用电话给他们发指示,用一句暗号表明自己的身份。暗号不定期更换。我记得当时在法官的要求下,她举出了一个例子,这句暗号充满了魔力,使我至今犹牢记不忘。这就是:“鞋匠”。她通过电话下达的指示后来都有她亲笔信证实。每封信的末尾不仅有她的签名还有她八个小手指和两个大拇指全套的手印。她叫作:“我小小的八个手指和小小的两个拇指。”
这就够了。格拉汉姆太太肯定还活着,如今她又可以自由自在地销声匿迹了。
“我多次见到过李恩先生。”克利夫兰·劳伊斯说。他指的是拉姆杰克集团董事会主席和总裁阿尔巴德·李恩先生,他是个十分爱抛头露面和发表意见的人。后来我和克利夫兰·劳伊斯两人都当上了拉姆杰克集团的高级职员时,他就成了我们上司的上司。我现在可以说,阿尔巴德·李恩是我有幸能为之效劳的最能干、最懂行、最杰出、最知人善任的上司。他是个善于收购其他公司,并且防止它们倒闭的天才。
他常说:“你同我再合不来,那就没有人能合得来了。”
这话不假,一点不假。
劳伊斯说,阿尔巴德·李恩两个月前才来过亚特兰大,坐过他的汽车。因为亚特兰大有一些新开张的铺子和豪华酒店破了产,李恩想为拉姆杰克集团把它们买下来。可是,南朝鲜的一个宗教团体出价比他高,抢了先。
劳伊斯问我有没有子女。我说我有个儿子在《纽约时报》工作。劳伊斯听了笑道,他和我的儿子如今都是一个老板:阿尔巴德·李恩。原来我错过了那天早上的新闻广播,因此他得向我解释,拉姆杰克集团刚刚收购了《纽约时报》及其所属机构的控制权,包括其下属的世界上第二大猫食公司。
“李恩先生在这里的时候,”劳伊斯说,“他就告诉我会发生这件事。他要的是猫食公司,不是《纽约时报》。”
两位律师爬进了汽车的后座。他们一点也不安静。他们在笑那个像美国总统的狱卒。一个说:“我真想对他说:‘总统先生,您为什么不就在这里马上宣布赦免他?他已吃够了苦,(您现在放了他,)他今天下午还来得及去打高尔夫球。’”
一个试了试假胡须,另一个说他像卡尔·马克思。如此等等。他们对我一点也不在意。克利夫兰·劳伊斯告诉他们,我是来探望我儿子的。他们问我,我的儿子为什么入狱,我说:“邮件诈骗。”谈话就到此结束。
我们就这样去了亚特兰大。我记得,我面前的放手套的小翻屉上有一个用吸盘吸住的奇怪的东西。从吸盘那里伸出来一根一尺长的绿色浇水皮管似的东西,正对着我的胸口,那东西头上是一只白色的塑料盘子,有菜盘那样大。我们的车子一开动,盘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它随着车的颠簸而上下,随车的拐弯而左右。
因此我就问这是什么。原来这是个玩具方向盘。劳伊斯有个七岁的儿子,有时跟他一起出差,小孩子就用这只塑料方向盘假装开汽车。我自己的儿子小时候没有这种玩具。不过话说回来,他也不见得喜欢这种游戏。小瓦尔特七岁的时候就不愿同父母一起出去了。
我说这个玩具设计得很妙。
劳伊斯说,这个玩具可能很惊险刺激,特别是如果掌握真正方向盘的人喝醉了酒,险些同迎面来的卡车相撞,或者刚刚擦过停着的汽车等等。他说应该在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上送他一个这样的方向盘,让他和大家都知道,他能做的事也就是假装掌握方向盘而已。
他在机场让我下了车。
去纽约的飞机都满座了,我到那天下午五点才离开亚特兰大。我倒无所谓。我没有胃口,就没有吃中饭。我在厕所捡了一本平装本的书,读了一会儿。这是一个关于心狠手辣的人成为国际大公司首脑的故事。女人们都倾心于他。虽然他完全不把她们放在眼里,可是她们仍围着他转。他的儿子是个吸毒犯,而女儿是个花痴。
我看书的时候被一个法国人打断过一次,他对我说法语,指指我的左边衣领。我开始以为又把衣服烧了窟窿,尽管我已不抽烟了。后来我才明白,我仍佩着那条窄窄的红绸带,表明我是法兰西荣誉团的一位武士。可悲的是,在整个审讯期间我都佩着它,进牢去的路上也佩着。
我用英语告诉他,这是同旧衣服一起买来的,我不知道它标志着什么。
他的态度马上冷淡起来。“请允许我,先生[8]。”他说,一把就把绶章从我的衣领上扯下来,好像那是只小虫似的。
“谢谢[9]。”我说,又回过头来看书。
最后飞机上终于有了一个空座,扩音器上广播了我几次:“瓦尔特·F·斯代布克先生,瓦尔特·F·斯代布克先生……”这个名字一度臭名远扬,但是如今我看不到有人露出似曾相识的表情,也没有人扬起眉毛来想一想这是谁。
两个小时以后,我就在曼哈顿岛上了,穿着军用雨衣抵御夜晚的寒气。太阳已下山。我呆呆地望着一家玩具火车专卖店的展示橱窗。
我并不是没有地方可去。我已走近要去的地方。我事先写了信,订了一个没有洗澡间和电视的房间,为期一周,预付房钱——那是以前一度很时髦的阿拉巴霍酒店,现在却是距时代广场只有一箭之遥的一家下等旅馆了。
注释:
[1]卡迪拉克(Cadillac):现译作凯迪拉克。
[2]F.M.S.A.C.F:“联邦最低限度安保措施成人改造所”(Federal Minimum Security Adult Correctional Facility)的英文缩写。
[3]华道夫酒店塔楼(Waldorf Towers):指的是“纽约第一酒店”华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Astoria Hotel)(现译作华尔道夫酒店)28层以上、专门用于接待国家元首和政要的部分,塔楼里全部是豪华套间和公寓。该酒店于1893年由威廉·华尔道夫·阿斯特(William Waldorf Astor)建造,是见证美国历史的重要地标之一。
[4]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美国南北战争末期,南方联盟总司令罗伯特·E·李(Robert Edward Lee,1807-1870)深感没有取胜的希望,为了减少民众和士兵的进一步伤亡,决定投降,率领部众,前往阿波马托克斯镇,会见联邦军总司令修斯·S·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签署了有关投降的事宜。但提出条件,败军不受辱,必须充分保证南军将士的人格和尊严不受侵犯。格兰特将军接受了它。
[5]紧张症(catatonia):(医学)具有紧张症特征的,尤指四肢的极端僵硬或松弛的病症。
[6]三K党(Ku Klux Klan):是美国历史上和现在的一个奉行白人至上和歧视有色族裔主义运动的民间排外团体,也是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组织。
[7]佛兰克福(Frankfort):现译作法兰克福。
[8]原文是法语“Permettez-moi,monsieur”。
[9]原文是法语“Mer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