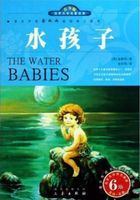大妹的床跟大妹一样,软绵绵的,还带着棉花、草垛的气息。郝彪一躺下去,就睡着了。半夜醒来,不停地用大搪瓷缸喝水,跑厕所,呕吐、拉肚子,还出了很多汗,被子和褥子差不多湿透了。第二天常好上楼,拿凉手试了他的额头、脖子、肩膀,说烧退了。但郝彪依然一点气力都没有。入狱四年七个月,他从未因病倒过床,今天这一病,算是把错过的病都一齐发作了。常好叮嘱他多躺,他就躺着,每天喝几口米汤。
躺到第三天早晨,他听到雨淋在泡桐叶上,淅淅沥沥,煞是好听。到了近午,雨声没了,顾客还没开始上门,安静中听到自行车脚架啪地一响。他心里一动,撑起身子从窗口往下瞄,看见邮车正停在两棵泡桐下,带着雨水,油绿得好看。他脑子一松,感觉病轻了好多。
几分钟后,也许没有几分种,又是啪地一响,自行车走了。
他吁口气,心里忽然有点空空的,就瞪着天花板发呆。天花板上贴满明星海报,是大妹的最爱,个个皮包骨头,灯泡大眼睛,活脱脱女鬼,却印着“窈窕淑女”四个字,他看着看着,就笑了。就在这时,大妹端了盘碧绿的馍馍走进来。
“梯梯的妈妈来谢你。可惜,常姐说你病了,没让她上楼……你就这么高兴吗?”
郝彪赶紧把笑收了:“啥?”
“清明花粑粑,她为你做的。她还说,梯梯很想你。”
“她说?”
“当然,她没法说,”大妹递给他一张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的,上边写着三行工整的铅笔字:
叔叔,谢谢您。
我请妈妈给您做了清明花baba,很好吃。
您要多吃些。
缅小梯
郝彪有一点发蒙:“缅小梯?”
大妹说:“缅小梯就是梯梯嘛。”
“可是,他应该姓常……”
“吃自己的饭,管人家的事!”大妹夹了一块粑粑,塞进郝彪嘴里,把他的话堵回去。
郝彪慢慢地嚼着花粑粑。花粑粑的原料是糯米,馅里有切碎的冬菜和腊肉,味道醇厚、油腻,又带着淡淡的清香。他能吃出来,这清香是因为糯米中掺了磨细的艾蒿。他不晓得大足把艾蒿叫什么,但他小时候吃过母亲做的艾蒿馍,味道还记得。那时候母亲还不是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她的嘴角有忧劳,但还有红润与微笑。她在靠近宽巷子的三洞桥摘艾蒿,把艾蒿放入摊开的手帕中。他好多年没吃过这种馍馍了,不光是河水脏了,摘不到干净的野菜了,是因为他像条野狗,疯窜了好多年。咋会想到呢,好多年之后,流窜到大足,还能吃到改头换面叫做“花粑粑”的成都馍。他就这么一直吃着,心里念着,把一大盘的花粑粑全吃了。
〇一六
鲫鱼馆隔壁是家杂货店,生意不死不活。常好过了清明,就把杂货店盘过来,请了施工队,打通墙壁,重新装修,店堂扩大近一倍。周六,趁馆子暂时歇业,她回宝顶看望父母亲。郝彪问,他能不能同去呢?
常好看着刘建设:“郝彪也要去孝敬我父母,你说行不行?”
刘建设不说行不行,只是朗声说:“我也要去孝敬老人家。”
郝彪喃喃说:“我是去看小梯梯。”
但常好似乎没听见。早晨吃过稀饭、包子,三个人搭公交车往宝顶而去。郝彪腿上放了一把塑料机关枪,是送给梯梯的礼物。汽车爬上宝顶山,挡风玻璃粘上些细雨珠。庄稼地和果园舒缓起伏,郝彪看在眼里,说不出地安逸。
宝顶过了香会,四下都很安静。圣寿寺山门外黄桷大树下,几个老汉叼着两尺长的烟杆在摆龙门阵。圣迹池水波不兴,绕过池子,有一片桃林,一堵青砖照壁,与圣寿寺隔水相望,气象阔大。再从照壁前绕过去,就是宝顶镇的老街了。街上多是木板屋、带阁楼,一条石板路。常好走在前边,走了几步猫步,回头挤眉一笑,野辣辣的风情,把刘建设看得噼啪鼓掌。常好把笑收了,站在小小的邮政所门外,指了指前边,冷脸对着郝彪:“我到了。你拐弯过去就是梯梯家,门外堆着烂砖头。”
然而不是烂砖头,是青石、砂石,大小不等,都均匀地贴墙码着,就像墙外有墙,十分好看。墙是老旧的木板,擦得干干净净,见出一波一波的木纹,上面还留着“文革”时的毛主席语录,大多模糊了。郝彪歪头看了半天,只辨出三个字:“要团结。”他咧嘴笑笑,又吸口气,稳了稳神,轻轻敲门。
门立刻就开了,门口站着梯梯。梯梯有点发愣,小脸红红的,竟忘了招呼客人。郝彪也有点紧张,默然相对一刻,他把机关枪对着梯梯:“缴枪不杀!”
梯梯咯咯笑起来:“枪在你手上啊,叔叔。”
郝彪就把枪塞到他手上:“现在是你的了。”
梯梯抱着枪有点不知所措:“真可以打子弹吗?”
“它打水。”
梯梯好像突然醒过来:“谢谢叔叔,叔叔请进。”
郝彪跨进去,屋里光线暗了一暗,外间本已很小,多了他显得更加局促。然而四壁雪白,墙上一面镜子,中央一张餐桌,摆了梯梯的课本,还有一只青花磁盘,盘中摊了一圈新摘的黄桷兰,香味甜丝丝,微微腻人。
“妈妈呢?”
“加班。”
“就你一个人?”
“还有外婆,买菜去了。”
“谢谢梯梯,清明花粑粑很好吃。”
“是妈妈做的。”
“妈妈真听你的话。”
“我也听妈妈的话。”
“是好儿子,都听妈妈的话。”
梯梯埋头看着自己的手,看了半天:“我太听妈妈的话了……”
郝彪笑起来:“不好吗?”
一滴泪水落在梯梯的手背上:“连女同学也笑话我,说我不是男娃娃。”
“笑就笑,怕什么?”
“香会那天晚上,几个男生跟我打赌,问我敢不敢走丢了都不喊妈妈。我说敢。他们就把我带到倒塔去,一下子都跑光了。”
“倒塔?”
“就是你和妈妈找到我的那地方。”
“他们经常欺负你?”
“嗯。”
“那你咋办?”
“不晓得。”
“他们再欺负你,你就该抓一块砖头、一把刀,跟他们打,不要命地打,他们就再不敢打你了!”但他没有这样说。他把“你就该……”后边的话都吞回去。他这样说:“他们再欺负你,你就找叔叔。”
梯梯抬起头,看着郝彪。郝彪看见他眼里水汪汪的。他说:“叔叔,我到哪儿找你?”
郝彪叹口气,把拳头捏紧了,说:“你把拳头练硬了,他们就不敢碰你的拳头了。”
梯梯也捏了拳头,一下子砸在郝彪的拳头上,痛得嘴都歪了。郝彪嘿嘿笑起来,问梯梯几岁了?梯梯说,七岁。郝彪说,好,七岁的男子汉。说着,伸手在梯梯的腋下一叉,就把他叉起来,像甩印度飞饼一样,把他上上下下甩了十几遍。梯梯又乐又怕,嘎嘎怪叫。突然,他的手扫着墙上挂的一个小东西,小东西斜着飞出去。
梯梯尖叫了一声!郝彪搂紧他,躬身一捞,竟在空中把小东西捞了起来。
是一尊小小的木雕:一个女人的头像,头微微抬起,脸颊丰满,五官精细。郝彪一眼就认出,这是缅忆君。不过,他还是头一回看见,缅忆君的视线是这样向上的,仿佛前边有一束光打来,她的眼虚着,而嘴角弯弯,漾着淡淡的笑意。
“是你妈妈。”
“不是我妈妈。”
“是你妈妈啊。”
“是观音。”
郝彪叹口气:“你妈妈,这么像观音……”
梯梯咯咯笑起来:“妈妈说,她是打石头、捏泥巴的维修工。”
“你见过有妈妈这么漂亮的维修工?”
“妈妈说,姑姑才漂亮。”
“为什么?”
“妈妈说,姑姑是窈——窕——淑——女。”
郝彪想起常好撑杆一跳的样子,嘿嘿笑起来。这时候门开了,刘建设进来传常好的话:请梯梯和外婆,也捎带郝彪,过常家吃午饭。
〇一七
常好从宝顶带回一包葵瓜子。她精选了一小把,其余都丢给了郝彪。郝彪嗑了几颗,喃喃说:“生的,没炒过。”常好说:“生的好,不上火。”
她把选出的瓜子,亲手种在后院里,早晚浇水。过些天,向日葵的种子发了芽,钻出土来,水汽饱满的,也是羞答答的。常好看了,脸上是藏不住的欢喜。刘建设嘟囔:“老板,你还缺几颗瓜子钱?”常好说:“你不懂。”
好妹仔鲫鱼馆店堂大了,四壁粉新,左右的小店凑份子送了几只花篮,“快刀卢”的卢老板还送了一尊财神和两支电红烛。常好不好拂卢老板的好意,把财神供上了神龛。她把自己跳高的塑像拿下来,问大伙儿:“哪个愿帮我保管呢?”
大伙儿愣了片刻,还没回过神,她又说:“都不愿意嗦?没心肝。那就郝彪吧,你资历最浅,多做点杂活。”说着,就把塑像递了过去。
大伙儿面面相觑,刘建设脸上很不好看。大妹说:“好姐姐偏心,啷个不给刘大哥?”刘建设忽然嘿嘿笑起来,解嘲道:“给我,我还不要呢,不就一坨泥巴嘛。我要,就要……”
大妹问:“要什么?”
刘建设咽了咽唾沫,说:“我不说。”
可郝彪拿着塑像,就像拿着烫手的山芋,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常好大怒,喝道:“你怕脏了你的手?”
郝彪涨红了脸,就停了手,盯着塑像看。看到眼角那块疤,禁不住拿手指摸了摸,喃喃说:“何必呢,连块疤也不放过。”
常好的脸也微微一红,似乎郝彪的手指就摸在她脸上。她说:“既然是我,就要一丝一毫都像我。——是我喊她一定要刻的。”
“她是谁?”
“缅忆君。”
郝彪吃了一惊:“梯梯的妈妈?不是维修工吗,她还会雕塑?”
常好冷笑:“你又在装哈了,成都人都这副德行?你不是从前就认识她了吗。”
郝彪闷了半晌,喃喃道:“不是认识,是见过。”
常好把自己的塑像从郝彪手里拿回来,若无其事地放回壁龛,和财神菩萨挤一堆,随口说:“哦,是见过,过目不忘的一面吧?”
郝彪从口袋里掏出钱夹子,从钱夹子里拈出张邮票,递到常好的眼皮下。大伙儿都把头凑过来。
刘建设骂起来:“你以为我们瞎了眼!明明是日月观音嘛。”
常好吁了一口气:“是的,是她。这么多年了,我们就没看出来,她像她……”
郝彪说:“你,是不是不喜欢她?”
常好露出吃惊的表情:“我为啥不喜欢她?我把她当嫂子。”
“那,梯梯是不是你哥哥的儿子?”
“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跟我都没关系。”
大妹说:“你可以讲给我们听听嘛。”
“我可以讲。可我为什么要讲呢?”
刘建设说:“不讲就算了。要讲,我们也都愿意听。”
常好目光扫了一圈,她的人都静静看着她,等着听她说。她默然一会儿,又侧脸看了看门外:一地阳光,大团树荫,风吹着泡桐叶,发出密雨一样好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