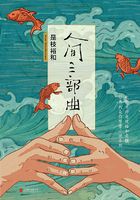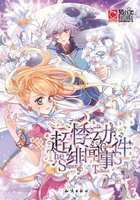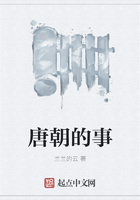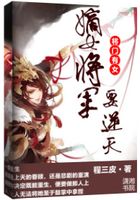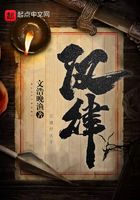第六节 圣寿寺
〇一八
常好从记事起,宝顶镇的小街上,就有了缅忆君。缅忆君是常家的常客,常好曾叫她“君姐姐”,她则叫常好的哥哥是“大哥哥”。当然,她不说话,她用的是眼神、微笑、铅笔写下的工整的字迹。
然而,缅忆君不是一出世就发不出声音的。
忆君的父亲缅青山,是大足石刻文物管理所的维修工,每天去大佛湾上班。缅家五代银匠,祖居重庆下半城的白象街,有一爿小小的银饰店。抗战中,银饰店被日本飞机炸没了,祖父也被炸死了,祖母就带着他父亲回了大足宝顶的娘家。青山是银匠之后,手巧得很,做什么活都细致、有耐性,被文管所的老所长相中,高中一毕业就招进去维修文物。老所长智慧、仁慈,教导青年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石刻,要像做眼科手术一样维修石刻。”青山说:“我懂了。”
他不负老所长期望,工作十年,就评了高级技师。
青山的妻子甘敬慈,在玉龙山林场做会计,周末才搭班车回家。她是个白净的女子,头发在脑后绾成乌亮的发髻,插一把丈夫亲手为她打的银簪子,随身带一只慈竹编的菜篮,回家总盛满山货,让丈夫尝一口鲜,譬如木耳、黄花、竹笋、樱桃、杏子、白果、猕猴桃……有一回,是只叽叽叫的鸟,青山见着眼生。“啥雀雀呢?”
“是伯劳。我不在,她好陪你啊。”
“放了吧。劳燕分飞,说的就是她跟燕子啊。别作孽。”
敬慈撅着嘴,舍不得。青山就把伯劳双手捧了,在屋檐下轻轻一托,伯劳扑扑地钻到天上,眨眼就飞没了。
有一年春天,青山应邀去昆明邛竹寺交流佛像修复术。回家时带回一棵小树苗,亲手栽在后院里,又浇水,又修剪枝叶。敬慈说:“这不就是黄桷兰吗?重庆、大足多得是,还值得千里驮宝贝一样驮回来?”
青山说:“是黄桷兰,可是在云南,她就不是黄桷兰。她跟我同姓呢。”
敬慈反应不过来:“姓什么?”
“姓缅啊,”青山呵呵笑,“在云南,人人都叫她缅桂花。好听不好听?”
“好听,再好听,缅桂花还是黄桷兰……”敬慈嘀咕,“有你这样的憨子、迂夫子、老实人?”
青山夹一筷子妻子炒的竹笋,呷一口江津老白干,笑眯眯。“老实人好,老实人不吃亏。”
敬慈也笑。丈夫笑了,她如何不笑?入了夏,缅桂花开出一朵朵瘦长的、淡黄的花,香气扑鼻,香得人心乱。敬慈周末回家,摘十几朵花,摊入青瓷盘,摆成一圈,搁上床头柜。夫妻十年,周末总像新婚。屋里还沆瀣着花香和酒味,饭桌上碗筷还没有收拾,敬慈就拔了头上的银簪,两口儿在床上绞成一团。两口儿都在盛年,身子硬朗,有的是气力。这床是老楠木打的,够沉,够结实,也被折腾得如牛马般呼呼喘气。
但折腾了十年,敬慈的肚子也没能挺起来。邻居老常,结婚比他们还晚几年,娶新娘的时候在门上、铺板上油了绿漆,次年就生了个儿子。现在绿漆都斑驳了,儿子都满地乱跑了,缅家的儿子还没影子。两口儿去大足医院、重庆医学院都检查了,结果是没问题。然而,肚子就是不结果。
敬慈跟丈夫商量:“要不,我们去抱一个?”
青山摇头:“不着急。”
他是大佛湾里最优秀的维修工,佛身爬了蕨草、青苔,他用竹片小心翼翼地刮,一个星期,也就刮干净一只佛指甲。玉龙山的杜鹃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过了两遍寒暑,他也未必能把一只洞窟,譬如圆觉洞的三身佛、十二菩萨像都清理出一遍。没有耐心,他吃不下这碗饭。
深秋天,大佛湾的枫叶红了,黄桷树黄了,衬托得万尊石像格外地庄严。央视专程来大佛湾做节目,摄像机把佛、菩萨、神仙、鬼怪、所长、副所长都扫了遍,最后却突然把话筒伸到了缅青山的嘴边。
女主持人做出诚恳幼稚状:“请问缅师傅,这么多年了,是什么精神支撑您坚持着、守望着这份默默无闻而又枯燥乏味的工作呢?”
青山摇头:“没什么精神。”
女主持人把头微微一歪,撅嘴微笑:“为什么呢?”
“与佛为邻,三生有幸。”
女主持人对着摄像机镜头朗诵道:“三生,就是三辈子的意思吧。看来,缅师傅是维修工世家的第三代传人了。那么,请问缅师傅,您的孩子,是不是也打算接您的班,世世代代把咱大足石刻、国之瑰宝维修下去呢?”她的“呢”拖得很长,像一把弯曲的镰刀。
青山的脸沉下来,默然片刻。“当然不。”
女主持瞟着镜头,嗲道:“为什么呢?”
青山掉身就走了。
电视节目播映时,这段对话被删得干干净净的。但这段对话却传了出去,不少人夸缅青山“有脾气”。就连来大佛湾视察的县长也风闻了,他跟老所长说:“啥子脾气?把媒体都得罪了,你还想不想搞旅游?”
老所长说:“不是脾气,是他根本就没孩子,说什么‘世世代代’呢?哪壶不开提哪壶。”
县长皱了眉:“还没孩子?那就赶紧嘛。”
老所长苦笑:“这种事,能赶紧吗?”
缅青山发了脾气,回家闷闷的,喝了一周的江津老白干,还上老常家喝了一次。老常的儿子常大路,踮着脚尖给他斟酒,他摸着常大路的头,差点落了泪珠子。老常叹口气,说:“不嫌我们大路丑,就让他给你当个干儿吧。”
青山说:“可我爹从小跟我说,地要深耕,儿要亲生。就算有了干儿,我还想要一个亲儿。”
老常说不出话,只能再叹口气,陪他把一瓶白干都喝了。
甘敬慈周末回来,一边收拾乱七八糟的屋子,一边又嘀咕要抱养孩子。青山口齿都被白干僵住了,但还能清楚地吐出一个字:“不。”
冬天随后就来了,落叶拍窗,北风飕飕地吹,缅家后院的缅桂花,被小心翼翼地覆了层塑料膜。老常早晨下乡送邮件,满脸披霜,晚上回来,鞋子、裤头全是露。
寒露那天,甘敬慈从山上赶回家,在后院点冬菜子,累得腰酸背痛。缅青山在一边歇着,小口呷酒,就是不帮她。她也不埋怨,只叹气。“要是屁股后跟着个娃儿,替我撒种子,多好。”
〇一九
元旦头一天,宝顶山飘雨夹雪。镇上人只习惯过旧历年,这一天反倒关门闭户,四下阒然,只远远从圣寿寺传来一两声钟磬声。
缅家生了一炉火,两口子围炉坐到下午。敬慈说:“我晓得你不信佛。可事到如今,不信也当是信了。我们去给观音菩萨烧一炷香吧,求她保佑我们有一个儿子。”
青山摇头:“佛和菩萨是什么做的,我还不清楚?石头和泥巴。我每天去大佛湾做啥,不就是修补石头、泥巴吗?就算我信吧,我天天去伺候他们,他们要给我儿子,早就该给了。”
敬慈叹气,央求他:“去嘛。回来我给你炒豆豉、蒜薹、回锅肉,再奖一瓶江津老白干。”
青山哼一声,坐着不动。敬慈就用手捧了脸,呜呜哭起来,泪珠子从指缝间淌出来,落到火炉上,伤心地噗噗响。青山心痛了,说:“走吧。”
圣寿寺冷冷清清的,山门虚掩,没一个香客。梯槛湿漉漉,粘满了落叶。
寺里僧人,缅青山都认识,但也都很泛泛,只跟一个劈柴、升炉子、烧开水、蒸馒头的老和尚比较熟,他曾请青山替自己打磨过手铲和刮片。这老和尚俗家姓何,川北阆中千佛乡人,七岁由大舅送来宝顶出家,“文革”时被迫还俗,浪迹川东、鄂、湘、黔,替人看相、算命,也砌墙、起灶、修锅补碗、打铁、打家具,论十指之巧,不输于青山。他十年前回到圣寿寺,长眉毛已然花白。青山敬重他,偶尔会送他一包敬慈带回的山货。他称他“老师傅”,他叫他“缅师傅”。两个师傅之间,却从不说佛谈禅的。
只有一回似乎是例外。暮色里,青山替老和尚劈一只黄桷树疙瘩,瞥见墙上抄写的禅诗“菩提本无树……”,随口打了个哈哈:“菩提到底是树不是树?说不是树嘛,佛祖不就在菩提树下觉悟的?说是树嘛,我倒硬没在圣寿寺见到过一棵菩提。”
老和尚也呵呵笑了笑:“缅师傅,你是见过的。”
“我见过?”
“菩提即是烦恼。你还愁见不到?”
青山听得似懂非懂的。但他的烦恼他清楚,那就是没儿子。
这一次两口儿来烧香,倒没想要跟老和尚请教些什么。登上维摩顶,穿过两棵擎天柱般的黄樱树,却正见着老和尚在躬身拾落叶。
老和尚合掌,招呼他:“缅师傅。”
青山还礼:“老师傅。”
老和尚笑眯眯:“是拜佛求子?”
青山红了脸,有些忸怩,还是点了头:“她硬拉我来的……”
老和尚又笑笑:“我活一辈子,没见过不求人的人。万事不求人,岂不自家把自家将死了?再硬的汉子,也有翻不过的坎。就算万事不求人,总还跟爹娘、兄弟、姊妹开过口的吧?你跟佛祖、菩萨开一次口,也是一回事。”
敬慈拿拳捶丈夫的肩膀:“听懂了?是一回事。”
维摩殿里,两口子烧了三炷香。敬慈还按着丈夫的脑袋,让他跪在蒲团上磕了三个头。烛光影里,一个打瞌睡的小和尚啵地敲了一声钟。
下梯槛时,敬慈吊着丈夫的手臂,却黯黯的,一点气力都没有。跨出山门,风卷着雪花、雨沫子,从圣迹池上吹来,扑扑打在他们的脸上。敬慈把头埋在丈夫怀里,喃喃说:
“青山、青山,你说说,我们是好人,为什么好人就没有好报呢?”
青山顺了顺妻子的头发,想说什么,喉头一哽,没说出话来。就在这时,猛听到一声婴儿的啼哭,一声,两声……四下打量,除了风在跑,没见一个人影。于是就在心里笑,想孩子都成幻听了。
但敬慈又唤了声“青山”,愣愣地指着个地方。这回青山看清了,她指的是一只木盆,搁在最末一阶台阶上。
木盆里盛满了谷草,谷草上放了个裹青花被褥的婴儿。婴儿脸胖胖的,红彤彤的,睫毛很长,眼缝也很长,有些雨、雪花飘上去,融化了,润润的。啼哭声不尖厉,不撒泼,不蛮横,哭着,就像在呼吸,打招呼,告诉别人:我在这儿呢。
青山和敬慈伏在木盆上,看了很久。木盆是新打的,没有过漆,也没有磨砂,却从纹理中散发出新鲜的、好闻的,又让人难过的柏木味。
青山用食指在婴儿下巴上刨一下,啼哭一下就停了。他再刨一下,婴儿瞅着他,嘴角一弯,漾出了一弯笑。青山心口一痛,噗噗地滴了两颗泪蛋在婴儿的脸上。他的手指、嘴唇,都在轻微地哆嗦。
敬慈唤了他一声:“青山……”
青山没听见。他看着婴儿,婴儿眨巴着眼睛,由他看,也看着他。
他说:“我的儿。”
〇二〇
后来,敬慈好多次问青山,“青山:青山,你不是说要有个儿子吗,你不是说要有亲生儿子吗,你爸爸不是跟你说,地要深耕、儿要亲生吗?你咋会捡了她做我们的女儿呢?青山。”
青山不说话,抱着、看着他们的女儿,傻傻地笑。敬慈不依不饶,撅着嘴,问了又问。青山就亲一下女儿光生生的额头。“君君,君君,你替爸爸跟妈妈说,好不好?”忆君嘴角一弯,漾出一弯笑,眨巴眨巴眼睛,她还说不出话来呢。
在那个元旦前夕的雨雪天,缅青山脱下外衣罩住木盆,把木盆扛在肩上,把敬慈的手握在手里,一步步走回家。敬慈烧了热水,把木盆清洗了一遍,再把婴儿放在温水中轻轻地漂,漂了又漂,漂得她觉得干净了(差不多是透明了),她才把她放入被窝,放在楠木大床的中间。婴儿由她摆弄着,偶尔发出几声轻微的哭啼。但即便在哭啼,她的表情也是沉静的,嘴角偶尔还会弯出一弯笑。
敬慈用奶粉兑了开水,一小勺一小勺地喂入婴儿的口中。她的动作起初有一些紧张,僵硬,奶水洒在婴儿的下巴、颈窝,但婴儿不吵、不闹,咂咂嘴巴,很惬意地吮吸着,这使敬慈很快就熟练了起来。一杯奶没喂完,婴儿就睡着了。一滴奶留在她的小嘴角,就像叶尖挂的一滴露。
敬慈说:“她父母啷个舍得丢弃她?”
青山说:“一时糊涂吧。他们会后悔的。”
敬慈说:“后悔也晚了。”
青山说:“不晚的,总该给他们后悔的时间吧。”
敬慈说:“不……”
青山说:“你不要也糊涂。”
敬慈说:“给她取个名字吧,你不是叫她‘我的儿’吗?”
青山说:“取名?明天孩子的父母就找上门来了。”
敬慈说:“那我也情愿当一天的妈妈。”
青山说:“嗯……就叫她忆君吧。”
敬慈说:“你是说,她父母在想她?”
青山说:“我是说,她明天就走了,我们也会想她的。”
第二天一早,青山就把柏木盆放到门外,靠墙立着。这样,忆君的父母找来了,一眼就能看见。但等到天黑,过了后半夜,也没个人来敲门。
敬慈要回玉龙山林场,她要把忆君带了去。青山不许,他说,山上寒冷、潮湿,生了病怎么办?他在镇上找了户卖竹器的人家,那家有个身子硬朗的老太婆,白天就把忆君托在竹器铺,中午、晚上下班,都把忆君抱走,亲自给她喂吃的。
青山手巧,给忆君喂牛奶,也给忆君熬米糊、菜糊,榨果汁,还把鲫鱼蒸熟后,一点点将鱼刺剔干净,再一点点夹到忆君的小嘴里。
天气好的时候,他就用竹篮盛了忆君,提到佛湾里。他蹲在石像前修修补补时,忆君就躺在两步外的篮子里。她睁着眼缝长长的眼睛,看树叶,看穿过叶子的黄澄澄的阳光。青山手里的竹片刮下青苔、蕨草时,带出好闻的湿土味,她吸一口,嘴角一弯,漾出一弯笑。
有时候她看腻了,也发出一两声啼哭。青山就顺手递给她一只竹片、一块石头、一团泥巴。她喜欢泥,在手里捏来捏去,捏得满手满脸脏兮兮的。潘大姐是大佛湾的解说员,看了她这副尊容,哈哈大笑道:
“哈妹仔,哈妹仔,简直就像泥菩萨。”
青山听了挺得意,瞅着忆君,板起脸,轻声骂:“小淘气,看爸爸回了家不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