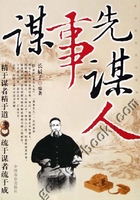08
这是我这辈子最不愿意打、却又非打不可的电话。没有人生气,没有人大吼或控诉,却带着莫大的失败和恐惧之感。
我跟沙特阿拉伯的调查总局主任道别之后,他们派了一辆黑色越野休旅车载着我行驶一小段距离,来到围墙之内高度戒备的美国领事馆内。贝鲁特工作站的卡特已经先帮我打了电话,跟他们说我会过去,所以我很快就通过了防止自杀式爆炸袭击者的路障和警卫室。
一进入领事馆内,值班的年轻官员就以为我只是来住宿的,于是便要带我到客房去。但还没走到电梯,我就阻止了他,跟他说我要去馆内的暴风雨区——一个特别设计的区域,可以防止任何电子窃听——打电话。沙特阿拉伯的调查总局和我或许相处得还不错,但这并不表示我信任他们。
那个值班官员犹豫了一下,大概是搞不懂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然后他开始打开防爆金属门上头的电子锁,带着我深入建筑的中央。我们经过一个内部的警卫检查站,于是我知道我们进入了中央情报局所属的区域,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小房间,里头只有一张书桌和一具电话,平凡到极点,唯一的特色,就是里头完全没声音。
我关上门,启动电子锁,拿起电话,请接线员帮我接通椭圆办公室。
对方立刻接了电话,我听到总统的声音。很明显他累坏了,但同样明显的是,因为期望听到好消息,让他精神振作起来。我之前告诉他们,我将会查到撒拉森的全名、出生日期,大概还会有张照片。结果没错,我都查到了,只是没想到根本没用。
然后“低语死神”说他也用分机接听了,从我无精打采的招呼声中,我想他猜到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就像任何优秀的项目调度官,他已经学会判断外勤探员每个行为的细微差异。“怎么了?”他问,声音很紧绷。
我冷酷而直接地告诉他们,就像在每日新闻中看到的那些意外报告一样。我说,尽管我们花了那么多力气,而且几个小时前看起来很有希望,但结果一无所获。什么都没有。
接下来是一段可怕的沉默。
“前一分钟我们是还神气活现的公鸡,下一分钟就变成鸡毛掸子了。”“低语死神”最后终于说,“这是个失败——”
“不但失败,而且时间不够了。”总统补充,失去了原来的希望后,他的疲倦清楚无比。
“那其他人呢?”我问,“去追查核反应器的那些人呢?有任何消息吗?”
“总共有十万个人在查,结果什么都没有。”葛洛弗纳总统回答。
“我想我们从来就没有机会。我想我们碰上了完全风暴——”“低语死神”开始说。
“一张白纸,又是独行侠。”我说。
“一张白纸,没错。但不完全是独行侠——不是。”他说。
“什么意思?”
“在阿富汗——他至少有一小段时间是有帮手的。一个独行侠不可能抓得到三个人质。”
他说得没错,但这似乎不重要,而且无论如何,总统已经开始讨论其他办法了。
“我们会尽快去抓那个女人,她叫什么名字,库马利?我们的计划是这样吧?”他问“低语死神”。
“是啊,‘朝圣者’相信她还不知道——对吧?”
“应该吧,”我说,“‘低语死神’大概也跟你报告过了,总统先生,她有一个跟他联络的方式,但我想那会是圈套。她会故意拼错一个字,用一个不同的单词,警告他快逃。”
“你说得可能没错,”总统说,“他都买过死亡证明了,绝对不是笨蛋——不过我们还是得试试看。”
“我会赶紧派一组人马过去,”“低语死神”说,“我们会带她离开土耳其,引渡她到‘光明点’去。”
“光明点”是个代号,指的是我去过的那个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位于泰缅边界的坤戎。据说一旦有人进入“光明点”,就再也不会出来了。说来奇怪,尽管我们面对的事情这么严重,但我不禁想着那个小家伙,还有他会怎么样。我猜想,会送回加沙的孤儿院,或是土耳其当地的孤儿院吧。无论去哪里,都不会有太多的鞠躬和笑声了。
“天亮的时候,或是接近的时间,我会发出总统令,”葛洛弗纳继续说,“关闭所有边界。我们会尽量封锁这个国家——机场、陆路通道、港口,任何我们能想到的。”
显然他们还是把目标放在防止带原者进入,就算他们猜对了这个传染途径,全美国每年有超过五十万的非法移民进入,所以显然任何封锁边境的企图都不太有用。就像那个老病毒学家所说的:早晚我们全都得坐下来,面对种种后果所组成的一场盛宴。
虽然我不认为他们的计划能奏效,但我还是什么都没说。我也提不出更好的办法,所以去批评他们的计划就未免太没礼貌了。他们只是尽力让这个国家不要陷入困境,如此而已。
“我们不必说是天花,”“低语死神”建议,“我们可以宣称那是一种很致命的禽流感。虽然这样也够糟糕了,但至少不会引起那么大的恐慌。一旦你说‘天花’,再加上‘出血型’,那就像是圣母峰——有什么后果你就完全无法预料了。”
“不,”葛洛弗纳回答——他显然也已经考虑过了,“要是真想泄露出去呢?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全民的合作——只要有机会,美国总是能努力迎接挑战。要是背叛人民,你就会失去他们的支持了。一个带原者就是一条线索,我们只需要这么一个,就可以反向追回去。我也计划要释出疫苗,虽然不晓得能有什么用,但我们必须尝试各种可能,利用现有的一切资源。”
“是,总统先生,”“低语死神”说,“那你呢,‘朝圣者’?你要回来吗?”
“我要去加沙。”我说。
他们两个人一时之间都愣住了,然后“低语死神”先回过神来。“一个美国人单独跑去加沙,没有伪装?他们会拿着炸弹腰带和球棒排队等着你——你一天之内就会死掉。”
“我跟沙特阿拉伯人谈好了,他们会找当地一些人帮我。”
“这表示排队的人会少一半而已。”
“纳苏里去过那里——这是我们唯一有的线索。”
“你不必这么做,”总统说,“没找到他不能怪你。相反地,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曾要‘低语死神’留下来跟我单独谈一下,然后我告诉他,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冷静的混蛋。我当时不晓得,你也是最优秀的。你已经做得非常出色了。”
“谢谢。”我只是简单地说。
“我不会送你一封总统的褒扬信,”他说,设法把口气放轻松,“因为你已经有一封了。”
“还有高尔夫球。”我回答。
他们笑了,这给了我一个机会。“我可以要求一样东西吗,总统先生?”我说。
“你说吧。”他回答。
“有个黑客是我们从雷文渥斯联邦监狱找来的,他做了一些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有没有可能别再送他回去?”
“你的意思是,给他特赦?”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回答。
“你觉得呢,‘低语死神’?你知道这家伙吗?”
“是的,表现非常杰出——我赞成给他特赦。”
“好吧——我会跟‘低语死神’要他的名字,写一份特赦令。”
“谢谢,总统先生。”这是我唯一能说的。我想象着“战斗小子”听到这个消息时,将瑞秋紧拥在怀中。
“祝你好运了,‘朝圣者’。”总统说,为这通电话收尾,“希望我们以后能在更好的状况下见面。”他的口气没什么信心。
然后电话挂断了,我坐在那片无声的静默中,想着往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大概都不会有这样的平静时刻。说不定永远都不会有了。
加沙。
“低语死神”说得没错——那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那里唯一的好处,就是没有地方可以航行:至少不会有任何船帆补丁的旧船在那里等着我。
其他地方或许有,但不会是在加沙。
09
这里是德国,所以那些卡车准时抵达。车子驶入警卫看守的栅门时,才刚过清晨六点,天空正下着小雨。
一如这些司机们做过上千遍的那样,他们转弯经过玻璃正面的行政大楼,进入工厂旁的通路,停在厂房后方的装卸货区。那个仓库人员——是个高个子,他的名字所有司机都不太记得——已经坐在一辆堆高机上,等着要帮忙把一箱箱预定运到美国的药品装上卡车。他什么话都没说——他向来话就不多——但那些司机都很喜欢他:他工作迅速,而且似乎比大部分同事都聪明太多。
这批货物的量很大,包括了各式各样的疫苗和抗生素,总共有几百万剂不同的药品。即使如此,撒拉森还是不到五分钟就把货物全都装上卡车。他也把所有文件全都准备好了,那些司机知道不必检查,因为只要是他准备的,向来都不会出错。
他们抓了那些文件,冲过小雨,爬上驾驶座,以破纪录的时间回头开上A5高速公路。
他们没有人朝后视镜看一眼,要是他们看了,就会发现撒拉森还坐在堆高机上,静静思索并观察着他们,直到那些卡车离开视线为止。他知道下雨和A5高速公路上的施工(那条高速公路老是在施工),会耽误那些卡车的速度,这就是为什么他动作这么快。但反正,天气和路况不至于害那些卡车赶不上预定的货机。
最后他垂下头,趴在前臂上,介于祈祷和筋疲力尽之间的状态。终于结束了,东西已经脱离他的掌握,那种解脱之感简直排山倒海而来,让他泪水差点夺眶而出。过去三年来沉重不堪的责任,执行安拉的事功所带来的庞大压力,终于消失了。武器已经离手飞走,这个任务的命运、各国的福祉、哪些无辜者能幸存,就要交由一套国境管制的系统来决定,而撒拉森相信,这个系统太过脆弱无力,因而几乎是不存在的。但那已经是他无法控制的了,他已经做了所有他能做的:剩下的一切,现在就交给上天了。
随着自由之感愈来愈强烈,他抬起头,跨出驾驶座。他走回仓库里,到他的储物柜,清空里面的东西。自从他来凯隆公司上班后,他头一次、也是仅有一次没有等到下班时间:他背起背包,走出大门,满心兴奋地走在飘着细雨的空荡街道上。
他回到小小的公寓,里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还有角落的一个水槽。他把架子上的食物扔掉,换洗衣物收进背包里,钥匙放在桌上,然后走出去带上门。他不打算去领剩下的薪水,也不打算去拿回他的房租押金,或是去跟威廉街清真寺那些慷慨待他的教友们道别。他神秘地离开,就像他来到时一般。
他很快穿过苏醒的城市,来到火车站,买了一张票。几分钟后,往法兰克福的快车进站了。他会去法兰克福的长期寄物处领回行李箱和医疗工具包,去厕所换回原来的衣服,也回复到当初那个来参加会议的黎巴嫩医生身份。
几个星期以来,当任务愈来愈接近完成之际,他也就愈来愈常思考结束后要做什么。他不想留在德国,也没有理由回黎巴嫩。他知道,再过几天,一场现代的瘟疫——他总想成“黑天花”——将会爆发。一开始很慢,像稻草堆里的一根火柴,但很快就会变成科学家所谓自行扩大的过程,感染状况急剧增加,让整个“谷仓”陷入一片火海。
美国这个最重要的异教徒,将会成为原爆点,死亡率将会极高。而失去了保护者的以色列,就会变得很容易攻击,最后将会任由身边的敌人予取予求。当经济活动大幅衰退时,石油的价格也会暴跌,而沙特阿拉伯的统治集团——他们再也无法收买自己的人民,也无法再依赖美国的支持——将会采取可怕的镇压行动,因而播下自我毁灭的种子。
短期内,整个世界将会停摆,也不可能旅行,因为各国政府为了安全,都会采取检疫隔离与封锁。有些国家会做得比较成功,不过在天花灭绝之前的一百年里,就有十亿人死于这种传染病。现代世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就连艾滋病都没有,因而没有人能预测传染的河流将会泛滥到哪里,又会在哪里转弯。
他心中将这个状况称之为“临终时间”,当这个时间接近时,他愈来愈确定,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想跟儿子在一起。如果他们会丧命,那么那是安拉的旨意。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跟自己的孩子相守,这样他就可以抱着他,告诉他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不管是这个世界或是下一个世界。如果上天的旨意要让他们活着,那么,只要有办法,他就要带他去阿富汗。他们会一起沿着阴影下的河岸行走,或许他会带他去看自己当年击落雌鹿武装直升机的那些山坡。当夏天转换为秋天时,他们会穿过遥远的山谷,等到时机到来,他们会笑着重返沙特阿拉伯,在最接近他父亲灵魂的土地上一起变老。
跟他儿子在一起?这个想法支撑着他熬过卡尔斯鲁厄的一切。有天晚上他到一家提供网络的咖啡店上网搜寻,已经在米拉斯找到一栋出租公寓,很适合男性居住。
没错,他会以医生的身份重新出现在法兰克福,搭火车到机场,登上飞机。他要飞到博德鲁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