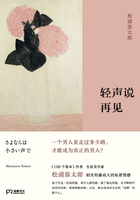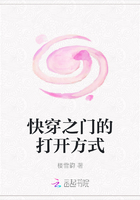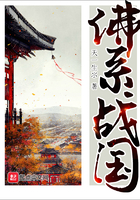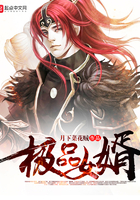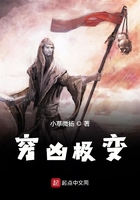安德烈·塔可夫斯基,1932年4月4日出生于俄罗斯札弗洛塞镇,诗人阿尔谢尼伊·塔可夫斯基之子,著名导演。
1986年12月28日因癌症病逝于巴黎,享年54岁。
1979年,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远赴爱沙尼亚拍出了科幻杰作《潜行者》,电影改编自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经典短篇小说《路边野餐》。尽管远离苏联故土,但塔可夫斯基镜头下的流动时空和精神内核,依然是原汁原味的苏联风格;而更令人叹服的是他对潜意识和外部世界的无缝隙转换,正如影片中那行诗句:“过去、未来只是现在的继续,一切变化只是在水平线那里闪烁。”
去年是塔可夫斯基去世30周年,先后落幕的第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纷纷祭出老塔作品回顾展,无数影迷景仰备至、抢票观摩。然而,如何看懂老塔,如何理解大师,如何书写这位影史最伟大的时间潜行者,依然是一门难度指数极高的电影功课。
不同于普通线性叙事的电影,非线性叙事往往采用倒叙、分段、重复、环形、多线索、罗生门等各种叙事结构。而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又往往不同于既有的非线性叙事类型,更多的手法是从他自身的日常梦境与生命体验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极具独创性。
比如塔可夫斯基拍摄于1972年的长片处女作《伊万的童年》,便是以“梦境”作为叙事筹码,整个故事从伊万的梦境开始,又以伊万的梦境结束。童年的布谷鸟、战壕上的风门和营房中的臆想,都如同梦境中的一枚枚记忆碎片,穿插在伊万天真无畏的日常斗争中。而1983年的《乡愁》开篇第一个镜头便是塔可夫斯基生命中最重要的回忆:土地,水源,马匹,狗。
在塔可夫斯基仅有的七部长片作品中,拍摄于1975年的《镜子》无疑是一部将塔氏非线性叙事运用得最为炉火纯青的作品。在宛如梦境的《镜子》中,老塔常常只保留必要的意象,并不加以任何解释说明,同时在影像时序上相互错位,构建出一种类似于“破镜重圆”的碎片化拼贴叙事,但这并非冰冷生硬的排列组合,而是基于以梦为马的流淌的内心感受。
假如塔可夫斯基以线性时序处理《镜子》的话,无疑应该是先有童年第一眼见到母亲的手,再有成年后黑夜梦境中的依次闪现。然而,这是一部伟大的塔可夫斯基电影,叙事逻辑永远不该遭受日常的掌控,所有记忆、梦境、幻想、白日梦,如水流般彼此交织融合,早已无法明确区分开,唯有吉光片羽的生命体验是活生生的。
正如电影理论家麦茨所言,非戏剧性就是把构成日常生活的一切失掉的含义网罗到一种更精细的戏剧中,揭示无重大意义可言的生活瞬间所具有的广泛含义。而意义的来源始终在于文本构成,文本可以是生活碎片,可以是意识流,可以是非线性叙事,但是意义不等于闪烁其词,不等于含糊性,不等于创作的绝对自由。
电影史上的长镜头大师有很多,如安哲罗普洛斯、贝拉·塔尔、米克洛斯·杨索、努里·比格·锡兰等,各自凭借独一无二的作者意识开拓了长镜头美学的广阔疆域。但真正使长镜头具有创世纪意味的却只有塔可夫斯基一位,其在电影史上的影响力与公认度,正如伯格曼之于小剧场、费里尼之于马戏团、爱森斯坦之于蒙太奇。
英年早逝的塔可夫斯基一生只拍了七部半电影,创作生涯弹指须臾,令人叹惋。所幸,长镜头拯救了他。诗意流淌的长镜头无形中延拓了老塔的艺术时空,正如他始终坚守的严肃的创作理念——“艺术家应当承担近似上帝的使命,艺术创造不是自我表达或自我实现,而是以自我牺牲创生另一种现实、一种精神性存在。”而老塔的长镜头美学,正是对他艺术使命的完美照应。
在《伊万的童年》中,塔可夫斯基还处于长镜头探索阶段,尚未抵达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他却别有技巧地调动了长镜头的蒙太奇功能,借由空间层次的逐渐变化,极其细微地展现了时间静静流淌的过程。一个镜头内部完成丰富的变化,甚至跨越现实与梦境的鸿沟,将伊万生命中的白天黑夜连成一种极具凝视之美的诗意状态,令人叹服。
在《潜行者》中,塔可夫斯基同样使用了大量的长镜头极力去制造出一种神秘主义氛围。作为影史上最与众不同的内涵型科幻片——《潜行者》被赋予了高度的隐喻和象征意味,而长镜头的运用则为全片缔造了一种壮观而肃穆的史诗气质。
塔可夫斯基生命中倒数第二部的电影作品《乡愁》则为我们贡献了影史上最伟大的长镜头之一。漫长的八分四十五秒,戈尔恰科夫手持燃烧的蜡烛涉入圣凯瑟琳水池,教堂无声地摇曳,没有布谷鸟的歌声,水很静。塔可夫斯基如此不动声色地完整展示了这场朝圣般的仪式——庄严而神秘,有一种诗性之美。
所谓“诗电影”,素来有所争论。但往往离不开抒情功能和联想自由,以及对隐喻、象征、节奏的艺术探索。而塔可夫斯基也正是因为对艺术电影全新境界的诗意探索,被世人赋予了“电影诗人”的美誉,尽管这个称呼还远远无法涵盖老塔的成就,尽管他也并不乐意被评论界称为“电影诗人”,但他的七部半作品无疑从精神本源上深化了苏联20世纪50—70年代的诗电影创作。正如人所言,老塔是真正洞悉了电影本体秘密的导演,他的创作从来不在外围打转,而是直取要害核心,心无旁骛。
塔可夫斯基的父亲阿尔谢尼伊·塔可夫斯基是苏联著名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出现在儿子安德烈的电影作品里面,尤以《镜子》中的那首诗最为经典:“透过监狱的围栏它听到:树林和草地的欢腾,海水的喧闹……我梦见另一个人的灵魂,穿着另外的袍子,掠过怀疑直达希望,像酒精那样,燃烧而没有阴影……”由此,母亲倚坐围栏的孤独背影,便成为了《镜子》中最著名的剧照。
而在塔可夫斯基精神自传《雕刻时光》的扉页上,伯格曼那段赞词早已被广泛引用:“初看塔可夫斯基的影片仿佛是个奇迹。蓦然我发觉自己置身于一间房间门口,过去从未有人把这房间的钥匙交给我……我认为塔可夫斯基是最伟大的,他创造了崭新的电影语言,捕捉生命一如倒映,一如梦境。”同被世人誉为“圣三位一体”的伯格曼,在他的无数作品中质疑上帝、睥睨众生,却意外地在塔可夫斯基这里找到了灵魂栖息的教堂。
塔可夫斯基说:“任何人想要成为导演,必须付出一生的时间作为赌注。”简单地说,拍电影这份所谓艺术家的职业,是贩卖时间与记忆、个人生命体验的行业。所幸的是,艺术一直都是人类对抗威胁着要吞噬我们心灵的物质产品的武器。
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作品中有着一系列关于“时间”的指涉,如《镜子》,如《牺牲》,如《飞向太空》,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回环往复,将我们一次次带入时间的秘境。在塔可夫斯基眼里,蒙太奇就是诗化的时间,而诗化的时间就是蒙太奇。至于电影的本质——永远是雕刻时光。
关于时间的最经典桥段,无疑出现在塔可夫斯基的《镜子》中。《镜子》是塔可夫斯基第一次决定用电影自由地表达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记忆。在这场名垂影史的超现实梦境里,沉默的男孩看着洗头的母亲,镜头缓缓流淌,时间恍如静止。直到母亲抬起头,她的头发开始“下雨”,水珠渗落,发出淅沥雨声。继而时间快进,渗水的墙壁出现斑驳水影,墙体大片大片地剥落。母亲拉过镜子,瞬间白发苍苍。塔可夫斯基在一个场景内实现了时间的瞬息流逝,传递了潜意识中母亲的痛苦。作为朝圣塔可夫斯基长大的毕赣导演,同样在《路边野餐》里置入了密码般的时间元素,无处不在的钟盘和手表,画在墙上的光线旋转的钟,火车飞驰投下的逆时钟阴影,等等。
至于对空间错乱的呈现,最著名的要数《飞向太空》中那一场“屋内的雨”,男主人公克里斯透过玻璃窗窥视屋内的父亲,他看到屋内雨若倾盆,而屋外却是晴空万里,以强烈反差制造记忆上的疏离。
看电影是一个呼唤记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时间并不是按秒计算的,时间更像一块可挤压的海绵,它并非物理上的时间,而是心理上的时间。正如塔可夫斯基所言,电影的本质在于它的客观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不仅包括对物质世界的客观记录,更加包括客观生活中人们的心理体验;而至于具体的表现方式,诸如记忆、梦境、幻想等,它们看似不可捉摸却均具有时间性质,并且都被时间记录下来。记忆与梦境早已成为塔可夫斯基电影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它们总能在特定情境下输出给时间,成为塔氏镜像中最珍贵、最激荡灵魂的闪光点。
1962年,年仅30岁的塔可夫斯基,手持金狮奖杯,站上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领奖台。《伊万的童年》在冥冥之中造就了一种完美的永恒。正如萨特所盛赞的,一位伟大的当代电影形式主义者到来了。
电影改编自俄国作家鲍戈莫洛夫的小说《伊万》,以哈尔采夫上尉第一人称回忆展开悲剧性叙事。电影中的小主人公伊万秉承了原著神韵,面色黝黑,单薄瘦削,总是目光坚毅地站在瑟瑟寒风中,由于发抖牙齿会咯咯作响。我们所看到的伊万,绝非常见的小战士形象,更像是一头因战争失去亲人拥护的兽物,在悲伤中学会独自战斗,孑然一身告别童年。
年仅12岁的伊万,就在内心种下了复仇的火焰。他随父亲的朋友到前线部队当上侦察兵,穿梭于战火和死亡的阴霾之中。一种因战争而扭曲的、不属于孩子的怪异性格在伊万的身体里开始生根发芽,属于他的真正的童年开始销声匿迹。
这是一种残酷的感召,积酿在整片属于20世纪的风景之中,伊万无疑就是这片风景中最让人不忍卒视的缩影。二战时期的苏联,沉重的失守之地。童年与战争,则成为这片失地上最难以绕开的母题之一。
所幸,伟大的塔可夫斯基为伊万造了另一重时空——残酷现实之外的梦境乐园。而正是这四场穿插其间的梦境将《伊万的童年》牵引到伟大电影的行列中。梦境中的和平生活,交杂着伊万对曾经美好岁月的所有记忆,以及对未来的遥远想象。
塔可夫斯基电影中惯用的经典意象一一出现在伊万的梦境中:布谷鸟、白桦林、路边的马、柔软的海滩、散落一地的苹果、雨水、星空、空无人烟的荒原。值得一提的是,塔可夫斯基电影中的意象绝非简单的隐喻符号,而是高于生活的诗意呈现。《伊万的童年》开场梦境中的布谷鸟正是诗意的最好明证。当老塔的长镜头沿着白桦树的枝干向天空伸展,母亲的呢喃成为伊万耳畔挥之不去的主旋律,那一刻,他依然如孩子般抬头喊道:“妈妈,有布谷鸟。”
艺术家的命数往往分两种,或者命如长虹,或者英年早逝。但无论死期早晚,孤独的存在永远是人类的宿命本质。我们固然能够共享物质生活,却注定无法共续精神命脉。
在老塔的电影里,我们往往只能看到一个孤零零的主角——是《伊万的童年》中的伊万,是《乡愁》中的诗人安德烈,抑或是《牺牲》中的评论家亚历山大,我们姑且称他们为“孤独的朝圣者”。而《潜行者》与《安德烈·卢布廖夫》则更是如出一辙地呈现了世界上最孤独的一类人。他们服务于塔可夫斯基的长镜头,并将那种针对信仰的献身精神演绎得淋漓尽致。塔可夫斯基后来在《雕刻时光》中写道:“艺术家是不自由的,只有他们将自身完全献祭于某种灵感,听从某种召唤的时候,它才可能创造出不朽的作品。”
1979年的《潜行者》由亚历山大·凯伊达诺夫斯基主演。作为塔可夫斯基弟子中最具才华的一位,凯伊达诺夫斯基自己也曾执导过三部长片和一部短片,其中最具知名度的是改编自托尔斯泰小说的《伊凡·伊里奇之死》。而《潜行者》中的他,一如禁区内的一头孤独盲兽,漫无目的地踽踽独行。在风动的荒丛中,他看见马匹倒地,看见水草游摆,看见下水道里撒满了硬币和注射器,一如锈迹斑斑的神隐之手,牵引着他,一步步通往The Room的内核。
那一刻,老塔的灵魂附着于凯伊达诺夫斯基的身体,直至《潜行者》荣膺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凯伊达诺夫斯基也于同年拍出了短片处女作《约拿或工作中的艺术家》,改编自加缪同名小说,并由老塔《镜子》的编剧鼎力操刀。那一年,世人习惯性地以为苏联的精气神似乎就这样被传承了下来。然而,世事终究难料,老塔拍完《牺牲》便撒手人寰,享年54岁;数年后,49岁的凯伊达诺夫斯基也随之匆匆离世。正如托尔斯泰所慨叹的:生命空空如也,存在的仅仅只有死亡。
身处故乡却染上乡愁,或许很多影迷并不能切身体会到这种感受。但我们或许可以明白,很多时候乡愁并非空间上的位移,而是心理上的一种情绪。就像阿彼察邦一直拍泰缅边境的森林,塔可夫斯基无论到哪个国度拍电影,都能拍得像扎根苏联一样。按老塔的话说,“不回俄罗斯,我就会死去,那些白桦林,那些童年呼吸过的空气,都让我无法逃离”。
在被流放意大利的那些年里,塔可夫斯基拍出了影史上最伟大的乡愁电影,即《乡愁》。犹记得塞尔乔·莱翁内在《美国往事》中曾以汽车的沉没与焚毁表现了一个时代的“水深火热”,而塔可夫斯基同样借此深度探究了人性的疯狂与焦灼。
启示录般的声音以尼采式的魇语响起,疯子多米尼克站在大理石塑像上,向罗马广场上的人群大声呐喊:“社会一定又会联合起来,以取代混乱。我们必须返回我们误入歧途的转折点!我们必须回到生命的根基,那里没有污染的水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竟然要一个疯子来告诉你们该为自己而羞耻!”于是,当《欢乐颂》响起的那一刻,多米尼克点燃身上的汽油,走向了自焚的宿命。他留给诗人安德烈一个拯救世界的秘密巫术,成功的可能性却如风中摇曳的烛火。
1986年,塔可夫斯基依然漂泊在遥远的意大利,完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部电影《牺牲》。影片在主题上延续了《乡愁》的精神命脉,却又明显走得更彻底一些。在《牺牲》中,亚历山大和小儿子在海岸边种树的长镜头持续了接近10分钟,父亲把不可言说的上帝信仰种进了孩子心里。塔可夫斯基用尽最后的力气努力怀乡,即便被世人当成疯子也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