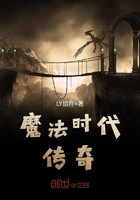房东是这东郊一带最出名的大户地主之一,家里有良田上千,有房屋无数。说话的一个近六旬的老妪,听说是那家地主的管家老婆。这些茅草屋本是租给佃户们的,可因为佃户们多不敢租太好的,担心太贵,一些质量上乘的房屋反倒空留了下来,偶尔会租给一些能出好价钱的人,或两三月,或半年、一载不定,只是租金略要比长租的贵些。
“那两位年轻男子,都是读书人,其中一个还精通剑法。瞧那模样,他们俩都对兰姑娘有那意思。有一次,老婆子问兰姑娘,是不是要在他们中间挑一个做夫婿。兰姑娘笑着说,那是她结义的大哥、二哥,反倒弄得老婆子有些不好意思。她说的倒也是实话,之后许多次,倒听兰姑娘唤他们大哥、二哥,他们待她也极好,总是从城里给她弄些好吃、好玩的来,有时玩得晚了,兰姑娘便留他们留在茅屋里过宿。那时,就听这院里又是唱歌、又是舞剑,还有人弹琴吹箫的,好不热闹……”
老婆子说完,颇是神秘的问道:“公子竟是兰姑娘的故人,可知她的身份。听这附近的人说,她极有可能就是名扬天下的小素女林幽兰,不知此话可是当真?”
沈思远的心情沉重。
老婆子又道:“若是真是她租了这里,恐怕这屋子就要涨租金了。”
沈思远冷哼一声,带着无尽的落漠,道:“大娘,在下告辞!”
有些人,注定了要错过。
即便,你拼命地追寻她的脚步,你跨一河一山,她却已经行走了千山万水,化成了天际可望却不可即的彩云。
待沈思远回到晋陵常平候府时,方从二哥、二嫂处得晓,就在他上次离开晋陵去姑苏的第二天,一个自称是兰姑娘的少女和两个年轻男子就到了府上拜访。
“那姑娘倒也生得水灵,言谈举止极是大方得体,临走的时候留下了一百零五两银子,说是数月前找四弟借的。我们不收,她硬是留下就走了!”
“可说去哪儿了?”
沈二夫人道:“我猜许是你要寻的兰姑娘,可看到她身边还有两位年轻男子,也不便提及你的事儿。本想留她们住几日,可与她同行的一个男子说,再晚就要误了船期,瞧那样子,她们像是要行船出门……”
浩浩天潮,东临海、西有海、南、北皆通海,她自是要去看海的,只是她现在要看的哪一处海,沈思远猜不到。
沈忆南道:“如此,四弟还要寻她么?”
“一切随缘吧!”
寻她时,总是错过,不寻时,也许就能有幸碰到。
沈二夫人道:“四弟可想过往后如何打算?”
“还能如何?只是和往年一样,到江湖走走、看看,许能碰上什么新鲜事。”
自此,沈思远再度行走江湖,直至两年后方才与林六再度相遇。
彼时,他是江湖四大侠之一,而她却成为江湖四大美人之首。
两年后,又值桃花盛开时节。
这一年的桃花会仿佛与往年并没有什么不同,深闺娇女未嫁,书院、武馆才俊未娶,花前相对,笑声连连,就连那空中飞放的纸鸢也沾上了自由与欢喜的气息。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飞狼、铁骑两营乃我浩浩雄师,南征北战,战功赫赫,今遣二皇子元武、三皇子元嘉奉朕旨意劳赏三军……”
就如林六最初的猜测,新月公主被夺去公主封号不到两年后,再复其封号。
沈思危正式出仕,上任文华阁大学士。
新月见沈思危归来,自是欢喜,早早儿地就迎了过去,依然是对恩爱小夫妻的模样。可,这只是表面。唯有思危知晓,他只是强迫自己接受新月,抛弃了是自己侄女的种种想法,勉强与她做了夫妻,可那心上的女子始终深埋心底。
“驸马今儿在宫里可好?”
沈思危道:“今儿早朝,皇上要二、三皇子前往南、北边关劳赏三军。嘉王那边还差一个副使,所以我就自请随行!”
新月心头咯噔一下:“你……要随三哥去边关?为何不与本宫商议?”
“自皇上封我为大学士以来,我对天朝寸功未定,总得争取些机会才是。这虽算不得是什么美差,可朝中想做劳军副使的大有人在。皇上一时高兴,也应了!”
新月最初的笑脸,刹时就变得阴暗起来:“父皇还真是,怎么就让你去北边,那么远,这一去恐怕又得许多日子……”
“快则三月,慢则六、七月,只要边城那边一切安妥,我们自会尽快回来。再则,大哥去边城亦有些日子了,我也想去那边看看他。”
“你去,那我也要去!”
“公主,这是劳军,可不是出去游玩。你且在府中好好休养,母亲那边还盼着你早些为我沈家开枝散叶,你得把自个儿养好,将来生下个娃娃也好带养。”
新月每每听他说到这儿,那脸色越发地难看,任她使出浑身解数,沈思危动不动就拿出子乎者也的说辞搪塞她,动不动就搬出佛经给她听。每月只有月满时,他们才能在一起,一个月一夜,要她如何怀孩子。
“沈思危,你瞧瞧,我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整日呆在这楼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都快被你养成一头猪了。养好,养好?我以前的锦衣,没一件能穿,回到宫里,皇姐皇妹们瞧见我的样子,都偷笑……想我新月,当年也是艳动燕京的大美女,可这两年下来,全变了模样……”
“你怎又说自己胖了。别人愿说,你由得别人去,只要我不嫌你就好。”
“你嘴上是没说,可你心里嫌了。以往一夜还有五六回,可最近半年,你每次就一、两回就吵说累了。分明就是嫌我胖了……”
“你又想束食?好,我不拦你就是,只有一点:别把自己饿晕了。我要去母亲那边请安,顺道说说三日后去边城劳军的事儿。”
沈思危不想和她纠缠时,总能找到藉口躲开,唯留下新月一个人在那楼里生闷气。看着桃纹镜里,那个胖胖的脸蛋,再看那越来越小的眼睛,越瞧越不顺眼,以往最喜欢和众姐妹在宫中欢宴,可如今都不敢去了,就怕看到她们异样的目光,尤其是新霁公主,每每见到她,眼里都是不屑的神色。
新霁下嫁才不过一年,就为婆家添了一个长孙,乐得婆家人把新霁都捧上了天。可是她呢,结婚也快三年了,却一无所从,以前怀过,还是男宠的骨血,加上落胎之后竟发了福,新月越发地不敢出门了,甚至不敢坐在镜子跟前。
北燕三十四年春,三月二十六日。
一行浩浩荡荡的长龙队伍从燕京城里出发,到了桃杏林外的官道上,一列长龙一分为二,一列往南,一列往北。
往北方的乃是由嘉王任劳军使臣的队伍,副使臣是沈思危,前往北方边城问劳铁骑营将士。
往南的,是由端王带队的劳军使团一行。
三月二十六出发,按理最多五十天就能抵达边城,然而嘉王府、镇远候府收到的消息却如晴天霹雳。
卫长胜身负重伤在五月二十的深夜赶回了嘉王府:“禀王妃、木妃,出大事了!”
崔王妃纨纨嫁入嘉王府后不到一年,身怀有孕,诞下一子,取名琰。之后,木妃有孕,育一女。王妃、侧妃有孕后,乌、桂等一干大燕籍姬妾也先后有孕,其间多有身子不适落胎、滑胎的,就连杏奉侍两番怀孕也未能保住。
崔王妃道:“出了甚事?”
卫长胜从怀中掏出一封带血的书信,递与崔氏。
拆开书信,从里面取出信笺,但见书着:“嘉王、新月驸马皆在我手,若想救人,着崔、林、木三妃亲往!”
崔王妃纤手一颤:“这……”
木妃也瞧见了信上的内容,道:“这林氏早不在燕京,就连沁忠夫人也不晓她的行踪,我们哪里去寻她。为何要她去救人?”
如此,众人便有些看不明白了。
卫长胜道:“当年,林王妃在时,曾从贼人手中救过新月公主夫妇。”
木妃道:“可现在她早不是嘉王府的王妃。这些贼人难道不知道,我们嘉王府现由崔王妃说了算。”
崔王妃秀眉一挑,看着一边的木妃,心里暗道:这是什么话?难不成还真巴不得她去送死。
“卫将军,你和王爷一行好好儿的,王爷怎的就被贼人抓住了?”
卫长胜回想着:“那日,我们在林城四海关一带劳军完毕,王爷、驸马爷便携着属下等前往北边飞鹰岭,四海关的将士刚离开不久,不知从哪儿就冒出了许多黑衣人,也不说话,只是放箭。如此,我们的许多人都中箭身亡,王爷和驸马爷因属下等保护得力,只受了些许皮外伤,不曾想,那些黑衣人好生厉害,竟敢我们团团围住,只要我们一反击,就立用毒箭射杀。最后,有个男子大声说:他们只要军饷和嘉王、沈驸马。剩下的皆是伤兵、弱兵,哪还敢反抗,他们便将我们一行剩下的十余人一并捉了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待属下醒转,便已在一处地牢之中。那些黑衣人将属下好一顿鞭笞,之后就给了属下这封信,放属下回来报信。”
木妃踱步房中,听卫长胜说来,那些黑衣人是一早就知晓行程的,早早儿地埋伏在途中,只待护送的四海送将士一走,他们就下手了。
按理,北边虽然近年来一直很太平,可据说前凉的余孽便藏在北边一带,所以军中一早就下了军令,着令各关口将士,准时前往迎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