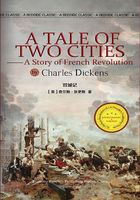“坦洋工夫”茶以珍奇的品质誉满天下,也带来了坦洋村的空前繁荣。沿溪两岸新房林立,三座拱桥临溪崛起,那一公里的小街,挤着36家茶行外,还见缝插针开办起”第三产业“的各类商铺140多家,几乎各大城市所拥有的各个商业门类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每逢茶季来临,街上商人茶工摩肩接踵;买卖茶叶的人熙熙攘攘,市井街坊,人山人海,也茶山茶海,从国外寄来的信件,无须以省地县前称,直书”中国坦洋“,即可准确无误地送达。时值后来的民国四年4月,杭城商会选“坦洋工夫”茶代表福建茶叶,赴美国旧金山参加万国博览会展览,荣膺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金奖,凡此等等,足可说明福宁府的茶事兴旺发达。福宁府的茶事如此兴旺发达,应运而生的水上茶叶之路自然也就兴隆发达。以鹤江流域莲花港为主的各口岸商船,虽然还没有从真正意义与实际地理位置上出国,却已经在这场出口贸易的大戏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码头“日均靠泊民船100多艘”,还不包括郑崇富兄弟他们这些小小的溪犁船了。
此刻,年已四十,人高马大,额头显得特别宽大黝红的郑崇富,正以大哥和载头的双重身份,吆喝着他的兄弟姐妹与族亲装货:“大家的手脚都快点,不要被雷雨赶上啦!”
略微白胖的茶商胡少琦在他旁边转着,有些不放心地对滩上装茶的溪犁船指指点点。
崇富说:“胡行主,您尽管放心好了!我都给您运了十几年的货,哪一次误过,又哪一次损过?”
胡行主回答:“正因为你这个人办事情守信用,我的茶米才一直留给你们兄弟的船帮运的。可眼下你睁大眼睛仔细看看!”
胡行主指着不远处的几只船——那几只船上的人仿佛很恨这些茶箱茶袋,而手脚很重地装船。
胡行主有些不客气地说:“崇富头,我怀疑你心狠,对你兄弟姐妹这些自己人的抽头抽太多了,他们嘴里不敢讲,却拿我的货出气呢!”
崇富有些羞恼,但自然不敢得罪胡行主,只能赶上前几步对那些自己人吼:“喂!喂!你们一个个脚手给我轻一点!人家那是茶米,不是菜干,受得了那样狠心踩吗?”
船上那些自己人,经这一吼,手脚显然轻了许多;但其中有一个却明显愤懑地嚷着:“这边要大家赶雷雨,那边又怕人手脚重,要不都让你们自己两个人来装!”
胡行主因为离得较远,听不大清楚,也看不大清楚,但也能猜出几分地皱皱眉头:“那人是谁?在嚷嚷什么?”
崇富恼怒地说:“你就当他放屁!”
胡行主偏要问个清楚:“他是谁?”
崇富有些无奈:“就是我那二弟崇发呗!你也知道他的脾气,人虽然率直,力气也肯花,但就是一个牛脾气,你当大老板的人,量大福大,不要跟他计较了!”
胡行主晒笑了:“我怎么会跟他一般见识?只是你亲兄弟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和气一些,保证我的茶米完好无损地运到莲花港里就好了。”
崇富又大包大揽地说:“胡行主,这您就放一百个心吧!我包您每一趟货都完好无损,要是掉了或湿了一粒茶米,我不但不要您一分一厘运费,而且卖了老婆孩子也赔您!”
胡行主打趣道:“老婆都卖了,你拿什么睡?”
崇富也做风趣地:“‘老婆后锅汤,死了再去扛’呗!”
胡行主听了这话却抢白道:“好了,好了,别说得这么轻巧了!我还不知道你们这溪犁船上的灶只有一个锅吗?再说,你们船人就娶这一个锅都要留一肚侪汗呢!”
崇富这回才不敢夸口地傻笑了。
从城外溪滩顺流运到莲花港的茶米,都是转驳到三条桅杆的大长驮或船首豁开的大乌驮,或使机器的“车轮”出海口的。每一次往大船卸茶米时,郑崇富都身体力行地跟他的兄弟们,一箱茶或一袋茶地往货舱卸货。这样的时刻,他们兄弟配合得很好,也很有秩序。卸一只溪犁船上的茶叶时,兄弟们都集中到这一只船上,同心协力七手八脚地往大船卸货。卸完货的空船就让舱后的女人荡桨退出去,揽在船帮外围等着,而后再依次靠近一只没卸货的,兄弟们又同心协力七手八脚地围上去装卸……
七星屿的上屿,是郑姓船帮的岙窝,炊烟袅袅中,卸完茶米的溪犁船上都开始张罗了吃饭了。紧聚在一堆的崇富兄弟们的几只船上,除了老二崇发与父母同船外,其他兄弟基本上都已经成家立业的小夫妻俩一条船。
相邻的几只船上,大家都敞开船篷在自家的船上埋头喝酒吃饭;与崇富虽然同一个母亲肚子出来,五观长得也差不多,只是身材没有崇富那样高大,却显得像铁墩一样壮实的老二崇发却黑着脸一个劲地喝闷酒。
这个暮霭笼沉的时刻,他们的老母亲有些不放心:“二仔啊!今晚你怎么一个劲地喝酒啊?”
崇发还是埋头喝酒,没理母亲。
邻船上的崇富预感有些不祥地跳了一下眼皮。
邻船上的其他兄弟开始没心思吃喝,他们都担心这一边的动静。很快,他们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崇发把最后一碗酒一饮而尽后,把碗往舱盖上重重一墩,就义愤地质问隔船的崇富:“哥,这回的船载(运费),你一个人不能再抽多么多了!你要是再这样心狠地抽头,你的货头我们大家就不帮你运了!”
也喝了不少酒的崇富顿时就恼羞成怒,脸红脖子涨地还耍大哥脾气:“你们哪个不想运我搭来的货头,就别运!我搭来的货头还怕没人运?”
“人家当载头的顶多抽一两成,你却一直这样狠心地抽三成,我们大家早就不想运了呢!只是你是当大哥的,大家都放不下脸来说……”
“我看就你一个人天天要跟我过不去!”
“就我一个人跟你过不去?你问阿爸阿奶看看,私下里哪一个弟弟妹妹不说你心狠?”
“哪一个嫌我心狠,就不要运我搭来的货!”
“你对亲兄弟姐妹都这样心狠,哪一个还替你卖命?但是你要把抽去的钱退还我们!”
“不想运我的载头,更莫想退!”
“今日我就要你退!”
“我就是不退,看你怎么样?”
“我就是要你退!”
崇发性子火暴起来,出人意外地跳过船去;崇富吃了一惊,但很快把心一狠,迎了上去。
兄弟俩起初还是你攥我,我攥你,胳膊对胳膊,脑袋抵脑袋,斗牛般地抵斗。一只溪犁船被弄得晃来晃去,好几回都差点要翻,船上的孩子们惊哭成一片。
他们边抵斗,还边骂娘:
崇富骂:“操你奶的!你这个臭婊子!敢和我闹!”
崇发骂:“操你奶的!你这个臭婊子!我怎么不敢跟你闹?”
而他们亲亲的阿奶就在隔船上,不知所措也无可奈何地看着听着儿子们骂自己。她只能一个劲机械地在回骂:“不孝子,不成子……”听不清也看不出她在骂哪一个儿子。
后来两个人又一起落到水里,扭在一起,也一起喝了不少浑浊的半咸半淡的水。打了许久都难分胜负。但最后还是心狠的人占了上风——做大哥的先爬回船上,竟然趁着当弟弟的两手抓着船舷要追上来时,冷不防地拔起硬木桨桩,狠狠地照自己亲兄弟的脑门中间干下去。
崇发顿时跌落水里,只顾抱着要爆裂的天灵盖就天旋地转地痛叫起来:“啊哟,阿奶哟!我痛死了!啊哟,阿奶哟!我痛死了!”
他的阿奶这回才旗帜鲜明地骂崇富:“你这大的一个畜生!你真的决断狠心打死你亲弟弟吗?你这个畜生!那你的脸真的长毛了啊!”
多亏她这样一骂,崇富打算再来一下的手,才停在半空中没敢再下去,只剩嘴巴凶:“我就是要他死!我就是要他死!”其实这时他看见其他兄弟都围上来时,心里头也有些怯了。
但是围上来的兄弟们,只敢用恨恨的眼光盯他,并不想群起而攻之;他们急忙看护着二哥崇发,下水把他拉了上来。弟媳妇之间有正在哺乳的,急忙掏出奶头来,搁在崇发那已经紫青出血的头顶上,不断地挤出乳房,射些乳汁来让弟弟们给他紧搓慢揉。就这样搓揉了许久,见崇发先前那头壳要爆裂的感觉稍有缓解,大家才松口气。
他们的老阿奶这才回过头,不顾什么亲情和船家的忌讳,搜尽世间的污言秽语,大骂起来:“崇富,你这个面长毛的畜生!你这臭婊子!你的心黑了!你今日不叫雷劈死,明日的船也叫浪给扳了!一家子都淹死,尸体都没处捡……”
她一连这样骂了三遍后,她的老丈夫和孩子们感觉这样骂有些不妥,都把脸皱成一把。
做老丈夫的很快就不悦地发话了:“老诸娘,你要骂,就骂那畜生一个人,不要‘一条竹篙压一船人!’”
老三崇旺也代表他的兄弟姐妹道:“阿奶,你不要这样虾米混糟地一起咒骂大嫂和孩子们,大嫂挺老实,孩子们也讨人喜爱的;大嫂不也经常挨他的拳头脚踢吗?”
这时,他们那老实怕事的大嫂,偷偷把船荡开时,却还挨崇富的骂——其实已经色厉内荏的斥骂:“臭诸娘!你把船荡开做什么?我还怕他们围过来把我吃了吗?”
这一个没有欢乐和温馨的夜晚,崇富倚靠在舱梁上一声不吭;昏暗的灯光下,他凝重的神色中明显透出某种苦郁。
老实巴交的女人水梅见他这模样,提心吊胆地躲在一旁,不知怎么是好。
许久,崇富深深地叹口苦气:“唉——”
水梅迟疑了许久,才敢怯怯地问:“当、当家的,你其实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做啥要抽自家人那么多啊?”
崇富竟然气不打一处来地憋火:“你懂个屁!要不是为了子孙,就为了吃穿,我难道还喜欢对自己的兄弟姐妹下狠心吗?”
水梅被他说得一头雾水。
崇富又长叹一口气,以罕有的和缓口气道:“孩子他奶啊!你知道我们船人为什么被山人欺负吗?”
水梅摇摇头。
“那就是因为没‘字’啊!但是山人怎么肯让咱们曲蹄子上岸读书呢?咱们连上岸走路他们都要你走旁边,有裤子穿的还要你把裤管卷的一边高一边低,还不准你大声说话,不准你笑!除非咱们脱胎换骨啊!”
水梅这才理解崇富的苦心,才温驯体贴地依偎上来。
崇富也顺手抚着她,流露出夫妻之情:“但咱们都这把岁数了,怎么还可能脱胎换骨去学字墨呢?我想来想去,想了很久,咱们只有想办法让孩子们上岸读书,让他们脱胎换骨,咱们的子孙以后才有出路啊!”
女人水梅担忧地说:“山人不是不让咱们船人的孩子上岸读书吗?”
“这事我早就想过了。咱们的孩子一定要认一个有头脸的山人做义爸,而后让他想办法帮我们把孩子弄成山人孩子模样,再弄到县城里头去读。”
水梅长嘘一气:“哦——”但她很快又忧虑起来:“到哪去认这样的义爸啊?”
崇富似乎胸有成竹:“这人我已经想定了,就是那茶行的胡少琦老板。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载头,也替他运了这么多年的茶米,逢年过节,我还都挑些特大的虾蟹与头季的鲜鱼给他,如今跟他都有半个亲戚的关系了。什么时候机会正好的话,请他到咱们船上吃一顿,我再求他,他肯定会给我这个面子的!”
水梅这才全部清楚崇富的苦心,不禁温柔地抚慰起丈夫来。
崇富却把眼光投在舱里正酣睡的十岁儿脸上:“让大的一个先认他做义爸吧!”
茶商胡少琦的老家就在那著名的茶乡坦洋村。这一个驰名中外的盛产茶叶的山村,地型正如一艘巨轮的甲板。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村前清流如练,村后桂树飘香,隔岸松杉苍翠,远近茶园碧绿。
这一日,在一个山包上的茶园里,胡行主正不无自豪地对两个身材高大的洋客人介绍村景——其中一个是来自莲花港此时身兼翻译的摇橹神父。
胡行主指点江山般地四处指引着洋人遥看:“我们坦洋村还有十景呢!看,那里是‘锣鼓争鸣’、这里是‘龟蛇遥望’,这边是‘云桂飘香’、那边是‘清溪飞凤’;还有‘玉笔尖峰、骏马飞天、天台洞府、蒙井清泉、石门弄月、鲤鱼朝天’等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景物,我一一带你们去看!”。
摇橹神父不停地向洋茶商翻译着,洋茶商也饶有兴趣地频频点头。
胡行主带着洋客人看完茶园后,回到他的胡记茶行请洋客人品那“坦洋工夫”。这个名叫“坦洋工夫”的茶米,不知道是怎么加工制作的,喝起来的味道特别淳朴香醇;有一种绍兴老酒温热的味道,很暖胃,也很提神,不但岸上的山人,尤其大城大市的茶楼酒肆的常客喜欢,而且洋人也很喜欢。听说那个什么英伦三岛的洋女人喝午茶少不了它,就连那来自东洋的蛙寇,据说也很喜欢它。一个案例可以证明,就是他们每一次抢劫莲花港时,茶行都被抢一空。
因为舱盖上放不稳茶盅等原因,几乎不喝茶,渴了就用木瓢子往溪里舀一瓢水喝的船人,只管运茶。每一趟把溪犁船撑到五六十里远县城的溪滩上,然后就由这“胡记茶行”把各村民挑来的各种茶米,装成箱,谓曰茶箱,由码头工人扛到埠头,装上他们的溪犁船;再由溪犁船放下溪滩,返回莲花港转驳洋人的洋轮,运到他们的国家,或由本港的大船和车轮运往各城各市。
每年的清明节之际,这茶米就开始采摘制作加工,以及转运。这由山溪到江港的转运工作,几乎都由郑姓船帮承包了。当了多年载头的郑崇富,跟那胡少琦自然就熟悉成半个亲戚了。为了想让儿子到城里的书馆里读书,郑崇富几乎不惜一切代价了。除了逢年过节送海鲜,名叫“船载”的运费,从来不敢讨价还价外,而且平时也经常请这胡行主到船上喝拢络交情的小酒。
眼下,在胡记茶行的茶桌上喝茶时,摇橹神父慢慢品味道:“不知道这茶叶是怎么加工制作的,喝起来的味道特别淳朴香醇;有一种老酒温热的味道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