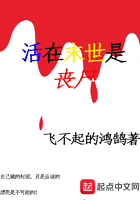有一次,街上正在铺沥青,我从热气腾腾的熬沥青锅里拿了一块咬了咬,结果被她当场抓住,跟我在一起的是我的朋友吉米·克莱恩,他家劳希奶奶是怎么也看不上眼的。这件事,使她对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其持续的时间,比什么都长久。这类情况越来越多,我干的坏事也越来越要不得。由于一次次受到处罚,我心里感到很难受,便向妈妈请教,怎样才能得到宽恕,同时还托她代我向老太太说情,得到宽恕后,我便会流下眼泪;可是后来,通过与世人所干的坏事比较,使我感到我的那些坏事实在应该得到更多的宽容,于是便对受罚产生了一种抵抗情绪。这并不是说,我已不再把老奶奶和那些最高贵、最美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如她自己所说的欧洲的宫廷、维也纳会议、她家的豪华,以及从她言行中流露出的渊博知识和文化教养——她会让人想起极其重要的含义,如德国国王的威严容貌、报刊插图上蔚为壮观的各国首都,以及最深邃的思想的阴沉等等。我并不在乎她的唠叨挑剔,可我不想在十四岁时便带着证明到肉类加工厂去做工。因此,偶尔有一阵子,我曾发奋用功读书,认真做作业,老师提问时,我几乎爬出位子,使劲挥动举起的手,抢着回答问题。这时候,老奶奶就会发誓说,我不仅可以读中学,而且只要她还健在,够精神,我还能上大学。“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她讲起她的表妹达霞,在开夜车准备医科考试时,为了保持清醒,竟在地板上打滚。
西蒙学校毕业并在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致词时,我也跳了一级。校长还在演说里提到了我们——马奇家两兄弟。那次毕业典礼,我们全家都去参加了。妈带乔治坐在后面,以防他闹起来,今天她可不想让他一个人留在家里,她俩坐在最后一排,也就是楼上的楼板和楼下的地板最接近的地方。我得意洋洋地和老奶奶坐在前面,她身穿黑色绸衫,戴着多股的金项链,链下垂着一个鸡心金盒,盒上还有她一个孩子长牙时咬的牙印;她鼻子尖尖的一副傲气,默然地强压着激动的心情,帽上的两枝羽毛垂向两个方向,和别的移民亲戚相比,她确实显得气度不凡。就是她一直想使我们明白:如果我们照她的话去做,就会有很多像这样博得公众尊敬的收获。
“我要看到明年你也能站在台上致词。”她对我说。
可是,她的打算落空了。尽管我曾发奋用功跳了一级,可是已经太晚了;我过去的成绩不行,而且,我也没有从这次成功中获得持久的鼓励。我生来就不是这种料。
而且,就连西蒙他也没能再接再厉。虽然他读书依然比我用心,可是打从那年夏天到本顿港去当侍者之后,回来人就变了,不仅志向和以前有所不同,连对于品行也有了新的看法。他的改变有一个标记,我觉得很重要。他在秋天回来时,人长得更壮实,毛发也更金黄,然而有颗门牙折断了,变成尖尖的,在那一口完整、雪白的牙齿之间,显得有点变色,虽然依旧笑声爽朗,可是整张脸就因而变得不同了。他不肯说这是怎么搞的。是跟人打架被人打断的么?
“是跟一尊塑像接了吻,”他对我说,“不,是我掷骰子时,咬着一枚角子咬断的。”六个月前,这样的回答是不可想象的。此外,有些钱的去向他也没能说清,以便让老奶奶满意。
“别对我说你一共才分到三十块钱小费!我知道,雷曼是个一流的休养胜地,客人有远从克利夫兰和圣路易斯去的,你去了一夏天,当然自己要花掉一点,可是——”
“嗯,我的确花了约莫十五块钱。”
“西蒙,你是一向很诚实的。奥吉现在把挣的每分钱都带回家来。”
“我不是吗?我也还是一样!”他说道,自尊心越来越强,摆出一副神气十足、不屑撒谎的样子,“我带回来我十二个星期的工资,另外还有三十块钱。”
她没有作声,金边眼镜的后面射出两道炯炯的目光,露出一种不要以为她头发花白、面多皱纹便可欺骗的神色,双颊迅速一吸,不再谈论此事。她表示,到时候,她会给他来个不客气。不过,我第一次从西蒙那里了解到,他认为这事不必担心。他并不是准备开始公开反抗。可是他有他的一些主意。后来,我们俩便互相谈论不能在女人面前讲的事了。
起初,我们常在同一个地方干活。有时考布林人手不够,我们俩都到他那儿帮忙,或者在伍尔沃思百货商场的地下室,把陶器从大木桶里搬出,木桶大得惊人,简直可以在里面行走;我们还得扒出里面发霉的稻草,扔进炉子。有时候则把纸张装进老大的打包机打包。地下室里堆有变质的食品、芥末罐头、放得太久的糖果,还有草制品和纸张,它们都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吃午饭我们才到上面来。西蒙不肯从家里带三明治来吃;他说我们是在干活,需要吃热餐。我们花两毛五分钱买两个热狗、一杯沙士汽水,还有馅饼;小红肠夹在松软的面包卷里,撒滴着使地下室空气变坏的同一种芥末。不过要紧的是,要装成一个雇员的样子,以雇员的身份和那些女孩子搭讪,身穿工作服,在那罐头般拥挤、吱嘎作响、热闹嘈杂,出售五金制品、玻璃器皿、巧克力、鸡饲料、珠宝首饰、呢绒绸缎、防水油布,还有流行歌曲唱片之类的杂货商场里干事——这是桩了不起的事;而且,他们还是那儿的阿特拉斯[50],在下面,可以听到头上的地板在千百人的踩踏下呻吟,隔壁就是电影院通风机房。从上面,还传来芝加哥大道驶过的电车的隆隆声——风刮起的尘土使蒙血的星期六变得阴沉沉,一幢幢五层楼房黑魆魆的轮廓,从各家店铺圣诞的辉煌灯火一直升向什么也看不清的北区的朦胧中。
不久以后,西蒙便在联邦新闻公司找到更好的工作。这家公司特许在火车站摆设货摊,以及在火车上出售糖果报纸。家里得先付制服押金。他开始半夜三更回家,在闹市区和火车上工作,穿着合身的新制服,十分神气,像个军校学员。星期天早上,他很晚才起床,穿着浴袍出来,派头十足地坐下来吃早餐,现在他挣钱多了,开始大胆放肆起来。他对妈和乔治火气比以前大了,有时候跟我也很难相处。
“在我没看以前,别去碰《论坛报》。他妈的,昨晚上我刚带回来,今天早上还没看,就扯得稀烂了!”
不过,他也瞒着老奶奶给妈一点挣来的钱,让她自己花,还使我有零用钱,就连乔治也有了买小糖人的钱。西蒙对钱一向不小气。他有爱送东西给人的东方人的脾气;一没钱,他心里就不踏实;他宁愿不付账白吃一顿溜之大吉,决不肯不留下像样的小费就离开快餐车。有一次在咖啡馆,他留下了两毛小费,我觉得太多,拿回一毛,气得他朝我头上揍了一拳。
“别再让我看到你干这种小气鬼干的事了。”他对我说。我怕他,没敢回嘴。
在那些星期天早上,从厨房里可以看到,他的制服小心地挂在卧室里的床脚上,窗子上热气凝成的无数水珠往下流着。西蒙觉得自己的地位已经足够巩固,俨然准备把这个家的控制权抓到自己手中,因为他有时跟我说起老奶奶时,把她当成一个外人。“她跟咱们其实没有任何关系,这你也知道,奥吉,是不是?”
她需要担心的倒不是反抗,而是摒弃,是当他把报纸摊满一桌,手撑前额,颜色渐深的金发往下垂着,自顾自看报时对她不加理睬。他还没有废黜她的任何计划,也没有干预她对我们其余人的控制,尤其是仍像以前那样听从使唤的妈。她的眼睛已越来越不行,去年配的眼镜已经不够深。我们又到免费诊疗所去配了一副新的,再次通过了盘问的关。这次,这个关过得很险;他们在记录上有西蒙的年龄,询问他是否不在工作。我想我已经不再需要老奶奶的排练,自己就能胡诌出答复;就连妈也不像平常那样乖乖地默不作声,而是提高她那清晰得出奇的嗓音,说道:“我的两个儿子都还在上学,放学后,我又需要他们帮助我做事。”
后来,我们差一点又被编制预算的职员识破,吓得要命,幸亏靠了那天人多,总算领到准配单,去了眼镜部。看来,我们没有老奶奶的调教还是不行。
现在,西蒙带回来的消息成了家里最感兴趣的事。他的工作岗位从火车上调到拉萨尔街车站的货摊,后来又调到出售书籍和小说的中心货摊,那儿是旅客必经之地,生意最忙,也最重要。他在那儿能见到身穿毛皮大衣、羊驼呢衣服或头戴宽边高顶帽的社会名流,在他们所带的随身行李之间走来走去,通常都比报道中描述的更加神气或者更加忧郁,更加和蔼或者有更多的皱纹。他们从加利福尼亚州或俄勒冈州搭乘波特兰玫瑰号,冒着从拉萨尔街高楼大厦顶端那不近人情的高处旋转而下的雪花,使劲地沿着火车的高速线路抵达这儿。他们乘二十世纪号列车前往纽约。在他们乘坐的小客厅似的包房里,装点着鲜花,陈设擦得发出暗光,地毯、窗帘、沙发垫套等一律深绿色;他们在银水盆里洗手,用瓷杯呷咖啡,抽的是雪茄。
西蒙对我们报告说:“今天我看到约翰·吉尔伯特[51],戴着一顶大号的丝绒帽”,或者是“参议员博拉[52]今天买《每日新闻》时,把一毛钱找头留给我了”,或者是“如果你看到洛克菲勒[53],你定会相信,他真像人们说的那样,有个橡皮肚子”。
当他在饭桌上讲着这些事的时候,他心中燃起了一线希望,既然他已接触到这些名流,说不定有一天他也会出名,会进入名流的圈子;也许他会被某位大人物看中;可能英萨尔会注意到他,给他名片,要他第二天早上去他办公室见他。我感觉到,过不多久,老奶奶就在暗自责怪西蒙不肯上进了。说不定是他对出人头地关心不够,或许是他的态度方法不对,也有可能是举止冒失莽撞。因为老奶奶相信,一个突然的机遇或者灵机一动会使你受到大人物的注意。她收集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故事。每当她读到朱利叶斯·罗森沃德[54]又要给学校捐款时,她便打算写信给他。她说,他总是把钱捐给黑人,从不给犹太人,这实在把她给气坏了,她大声叫骂道:“那个德国鬼子!”她这一喊,那只老迈的白狗便站立起来,竭力想快跑到她跟前。
“那个德国佬!”
其实,她还是钦佩朱利叶斯·罗森沃德的;他属于和她地位相等的那一阶层的内圈;他们对事物的理解和我们不同,他们坐拥一切,操纵一切。
当时,西蒙正竭力为我在拉萨尔街车站找份星期六的工作,好把我救出那家百货商场的地下室。至于他原来的位置,已由吉米·克莱恩顶补。非但老奶奶,就连妈也催他快想办法。
“西蒙,你得把奥吉也弄进去。”
“是啊,我每次见到鲍格都央求他了。唉,可是你们知道,那儿人人都有亲戚的呀!”
“怎么样,他肯不肯收礼?”老奶奶说,“相信我的话,他正等着你去孝敬呢。请他来吃饭,我教你怎么做。在餐巾里裹进两三块钱。”
她要教我们怎样处世哩。当然,除了尼禄[55]那种在餐桌上用毒羽拂对头或眼中钉咽喉的行径之外,什么手段都可以。西蒙说,他不能请鲍格来吃饭,他只是个临时雇员,跟鲍格还不熟,而且他也不想做得像个马屁精,被人瞧不起。
“得啦,我亲爱的波托茨基伯爵[56],”老奶奶说着,眼睛一眯,露出冷漠的神色,西蒙则已不耐烦得直喘气,“所以你宁愿让你弟弟留在伍尔沃思百货商场,让他和克莱恩家那傻小子一起在地下室里干活了!”
几个月之后,西蒙终于把我弄到了闹市区,证明老奶奶对他的控制权尚未告终。
一天早上,他带我去见鲍格。“现在要记住,”在电车上时,他警告我说,“别搞鬼。你这是将要给一个老狐狸爷爷做事。他可不容你玩半点儿花样的。干这工作,你要经手好多钱,这事会一直让你够戗的。一天工作下来,如果发现钱有短缺,鲍格就会从你那小小的工资袋里取出补上。你是试用。我见过有些笨蛋就气得走掉了。”
那天早上他对我特别严厉。当时天气十分寒冷,地面冻得硬邦邦的,野草在严霜中东倒西歪地立着,河流冒着水汽,火车的汽笛把蒸汽喷向威斯康星似的广阔蓝天。草编座位上的铜扶手已被手磨得雪亮,硬硬的草垫颜色金黄,连橄榄色和褐色外套的褶痕也映出金色。西蒙粗腕上的黄毛更亮,他脸上的汗毛也是如此。现在他脸刮得比以前勤了。他还有了压低呼吸、向街上大声清嗓子的新的粗鲁动作。他的一切都有了变化,而且还在变化之中,但仍没失去那股子能支配我的魁梧壮健、独立不羁的帅气。虽然我的个子已长得和他差不多高大,我还是怕他。除了脸以外,我们俩的骨架不相上下。
我在火车站的工作注定干不好。也许是西蒙的那些警告害了我,我第一天去干活就被扣了工资,惹得西蒙老大的不高兴。我实在不行,每天几乎都要少块把钱,甚至做到第三个星期还是如此。由于每天准许我用的钱只比车费多两角五分——车费是四角——所以根本就无法掩盖住账目上的短缺。于是一天晚上,在搭车回家的路上,西蒙绷着脸,简单地告诉我说,鲍格已把我辞退了。
“人家少给我钱,我又没法追上去要,”我不断为自己辩护说,“他们扔下钱拿了报纸就走。我总不能离开摊位去追他们呀。”
他终于冷冷地给了我回答,充满怒火的两眼冷漠地朝寂然不动的冬日里黑溜溜的铁桥钢缆瞥了一眼,桥下河水中缓缓浮动着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连同垃圾往回倒流着。“你呀,你不会从给别人的找头里扣回那笔钱!”
“什么?”
“还用我再说么,你这笨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