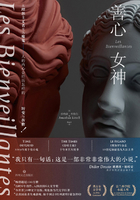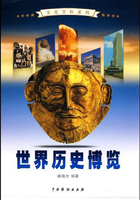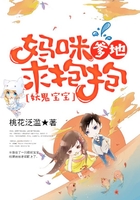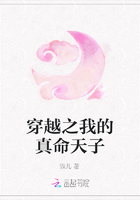一大早,杜玛就穿着簇新的百褶裙去公社领政审表。
近几天,杜玛成了洛加咀村的新闻人物,她前脚走,随后全村人就议论开了,虽然谁也不清楚政审表是怎么回事,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回,杜玛可能真的要走了,真的要去省城念大学了。
以前,村里还只是风言风语,在一片反对的声浪中,人们大都不相信那样的事情会在洛加咀发生,因为自古以来,只有男人才会出去当喇嘛、跑马帮,一个女孩儿会放着好好的家屋不守,偏要到千里之外的省城上什么大学,那岂不破坏了摩梭人的规矩?!
跟早晨出去时的满面春风不同,领表回来,杜玛脸色十分难看,像霜打了似的,大家见了,好生奇怪:咋回事儿呢这是?
杜玛直奔李老师家,别人问话,她都爱答不理。
李老师早年从内地来到泸沽湖北部的一摩梭村落,他不仅是杜玛的老师,还是杜玛的阿咪儿时的老师,在这一带乡村,他是有名的智慧之神,洛加咀村谁要有了难事儿,总喜欢找他请教。
“李老师,这大学我不上了!”
“噢,火气还不小呢,谁招惹你了?”
杜玛掏出政审表桌上一放:“就是它!”
李老师看了看政审表,笑了:“我不信,一个死物,怎么会招惹上你?”
“你看啊,家庭成员第一要填父亲的姓名,比母亲还靠前,在我们这儿,谁拿他当回事儿?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不想知道他是谁!”
“我说小杜玛,别跟政审表过不去好不好,表格本身没错,它是从汉族地区照搬过来的,在那里实行的是男婚女嫁,也就是说,女人大了,要嫁到男方去,生了孩子自然会随男方的姓。”
“不填表不行吗?”
“不可以。在内地,参军、入党、提干、升学什么的,都要过政审关,这是老规矩了,只要是共产党领导,政治永远是第一位的。”
“公社里那个新来的年轻人说了,家庭成员除了填父亲,还有什么祖父、祖母、伯父、叔父;社会关系栏又有外祖父、外祖母、姑父、舅父等等,可咱们这里只有阿咪(母亲)、阿乌(舅舅)、阿日(母祖)、阿普(舅祖),哪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
“公社的办事员可能是汉人,不了解摩梭民族的实际情况,前面我说过,咱这里男不婚,女不嫁,也就没有那么复杂的称呼和社会关系了。”
“要是我去了那儿,他们会不会把我也给嫁出去呀?”
“哈哈哈——”
几乎与杜玛和李老师谈话的同时,一个具有爆炸性的消息开始在洛加咀村传播:杜玛不去念大学了,因为上边要她认父亲!
听到这样的消息,大家心里颇感宽慰,毕竟杜玛才貌出众,谁也舍不得她走。只是,认父亲这件事不禁使乡亲们产生几多联想和感伤,“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上边就曾派来工作组,强迫以走婚为习俗的摩梭人结婚,那时的洛咀村,笼罩在一片世界末日来临般的气氛当中。如今,虽然那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人们仍旧过着暮合朝离的走婚生活,可那段惊险恐怖的经历,在大多数摩梭人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事情的发展好像要故意捉弄人似的,前不久,有好事者传出杜玛放弃上大学的消息,大家也全都信以为真。今天,一条新的消息又在洛加咀村传出:杜玛明儿去县城体检,她很快就要动身赴省城念大学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按说,人家姑娘上大学根本妨碍不到任何人,可那些好事者偏偏不依不饶,向杜玛的阿咪大兴问罪之师:
“不是说不去了吗,这么快就变卦了?”
“俺家杜玛没说过不去啊?”
和那些急赤白脸的人不同,杜玛阿咪一脸的平和、淡定,显得有礼、有节。
“上边叫认父亲她也认?”
“这、这都哪挨着哪啊!”
“姑娘那么小,你就舍得让她走那么远?”
“舍得。”
“你不怕她在外面被人娶了去?”
“可大学是学习的地方,不是谈婚论嫁的地方啊。”
“念完大学以后呢?”
“随她自己。我是希望她见了世面、学了知识还回来,为咱家乡繁荣进步做贡献。”
“……”
那几个人一时被咽得说不出话来了。
杜玛阿咪还是学生时,她就曾向往过外面的世界,一心想走出这大山,只是苦于没有机会,最终,只得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如今,当幸运之神向女儿杜玛招手时,她怎肯让机会白白溜走?
这时候,杜玛从外边回来了,见此阵势,她笑着言道:
“感谢阿乌阿普对我的关心,大人们请放心,我不会在省城嫁人的,学成之后我还回咱家乡,像李老师那样教书育人,让孩子们都成为有用的人才。”
至此,那几个人只有选择尴尬地离去。
“杜玛,你真是我的好莫!”
听到阿咪的夸奖,杜玛脸一阵通红……说实在的,出于内心对那个遥远的陌生世界的畏惧,杜玛自己也曾犹豫过,要不是李老师和母亲的支持鼓励,告诉她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告诉她走出去天高地阔前途无量,她早打退堂鼓了。
杜玛终于踏上了征程。第一次出门远行,就让她当了一回马帮,铃儿响声叮当,马儿驮着草料和行李,沿着崎岖的山路向县城进发。
杜玛从未到过县城,四周高耸的大山阻隔了这里与外界的联系,她去过最繁华的地方就是公社所在地,她经历过的最大场面就是每年转山节和转海节。
从县城到州府,她乘上了公共汽车,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使她感到特新奇特兴奋,然而,这美好的感觉很快就被突如其来的晕车和呕吐冲得杳无踪影。
马儿——汽车——火车,一个比一个快;县城——州府——省城,一个比一个大,这一切,无不给她带来心灵的震撼,而僻静的小山村与喧嚣省城的巨大反差,更让她产生天上人间的时空颠倒,使她分不清自己身处现实世界还是太虚幻境,耳边时不时有人声鼎沸和火车的声响:呜——哐、哐……
然而,大学校园毕竟是人的心灵得以净化和升华的地方,它把城市的热闹和喧哗挡在了外面,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杜玛慢慢恢复了心智,准备迎接崭新的大学生活。
谁料,随之发生的一件轰动整个师范学院的事件把杜玛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那是个星期天傍晚,夕阳西下,同学们饭后散步纷纷来到学院内的沉绿湖畔,或谈心,或饶有兴味地欣赏这怡人的景致。而杜玛的出现很快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她的百褶裙和摩梭头饰以及她的美貌无不令在场的同学惊叹。
杜玛也注意到了那些热辣辣的目光,她心里自然十分得意。以前过春节,在家乡泸沽湖畔跳锅庄舞的篝火晚会上,她同样受到小伙子们的狂热追捧,此时此刻,她仿佛又找到了以前的自己,那情状,宛若一高傲的公主。
她将目光投向了湖水。
这片湖水,跟老家的温塘略大一点儿,蓦地,她感觉浑身燥热难当,从心底产生一种亲近它投入到它怀抱的冲动。于是,她开始脱衣宽带,将百褶裙、内衣、内裤扔在地上,然后,不慌不忙朝湖心走去。
人群里爆出一阵惊呼:“快看——”
“天哪,莫非她疯了!”
众目睽睽之下,居然会出现一个赤条条、白光光青年女性的身子,这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大学校园内绝对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杜玛被带到了教务处。
在教务处办公室,杜玛根本不知自己惹下的事端有多严重,反倒表现出一脸的无辜。先找她谈话的,是一穿白大褂的医生,那人问话慢条斯理的,倒挺客气;随后跟她谈的领导可就不一样了,脸拉的老长老长,态度异常严厉,只不过,那位领导说了半天,她一句也没听明白,什么“有伤风化”,什么“流氓不端行为”,在他们摩梭人的字典里,根本就找不到那样的词语。
由于杜玛拒不认错,最后,校方以“犯有严重的作风问题且态度恶劣”为由,做出了开除她学籍的决定。
就这样,未满一个月,杜玛又孤雁般飞回了洛加咀村。
村民们对杜玛的去而复返表现出难得的平静和宽容,尤其那些当初的极力反对者,他们似乎早已料到了这一天,无论如何,哪儿好也不如家屋好,格姆女神山和泸沽湖牵着杜玛的灵魂,即使她走到天涯海角,也会把她拽回来。
回家后,杜玛一直闭门不出,除了愁闷,便是困惑,有一个问题让她百思不得其解:我究竟犯了什么错,单凭在水塘洗洗身子就把我开除,太不讲道理了吧!
阿咪劝她:“咱哪,没上大学的命,就老实在家呆着吧。”
阿乌一旁随声附和道:“省的让人说你心野。”
有时,杜玛自己也想死了那条心,可她无论如何就是做不到,也许她心真的变野了。以前,没走出过家门,觉得住“木棱子”房屋,砍柴、打草、放羊,虽平淡无奇倒也恬静舒适,并且,这儿的人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然而,有了在省城那一段时间的经历,心劲儿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她开始觉得这木楞子房是那么的昏暗狭窄,整个洛加咀村乃至泸沽湖地区都是那么的封闭、落后。与此同时,她越发地怀念曾经属于自己的大学校园,她留恋的并不是那里的高楼大厦,而是那里独特的与别的地方不同的氛围,那里边的老师,都是大学问家,一个个气质高雅、彬彬有礼;那里边的同学,不管来自何方,一个个都是那么的有文化、有教养,那里,是年轻人的世界,那里,是思想的圣地、精神的家园。
阿里·扎巴是杜玛在村里唯一的阿注,杜玛离家去省城读书的这些日子里,他一直闷闷不乐,现在,自己日思夜想的阿夏杜玛又回来了,他怎能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这天晚上,他悄悄来到杜玛花房,结果,让他吃了闭门羹。
以前,阿里·扎巴可以说是村里最幸运的小伙儿,因为,追求杜玛的男孩子太多了,而杜玛又是那么高傲,别的姑娘十六、七岁就开始结交阿柱秘密走婚了,可杜玛到了二十岁依然独守花房。这期间,有不少和她要好的姑娘悄悄跟她讲述走婚的性爱经历及感受,杜玛听了,倒是觉得很新鲜很刺激,也不时撩拨起她的春心,但那些追求者都难以进入她的法眼,她宁愿选择等待,也不愿让一个自己并不真心喜欢的男子潜进花房来与他共度良宵,体会一下那种被人说的十分美妙的甜情蜜意和销魂荡魄。
阿里·扎巴是个有心计还有点儿腼腆的小伙子,他不像别的男孩儿那么急于表白,朝思暮想的是如何成功进入杜玛的花房。平日里,他总是不声不响地帮杜玛做这做那,上山打柴,他干净利索地把树干剁成小节,再用绳子结结实实扎成两捆;砍猪草,他同样先把杜玛的筐子装满,再装自己的……扎巴无微不至的关照终于赢得了杜玛的芳心,有一次他们在坡地砍猪草,杜玛红着脸大胆邀他晚上去自己花房……
那一晚,杜玛完成了从处女到成熟女性的转变,这时候,距离她离家赴省城上大学不到半年时间。
如今的杜玛已经不是以前的杜玛,况且,她又正处于痛苦和烦闷之中,怎会与并不再相爱的男友重温旧好?
见杜玛整日魂不守舍的模样,阿咪心里比谁都着急,老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忽然,她想起了李老师,便对女儿说:
“你何不去找李老师?或许他能帮你拿个主意。”
提到李老师,杜玛不由得眼前一亮,在家独居的这两天,对她来说实在是太漫长太难熬了,自己咋就没想起李老师呢?
杜玛终于走出了家门,直奔李老师家。
李老师听说杜玛被学校开除学籍的事儿,感到既吃惊又纳闷,他这里正准备上她家询问呢,杜玛推门进来了。
见了李老师,杜玛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一肚子的委屈化作泪水夺眶而出……
李老师并不急于劝她,让她尽情地哭,等她哭够了,才拿出手巾递过去:
“哭得好,在大学里你没这样哭吧?”
杜玛摇了摇头。
“在那儿,你要这么哭上一哭,认个错儿,他们兴许就不会让你回来了呢。”
杜玛点了点头,说:“和校领导吵架是我的错,可我那也是被他们逼的,他们故意找茬小题大做滥施淫威。”
接着,杜玛讲述了事情的详细经过。
李老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杜玛说道:“当众裸浴不对,开除学籍也不合适啊……”说完,他又陷入了沉思。时间在这时仿佛凝固住了,杜玛盯着李老师大气不敢出。
突然,李老师站起身,眼睛望着窗外坚定地说:
“明天,咱们一块儿去省城,为你讨回公道!”
李老师带着杜玛到省城后便直奔省“民委”,在主管民族事务的机关干部面前,他掏出一份申诉书,正是靠了这份申诉书,轰动一时的“裸浴”事件才出现了转机。
申诉书是李老师出发前的那个晚上写就的,应该说,这是一篇文笔犀利流畅,论点论证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好文章。文中一开始就谈到,男女裸体共浴,是摩梭人古老的习俗。在我们泸沽湖西北处,有一个名叫“热水潭”的温泉,每当农闲季或逢转山节,这里像朝圣一样隆重、热闹。凡来此洗浴的人,不管是男是女全身裸体,在同一温泉里尽情地、自由自在地相逗相戏,欣赏着异性全裸的身体,也把自己的一切毫不保留地留在异性眼里。摩梭人崇尚自然美,认为世界上最美的形象是健美的人体,其实,这也是本民族一种原始的躯体崇拜。除了男女共浴,摩梭人还有对女性生殖器官和男性生殖器官崇拜的习俗,如,把格姆女神山半山腰的凹处以及俄亚阿布山岩洞内的石凹等视为女性生殖器象征,称其“为女石祖”,大加崇拜。同时,将女神山突起的山梁等视为男性生殖器象征,进行崇拜。文章的最后,李老师指出,党的民族政策,也明确规定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传统文化,对这种习俗上的差异,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通过沟通来达到相互理解和宽容,而不能用简单生硬的方法解决问题。
校方最终撤销了先前作出的开除杜玛学籍的决定,而沉绿湖畔自此多了一块“禁止下水游泳”的警示牌。
重新入学后,杜玛更加珍惜自己这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她在班级里原来基础较差,连普通话都说不好,可凭着她顽强的毅力和加倍的勤奋刻苦,学习成绩直线上升,两年后,便从一个曾被开除过的所谓“行为不端”者转变成了一个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
上大学期间,杜玛一直和李老师保持书信联系。就在那年他们一块儿来省城的火车上,杜玛望着老人一头的白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他老人家偌大年纪了还为自己的事儿奔波劳累!就在她以敬仰、的目光看着李老师慈祥的面容时,凭直觉她产生了一个奇异的念头,但马上被自己否定,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感觉它太荒唐了。
然而,以后的日子里,那个荒唐又甜蜜念头又时不时冒出来挑逗、骚扰她一番。
每当理性和直觉在一起打架,杜玛脑子里总要闪现李老师慈祥的面容,与此同时闪现的,还有阿咪的面容,两个人真的在某些地方有那么一点点相似之处,直觉告诉杜玛,李老师就是你的阿普,或者叫其他什么的亲人;理性告诉她,李老师从外地来,是汉人,不可能是你的阿普,至于其他,填政审表时李老师就讲过,咱摩梭人男不婚、女不嫁,也就没有那么多亲属关系。
如果说,大学前两年大都是以理性战胜直觉而告终的话,待杜玛彻底理清汉民族家庭结构和以父系为中心亲属称谓及社会关系之后,天平便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倾斜了。
原来,我们摩梭人虽然没有父亲、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这些称谓,但事实上他们都是客观存在着的,没有祖父祖母就没有父亲;没有外祖父外祖母就没有母亲,这,对汉人来说是基本的常识,连小孩儿都懂得的道理,可到了以母系为中心的摩梭亲属这里,那些称谓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过去填政审表时杜玛对那么多亲属称谓还一头雾水的杜玛,如今是搞明白了,而且,非但如此,她甚至想让敬爱的李老师对号入座,因为冥冥中她坚信,李老师一定跟自己有某种亲属关系!
他来自哪里,来之前是干什么的,为何来到荒僻蛮夷之地?这些问题,不仅困扰着杜玛,也困扰着洛加咀村的所有人,几十年了,李老师闭口不谈他自己,别人也就无从打听。现在的杜玛又增加了一个更撩人心魄的问题:他,究竟是我的什么人?
也许是太走火入魔了,这年的寒假,杜玛直接向阿咪求助,她想通过阿咪解开心中的谜团,结果,招来一通厉声斥责:
“不好好读你的书,成天捉摸这些乱七八糟的干啥?!”
这钉子碰得真叫干脆。
从阿咪那里败下阵来,杜玛在家老实了没多大会儿,她又去找李老师。当然,她不会再那么傻了,她也明白,从母亲那里得不到的东西在李老师那里同样得不到。再者,人家李老师学识比天高,城府比海深,他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自己也应知趣一点,该问的便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现在,杜玛只是想尽可能多地接近一下李老师,另外,她也想向恩师汇报、展示一下自己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进步和成果。
原先,杜玛只是从本校文学社团油印刊物上发表作品,现在,她拿出的则是一份国内公开发行的铅印文学杂志!李老师迫不及待地打开那本杂志,并很快自目录页找出阿客·杜玛的大名,此时的他,高兴的活像个小孩子……
杜玛在一旁,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读完昔日得意弟子的佳作,李老师连连点头称赞:“你这大学没白上,文化素养得到提高不说,更难能可贵的,是开阔了你的视野,这样,再回望那遥远的小山沟沟,就有了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居高临下的感觉。”
老师精辟的分析使一直沉浸在自鸣自得状态的杜玛一下子清醒过来,她瞪大了眼睛望着李老师,半晌,才蹦出一句话:
“没有您,哪有我的今天!”
“关键在于你自己当初的正确选择。”李老师举着那本杂志说,“设想一下,要不走出洛加咀,至今依旧呆在这深山沟里,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当然了,上大学、发作品,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来不得半点骄傲和浮躁,你还年轻,以后的路会很长很长,记住,一要有理想,二要坚持,另外,还要忍受得住寂寞。孩子,远大目标鼓舞人,奋斗的过程同样魅力无穷,它使你的人生变得更美好。”
李老师语重心长的嘱托,使得杜玛感动不小,原本打好腹稿的让他老人家提供小说“走进女儿国”素材的话最终也没说出口。
转眼间,杜玛就要大学毕业了,前不久,班主任找她谈话,告诉了一个让她既意外、又惊喜的消息:中文系唯一一个留校当大学教师的名额给了杜玛!
然而,当杜玛返回家把这好消息告诉阿咪时,母亲的态度却是坚决反对:
“当初离开时,你是怎么跟父老乡亲说的?”
杜玛呆呆地看着阿咪冷峻的目光,低声答道:“我是说过毕业后回家乡教书育人,可教大学不是能干更大事情么。”
“你不回来,那不真应了村上那些人的话。”
“什么话?”
“在省城被人娶了去呗。”
“阿咪,这分配工作和出嫁是两码事儿,你光记着那些见识短的言语,李老师怎么说的你忘了?”
一提起李老师,母亲马上不吭声了。
在李老师的劝说下,母亲最终还是同意女儿杜玛留校当了大学教师。
几年后的一天,杜玛突然收到母亲发来的加急电报:
李老师病危,速归。
杜玛当即请了假,急往回赶。
回到家,李老师早已归西,乡亲们正按摩梭人习俗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
阿咪先把杜玛拉进自己家的母祖屋,郑重其事地说:“以前,你问过多次,都没告诉你,今天,我把李老师和你、我的关系挑明了——”
“他是你的父亲?”
“嗯!”
“我的外祖父!”
阿咪流着泪点了点头……
杜玛一口气跑到李老师家,跪倒在他老人家的直立棺材前嚎啕大哭:
“李老师,为什么不等我叫一声外祖父,你就走了啊!”
杜玛的哭声慢慢被喇嘛们念经超度声盖住,那十多个喇嘛,或是李老师生前好友,或是李老师的学生。
火化前一天,又有好几位达巴自愿赶来念经,为李老师的灵魂开路……
葬礼结束后,阿咪交给杜玛一个小木箱,杜玛不解地问:
“这里边装的啥?”
“不知道。是李老师——不,你外祖父嘱咐让我把它转交给你的!”
杜玛不由得一阵激动,她小心翼翼打开小木箱,仔细一看:
啊,日记!他老人家的日记!!
打开尘封的记忆,展现在杜玛眼前的,一会儿,是风华正茂的北大学子;一会儿,是英姿勃发的红军战士;最后,又变身为摩梭女儿国里的文明使者……
至此,他是谁,他从哪里来的谜团已昭然若揭,尤其让杜玛兴奋和激动的是,原本搁浅了的“走进女儿国”也一下被重新激活了!其实,把外祖父的这些日记稍加整理,不正是一部很好的自传体小说?
在回省城的列车上,杜玛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她的行李箱,因为她比谁都清楚,这小小的行李箱,装着一个大千世界,那里面,有活生生的人物,迷人的风情;还有历史与文化、人生与梦想、奋斗与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