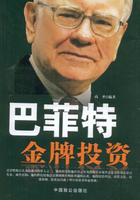夜深深,没有月亮,天上的星星繁多,拉出一条长长的星晕,如十五桃河上飘的明灯,闪闪烁烁。
桃河两岸都是密密匝匝的桃树,春季沿岸都是桃花香,秋季都是诱人的果香,从中流过的河,已被沿岸的桃树包围,因而就叫桃河。游人在不同的季节从中泛舟而下,或白雪皑皑,静逸美妙;或桃花灼灼,烈艳美曼;又或硕果累累,令人垂涎欲滴。
不过,这桃树可不是无主之物,它是和城大户苏家的所属之物,连两岸的地都通通买下。这苏家可不是普通的土财主,听说是上京的大官,几代忠君,轮到这一代,竟是已经封了侯爷。
可不得了。
当然,这只是听说,因为和城当街的苏府,虽然占地宏伟,装修雅致。但它从来都冷漠地似石人端端伫立,俯视蝼蚁般的凡人。它安安静静,从不喧闹,静得似一座死宅,大家都知道,它的主人从不来居住,只有一个年迈的瘸腿老奴,偶尔会在固定的时间开开角门,散散风。
他就坐在侧门半膝高的门槛上,衣衫褴褛,眯着浑浊的双眼,蓬松的胡子黑白相间,挡的连嘴都找不着。最爱懒懒的在太阳底下打盹,手里举着婴儿手臂粗的烟锅,喉咙一动,嘴里鼻子里就冒出浓烈的烟来,像点了一堆篝火,将他整个人都包住了。
这左邻右舍,行走路过的货郎和赤脚大夫都爱和他打招呼,天南地北海聊几句,时日久了,就知他看着糊涂,实则见多识广,有大智慧呢。
可前几日到了该放风的时候,却没有看到老奴勾着旱烟袋出来,而是敞开着大大门。那老奴穿了崭新的衣服,面朝着大路的方向,早早就恭敬的迎在了门口的石狮子旁边。
众人看他一动不动,便笑他,莫不是丢失多年的女儿回来了不成,还这般打扮给谁看?别人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的苏府,总之看到的时候,他就在了,也知道他糟老头子一个,身边无儿无女。
任由他们说的多了,老奴依旧不喜不怒,老这样也无趣,众人便撇撇嘴散了。背过身子却又骂,死了没人埋的老东西,嘴紧的跟蚌壳一样,说一两句就能掉肉不成。
直到中午,两顶青色马车才风尘仆仆而来,那马儿一身滑溜的皮子,在清冷的太阳下折射出一圈白光,它“哼哧、哼哧……”的喷着热气,蹄子上的马掌都磨出了毛边,也不知赶了多久、多远的路。
马车停在老奴身边,老奴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头深深的埋在冰冷的地上,半丝不敬也无,沙哑老迈的嗓音沉着有力,“奴才叩见世子!”
竟然是苏家在上京来人了,还是世子。角角落落偷看的众人一时兴奋,缩头缩脑的找角度,不知能否看到世子长啥模样。
“阿右。”车里传出干涩喑哑的声音,只说两个字,就是一连串急促的咳嗽声。正是天寒地冻,前段时间的积雪刚消,便连着好多天的风餐露宿,就是铁打的人也受不住的。
听得这声,车缘上立马跳下来一个黑衣少年,一把搀住老奴的胳膊,稳稳的将他扶起来。因为是侧站着,所以看不到正面五官的模样,只能听得他的声音,略显疲惫,但对老奴说话却很尊敬,“秦伯,舟车劳顿,有什么话咱们回去说!”
世子从小锦衣玉食,哪里受得了这般颠簸,听这咳嗽声,怕是有一阵子了。想到这里,老奴忙让开路,连声道,“老奴该死,老奴该死……”
那车里又不知说了句什么,车夫轻拍马儿的后臀,嘴里低声一吆喝。那马儿十分有灵性,跟着车夫的吆喝甩甩尾巴,似乎也知道回家了,四个蹄子迈得飞快,稳稳的进了苏府的大门。
留下阿右扶着瘸腿老奴,快步跟在马车后面,进门的那一瞬,阿右突然回了头。眼神凌厉且充满杀意,凶狠犹如一匹饿狼,很快的扫了一眼那些议论纷纷的角角落落。
众人一时噤声,都是心里一寒,汗毛直立,两股战战,仿若下一秒就要人头落地。
大门“砰!”的一声关上。
就这样,安静良久的苏府大门口,不知是谁先发出一声讥笑,不屑一顾的意思。
像捅了马蜂窝,“嗡!”的一下给炸了,大家从角落的阴暗处窜出来站在阳光底下,这次连高高在上的世子爷也给骂上了。端的是个活不长的短命鬼,定是有了肺病,被族亲从上京赶到这里来了,你瞧他给咳得…
要不然,谁爱来这穷乡僻壤般的和城,上京多好啊,那酒楼高的嘞,那马路齐整的嘞,那路上走的女人多的嘞……
啧!众人吸气,那该有多少女人啊……
不过,说来说去,这都是很多天之前的事情了,暂且不提。
且说今夜的月黑风高,一个模糊的人影突然从苏府高墙外面翻进来,正一条腿在左一条腿在右,骑在上面。低头朝里一看,发现在自己摞起来的柴火不见了,她嘴里“咦!”了一声,又是疑惑又是惊奇,待要再看。
忽听墙下一人冷声问,“墙上的人可是秦富?”
竟知道自己的名字,秦富一时犹豫,骑在墙上左右为难,不知是该进还是该退。她要去的可是无人居住的苏府,怕是夜里摸路,走错了地不成。
“看来是了。”阿右自问自答了一句,习武之人在夜间可以明视,秦伯描述过秦富的模样,见了面错不了,刚才那一问,不过是程序使然。
不过,秦伯收的义子,竟是这般不懂规矩,如是想着,阿右又道,“快下来,公子要见你!”声音倒是缓和了不少。
苏府哪里有什么公子,只有一个瘸腿老奴,果是真的是走错了。秦富轻叹,就将垂在墙内的腿往上拉,准备退回去,一边歉意道,“真是不好意思,我走错了,这就离开!”
阿右眉头一皱,不耐烦的握了握腰间的剑柄,又冷了声音,“这里就是苏府,公子从上京来了,要见你,有事情对你交代!”
秦富又将腿垂下来,眼睛一转,想了想,仿佛偶尔听街坊邻居说起过,这苏府是有主之物,而且主人还大有来头,莫不是这主人家来了?她再次低头瞅了瞅,问,“地上的柴火去哪儿了?”
若不是公子看重秦伯,怎会与这如此蠢笨的人在这里费口舌,吹冷风。阿右更是烦躁,直接飞身而上,揪着秦富后颈的领子,用跟抓一条沙皮狗差不多的方法抓着她,给提溜了下来。
秦富初来乍到,没见过什么世面,还是第一次见这种神奇的东西,眼睛当时候就是一亮。脚下还没踩实,身子就靠了过去,吊着肩膀悄声问他,“我说兄弟,这可是传说中的轻功?”
这走哪都快,可太方便了。
还没等秦富的胳膊肘搭到人家的肩膀上,阿右便闪身一躲,让她一个踉跄差点扑倒再地,狼狈的朝前紧走几步才稳下来。阿右嗤笑一声,他平生最是瞧不上这种个矮劲小,没什么本事还整日瞎逛的男子,所以对秦富更是没什么好脸。
“你这小子还是别再啰嗦了,快随我去见公子,耽搁了时间,有你的好酒喝!”若不是公子此番受此折辱,哪里需要来这简陋之处避那些流言蜚语,像秦富这种宵小之辈,更不会会有荣幸见自家公子。
听着语气倒不是吓唬。
说罢,转身就大步离开了。看得出来,他还挺讨厌自己的。秦富悻悻的摸摸鼻子,眼睛突然一转,在黑夜中透出一股机灵气来。
秦富吊儿郎当的抖抖腿,倒是对这个苏家的公子有了丁点好奇,如今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不去也得去了。
这几天她的三观不断被刷新,已经没有下限了,苏家如今是秦富的避风港湾,她有点被吓坏了,想着死活要抱紧秦伯的大腿,然后需要回去睡一觉,压压惊。
……当然,是在见完苏公子之后了。
主院里灯火通明,进进出出的奴仆井然有序,脚步落地无声,微垂着脑袋目不斜视。
秦富等在外面,眼睛滴溜溜的乱看,只是越看眼神越暗,这上京来的贵公子,随身服侍的人都无一女子。
这世道,女子果真稀缺到如斯地步?
冷风一吹,卷起地上的沙土雪粒,秦富不由裹紧了身上的衣服,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脚下不停的踱来踱去。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一股乡土气息,与这雅致的院子格格不入,这种排斥,让人看了真的很难受。
俗称辣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