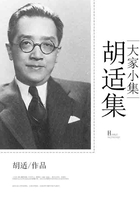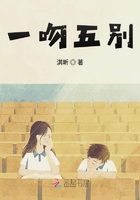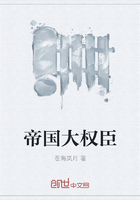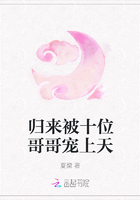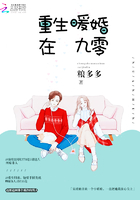1962年,香港友人赠给我一册陆丹林编的《郁达夫诗词钞》,我读后在书的末页空白处写了一首旧体诗:
展读诗词二百篇,两当、海涅忆华年,
寒风凛冽旧书肆,细雨氤氳冷酒边。
浩劫中原家国毁,投荒南岛志节坚;
晨曦将现人长瞑,彩笔难题解放天。
这首诗后半写的是郁达夫晚年不幸的遭遇,惋惜他没有看到全国的解放,他那清新俊逸的文笔也无缘描绘新中国的山水人物了。诗的前半是回忆20年代(主要是1924年)在北京我和几个朋友与达夫交往的情景。
1921年创造社的出现、《创造》季刊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当时不少爱好文学的青年读到作为“创造社丛书”第一种的《女神》,都被那些气势磅礴、富有时代精神的诗篇所震动,他们顿开茅塞,预感新中国将从旧中国自焚的火焰中诞生。不久,丛书的第三种《沉沦》问世了,作者大胆地写出一个久居异国的青年精神上和生理上的忧郁和苦闷,在文艺界激起强烈的反应,它被抱有同感的青年读者所欢迎,也受到一些卫道者的诟骂,一时毁誉交加,成为一部有争议的作品。这时,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一篇评论《沉沦》的短文,给《沉沦》以公平的评价,并启发读者,应如何看待这部小说。此后,《采石矶》《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名篇陆续发表,郁达夫读者的范围也就更扩大了。那时,住在上海的浅草社的朋友林如稷、陈翔鹤常与达夫交往,他们给我写信也有时提到他。
1923年下半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陈启修(豹隐)被学校派往苏联考察经济,他推荐郁达夫代替他讲授统计学。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那时我刚满十八岁,从来不曾拜访过名人,可是郁达夫,我从朋友们的信中知道,他为人如何率真,如何热情,尤其是对待爱好文学的年轻人,这使我下决心要去认识他。当时位于北京北河沿的北京大学第三院主要是政治、经济、法律三系学生上课的地方,我按照学校注册科公布的郁达夫授课的时间和地点,于10月18日下午准时走进一座可容八九十人的课室,里边坐满了经济系的同学,我混在他们中间,我知道,我期待的心情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上课钟响了,郁达夫走上了讲台,如今我还记得他在课堂上讲的两段话。他先说:“我们学文科和法科的一般都对数字不感兴趣,可是统计学离不开数字。”他继而说:“陈启修先生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们讲的是从同一个老师那里得来的,所以讲的内容不会有什么不同。”这两段话说得那样坦率,我感到惊奇,我已经念过四年中学,两年大学预科,从来没有从一位教员或教授口里听到过这类的话。这对于那些一本正经、求知若渴的经济系的同学无异于泼了一盆冷水。而且刚过了半个钟头,他就提前下课了,许多听讲者的脸上显露出失望的神情。可是我很高兴,可以早一点去找他谈话。我尾随着他走进教员休息室,向他做了自我介绍,还说陈翔鹤给我写信常常提到他。他详细地问我是哪省人,住在哪里,学什么,会哪种外国语,我也问他是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对北京有何感想等。我们谈了大约有半个多小时。此后,我再也没有去听他的课,不知他是怎样讲授那离不开数字的统计学的。可是他下课后有时顺路来找我,因为我住在距离北大第三院很近,被称为“三斋”的宿舍里。他约我出去走走,北京的气候渐渐进入冬季,也没有多少可供玩赏的去处,我们多半是逛逛市场,逛逛旧书摊。东安市场里有十几家小书店,出售的书籍中有不少是上海扫叶山房石印的线装蓝布套的诗文集、笔记、小说等。我向达夫说,“我读了你的《采石矶》才知道黄仲则(黄仲则(1749—1783),即黄景仁,清代诗人,字汉镛,一字仲则,号鹿菲子,武进(今江苏常州)人,有著作《两当轩集》22卷。),我的《两当轩全集》就是在这里的一家书店里买的。”他笑着说,“扫叶山房的老板应该谢谢我,我的那篇小说不知给他推销了多少部本来不大有人过问的《两当轩全集》。”关于黄仲则的诗,他并没有向我谈过他在《采石矶》里引用的诗篇,以及“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等名句,他却对《焦节妇行》一诗赞叹不已,他说,“这首诗写的恐怖而又感人的梦境,中国诗里真是绝无仅有,西方的诗歌间或有这种类似的写法。”
有一次,北京刮着刺骨的寒风,我想不起是什么缘故了,我们来到宣武门内头发胡同的“小市”。这“小市”有卖旧衣旧家具的,有卖真假古玩的,也有卖旧书的。(鲁迅在教育部任佥事时,就常路过这里买些小古董。)那天的风很大,尘沙扑面,几乎看不清对面的来人。我们走进一家旧书店,我从乱书堆里,抽出一本德文书,是两篇文章的合集,分别评论《茵梦湖》的作者施笃姆(施笃姆(Theodor Storm,1817—1888),德国小说家、诗人。又译施托姆。)和19世纪末期诗人利林克朗(利林克朗(Detlevvon Liliencron,1844—1909),德国诗人。又译李利恩克龙。)这两个人的诗。郁达夫问了问书的价钱,从衣袋里掏出六角五分钱交给书商,转过身来向我说,“这本书送给你吧,我还有约会,我先走了。”实际上那天我身边带的钱连六角五分也凑不起来。
1923年底(或1924年初),陈翔鹤从上海来到北京后,我和郁达夫见面的机会多起来了。1924年是我们交往比较频繁的一年。
我不止一次地和陈翔鹤、陈炜谟一起到西城巡捕厅胡同他的长兄郁曼陀的家里去看他。他住在一大间(按照北京的说法是三间没有隔开的)房子里,一面墙壁摆着满架的图书,有英文的、德文的、日文的,当然也有中文的。我翻阅架上的书,在一本德文书的里页看到他用德文写的一句话,“我读这书时写了一封信,叙述了对于结婚的意见”。这可能是他在日本留学时写的,可是我想不起来这是一本什么书。这时,他向我推荐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他说,“这篇游记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散文里的一篇,写得真好。”我听了他的话,就找出这本书来读,书中明畅的语言、尖锐的讽刺、自然美景生动的描绘,把一座哈尔茨山写得活灵活现,并引起我的愿望,将来把它译成中文。我们在他那里谈外国文学、中国文学,也谈文坛上的一些琐事。他曾应翔鹤的要求,把他喜欢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开列一个清单,约有二十几种,我记得的其中有斯特恩(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英国小说家。)的《感伤的旅行》、王尔德的《道林·格莱的画像》、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凯勒(凯勒(Gottfried Keller,1819—1890),瑞士德语作家。)的《乡村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屠格涅夫的小说等。有一次我们正谈得兴高采烈,郁曼陀从院中走过,也进来打个招呼,随即走去了。
有时郁达夫和我们不期而遇,便邀我们到任何一个小饭馆里小酌。我难以忘记的是一个晚春的夜里,断断续续地下着迷濛小雨,他引导我们在前门外他熟识的酒馆中间,走出一家又走进一家,这样出入了三四家。酒,并没有喝多少,可是他的兴致很高,他愤世嫉俗,谈古论今,吟诵他的旧作“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直到子夜后,大家才各自散去。
达夫也喜欢独自漫游。那时一般人游览只懂得近则公园,远则西山,达夫则往往走到人们不常去的地方,而且有所发现。一天,大约是将放暑假的时候,他向我说,朝阳门外三四里的地方有一座荷塘,别饶风趣。我听了他的话,便和一位姓张的同学,出了朝阳门,按照达夫形容的方向走去,果然三四里外,看到一片池塘,荷花盛开。我们在池边的小亭里坐下从附近的小饭馆买到包子和面条,也很适口。同时,不远的地方传来管弦清唱的声音。我当时想,这必定是北京本地人的常游之地,外来人不大知晓罢了。我没有打听那地方的地名,也没有再去第二次。如今那一带已是高楼大厦,那荷塘、那小亭,早已寻找不出一点遗迹了。
1925年2月,郁达夫去武昌师范大学任教,这年暑假把他的家属移居在北京什刹海附近,此后他往返于武昌、北京、上海、广州各处,在北京几做停留,都是时间不长,我们见面的机会也渐渐稀少了。
郁达夫有时到鲁迅新居的老虎尾巴、到周作人的苦雨斋闲谈,他跟现代评论社的一部分成员也有交往,他众中俯仰,不沾不滞,永远保持他独特的风度。
庄子的《大宗师》和《天运》里同样有这么一段话:“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煦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鲁迅晚年,写文章和写信一再提到这句话前半句里的“相濡以沫”,这意味着在黑暗重重的社会里,处于困境的进步力量要互相协助,像困在陆地上的鱼吐着口沫互相湿润那样。但庄子全句的主要含义并不在此,而是说与其这样以沫相濡,倒不如回到江湖里彼此相忘。“相濡”与“相忘”是两种迥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但是郁达夫,这两种态度则兼而有之。他对待朋友和来访的青年,无不推心置腹,坦率交谈,对穷困者乐于解囊相助,恳切之情的确像是“相濡以沫”。可是一旦分离,他则如行云流水,很少依恋故旧。我从1926年后,再也没有见到达夫,我们各自浮沉在人海中,除了我仍然以极大的兴趣读他的《迟桂花》《钓鱼台的春昼》等著名的小说与散文外,也就“相忘于江湖”了。
1984年8月27日 写于青岛
附记:
这篇短文是我受陈子善同志的嘱托,为他编辑的《郁达夫回忆录》写的。当时在青岛疗养,资料缺乏,文中所记大都是从记忆里掏出来的。写好后就寄给陈子善同志编审付印,并在《散文世界》1985年第一期发表过一次。后来杨铸同志给我送来他父亲杨晦同志保存的我在20年代写给他的信数封,其中有一信记有顺治门(即宣武门)小市买书事,与文中所记颇有出入。但文已发表,不便改动,仅将信里的话抄在下边,做为更正。由此可见,人的记忆是多么靠不住。
摘录1924年11月30日自北京中老胡同23号寄给杨晦的信:“……今天午后(也是狂风后)我一个人跑到顺治门小市去看旧书。遇见达夫披着日本的幔斗也在那儿盘桓。他说他要写一篇明末的长篇历史小说。我随便买了一本Lilien-cron的小说。他约我到他家喝了一点白干。归来已是斜阳淡染林梢,新月如眉,醺醺欲醉了。”
1986年5月2日 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