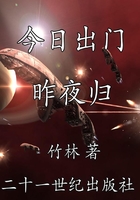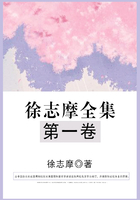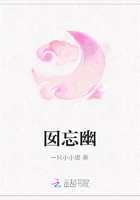一 前言
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近些年来,我总想写点什么,纪念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居住了七年半之久的昆明。可能是由于我对它的感情太深了,拿起笔来,就不知应从何处说起。每逢我写别的文章,只要略微涉及昆明,我便插入几句并非“略微”的话,回味一下我那时在那里的生活。这样写,好像是念念不忘昆明,但是零敲碎打,却冲淡了我比较集中地去写昆明的计划,起着破坏作用。
我怀念昆明,并不是因为它有四季如春的气候和一花末谢一花开的花草树木,也不是由于三百四十平方公里水势浩荡的滇池和横卧在滇池西北角的西山,以及那里著名的寺院与绝壁上的龙门石坊;也不是由于黑龙潭龙泉观里有唐梅、宋柏、明代的茶花,凤鸣山上有17世纪铸造的金殿;也不是由于我经常散步的秀丽的翠湖;更不是由于从昆明出发可以去观赏路南的石林,或者更远一些,西去大理,漫游苍山洱海。这些奇丽的山水花木,不知迎接过多少游客的光临,被多少诗人所吟咏,用不着我画蛇添足,浪费笔墨。我在这里只想写一写我旅居昆明七年半平凡而又难以忘却的往事,也就是说明一下,我对于前边提到的几个问题为什么那样回答。
二 初到昆明
1938年是抗日战争的第二年。我跟随同济大学于10月下旬从江西赣县出发,经过湖南到了桂林,在桂林和八步小住后,又经过平乐、柳州、南宁取道河内乘滇越铁路于12月到了昆明。那正是武汉失守、广州沦陷、长沙大火以后的一段时期,我们一路水上是狭窄的民船,陆上是拥挤不堪的火车和汽车,天空经常有敌机的空袭,晚间在任何一个旅馆或野店里把铺盖打开,清晨又把行李捆好,熟悉的事物越走越远,生疏的景物一幕一幕地展现在面前,一切都仿佛是过眼云烟。在广阔的天地之间,只觉得与狭窄的船和拥挤的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样日以继夜,将永无止境。体力的疲劳与精神的振奋在我身上同样起着作用。一到了昆明,说是要在这里住下,我立即想起杜甫也是在12月到达成都时写的《成都府》那首诗: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
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
但见新人民,未卜见故乡。
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
杜甫由陇入蜀,历尽艰辛险阻,到了成都,眼前豁然开朗,写出这首悲喜交集、明朗的诗篇。我入滇的行程,远远不能与当年杜甫经历的苦难相比,但我反复吟味这几句诗,仿佛说出了我初到昆明时的心境。经过常常有阴雨天气的赣、湘、桂三省,一到海拔二千公尺的昆明,只见天格外清,一切格外明亮,在12月的冬季,和暖如春,街上行人衣履轻便,女人穿着夹旗袍,上边套着一件薄薄的毛衣。真是“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
云南从前对于我是一个辽远的地区,在北平,在上海,我遇见过一些从云南来的朋友和学生,却很少听说有谁到云南去。如今大不相同了,从北平、从上海来的熟人,随时随处都可以碰到。不消说,这是迁移到后方的机关学校把他们带来的。所以在“但见新人民”之外,经常有平时很难见面的亲朋故旧在街头巷尾偶然相逢,彼此在惊讶的同时很自然地一握手,随即异口同声地说: “啊,你也在这里,什么时候来的,住在哪里?”有时也有机会遇见取道河内路过昆明去四川或其他地方的人士。我到昆明不久,在1938年年底,茅盾路过昆明,将飞往兰州,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在一家饭店里宴请他,我被邀参加,在座的我记得有楚图南、冯素陶,这是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唯一的一次与茅盾的晤面。此外,我还在1939年上半年接待过个别过路的朋友如梁宗岱等,既是重逢,又是送别,后来滇越铁路中断,这种机缘也就不再有了。
给我印象更深、帮助更大的是我在昆明结识的“新人民”。昆明人热情好客,可以说颇有古人的遗风,不像北平、上海等大城市的人们那样彼此漠不关心、不相闻问。我在昆明搬过几次家,每家房主人男的常说:“我们是交朋友,不在乎这点房租”;女的站在旁边说:“还不是因为抗战,你们才到昆明来,平日我们是请也请不来的。”这样的话,不管是出于客气,还是出于真情,风尘仆仆的远方的来人听在心里,总是感到一些温暖。更可爱的是小孩子们以惊异的眼光望着我们,听我们对于他们是异乡口音的谈话。我们就在这样和蔼的气氛中解开行囊,安排什物,心里想,这样可以住下去了。
在昆明住下,首先感到的是生活便宜,也比较安定,更加以昆明人朴实好客,不歧视外人,我真愿意把这个他乡看作是暂时的“故乡”。同时从北平、上海来的熟人日益增多,见面时谈谈战争的形势或沦陷区的情况,有许多说不完的话,颇不寂寞。在和青年学生的交往中,精神上也吸取了不少新的营养。
三 通货膨胀
我所提到的第一个优点生活便宜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我初到昆明时,一般物价还用滇币计算,折合法币,显得很便宜。大约过了三个月,商店门前都贴出布告,从某月某日起,所有货物买卖都改用法币。与此同时,从学校里领来的工资,市场上流通多时的旧纸币逐渐减少,崭新的刚出厂的票子日渐增多,大家不言而喻,通货膨胀的阴影渐渐临近了。它先是缓缓地,不久就急剧地奔腾起来,给靠工资生活的人们带来无法摆脱的灾难。战争结束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教授杨西孟写过一篇《几年来昆明大学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实值》并附一表格,在上海《观察》杂志第三期发表。他从生活费指数为一百、薪津约数与薪津实值相等的1937年上半年算起,到1939年上半年生活费指数已上升为二百七十三,薪金约数三百元等于战前法币的一百零九点七元,这是我初到昆明觉得生活便宜的时期。可是下半年就不美妙了,生活费指数上升为四百七十二,薪津约数仍为三百元,实值就下降到六十三点八元,不过,这还说得下去,战争时期大家都应该节俭过日子。此后通货膨胀便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杨西孟在他的文章里说:“自抗战以来,由于物价剧烈上涨而薪津的增加远不及物价上涨的速度,于是薪津的实在价值如崩岩一般的降落。到三十二年(即1943年)下半年薪津的实值只等于战前法币八元。由三百数十元的战前待遇降落到八元,即是削减了原待遇百分之九十八。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上半年薪津实值盘桓于十元左右,这主要是因为米贴按市价计算的缘故。”那么,1943年下半年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呢?表格里表明,生活费指数上半年为四万零四百九十九,薪津约数为三千六百九十七元,实值为八元三角。杨西孟继续写道:“在抗战后期大学教授以战前八元至十元的待遇怎样维持他们和他们家庭的生活呢?这就需要描述怎样消耗早先的储蓄,典卖衣服以及书籍,卖稿卖文、营养不足、衰弱、疾病、儿女夭亡等等现象。换句话说,经常的收入不足,只有销蚀资本,而最后的资本只有健康和生命。但这一切我们在这里不拟加以描写。”表格里的数字是冷酷无情的,是铁一般的事实,表格的制作者说他的目的是“可供目前和今后若干年代研究者参考,特别是关心于社会、经济,以及政治问题的人们的参考”。最后他这样结束:“回视抗战中高度通货膨胀下的昆明生活,恐怕大家都会感觉有如噩梦一场,这份数字也许可以认为(是)梦中的一种记载吧。”
经济学家杨西孟以精确的数字说明国民党统治区恶性通货膨胀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说那些教授们怎样“消耗早先的储蓄”,基本上也是实情。工资低于教授的众多教师职工们,他们的生活会多么困苦,更是可想而知了。可是杨西孟说:“有如噩梦一场”,却未免有些片面。据我看来,噩梦只是昆明生活的一方面,即物质方面,而精神方面,不仅没有贫穷化,反倒一天比一天更丰富(这是后话,我在下面的几节里将要谈到)。总之,我们在昆明过的不完全是一场噩梦,此外还有更多的另样格调的“美梦”。纵使是在“噩梦”里,也有美好的事物值得怀念。
我年轻时读郁达夫的小说《沉沦》,记得其中一首七言律诗里有一联是“乱离年少无多泪,行李家贫只旧书”,我每逢迁居或搬家,常常想起这两句诗。我初到昆明时,已经满了三十三岁,不能说是“年少”了。但自从抗战以来,一路上拖着沉重的书籍,从上海到浙江金华,后来又到了赣县;离开赣县时,觉得前途茫茫,不知将行止何方,这些书,再也不能继续拖来拖去了,于是把书捆成几十包,分为两批,一批寄给长沙徐梵澄,一批寄给成都陈翔鹤,剩下三四十本舍不得离开的书带在身边,既是一种负担,也是一种享受,郁达夫的那两句诗总是在脑子里萦绕着。如今要在昆明住下去,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安放我随身带来的“旧书”。书架是没有的,更不能妄想书橱。不知是谁的发明,从杂货店里买来大约一尺二寸宽、一尺高的装洗衣肥皂的木箱,两角钱一个,靠墙堆起来,就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组合书架”。我也照样办理。把书摆在里边,也不显得怎么寒伧,这真是架不在美,有书则灵。我寄到长沙的书毁于大火,寄到成都的书,后来翔鹤如数寄来,书多了一些,给我这用肥皂木箱组合起来的书架生色不少。
我们在昆明住的地方不是没有电灯,但是常常停电。战争时期,煤油奇缺,买个煤油灯也等于虚设。夜间停电时,照明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泥制的灯碟,注入菜油,点燃用棉花搓成的灯捻,发出微弱的灯光。它被放在桌上的中央,我和妻对坐桌旁,读书、读报、改学生的作业、写诗写文、译书、打毛线以及缝缝补补,后来初入小学的女儿也凑上来温习功课,都仰仗那点微光。我现在视力衰退,四十烛光的电灯泡还感到光照不足,我真难以想象,那时这点如豆的灯光竟能对我们发挥那么大的作用。而且这盏菜油灯,我们还要为它费尽心思,倍加保护,睡前把它用盆子盖好,以防老鼠来偷油吃,白天出门,也照样办理,因为老鼠在白天室内无人时也出来活动。
几只装肥皂的木箱,一盏泥制的菜油灯,始终如一地陪伴着我们在昆明生活,不管生活费指数怎样疯狂地上升,薪津实值又如何急剧下降。因为它们从我们在昆明住下来的那一天起,就符合后来薪津实值的最低水平,它们不能离开我们,除非把“组合书架”里的书卖光,油再也买不起。但是书,我又不肯卖光;油,也只能以节油、省油相告诫。
穷,总有穷的办法。读书时,没有卡片做索引或记录要点,就利用学校注册组发的“学生选习学程单”。这种“选习学程单”,学生每人一张,选课时交给教师,它比正式卡片小一半,它的背面可以代替卡片使用。在昆明的前两年,还买得到商务印书馆的标明年月日的《袖珍日记》,我一年作两年用,一年用钢笔写,一年用铅笔写,以示区别。这样,两本袖珍日记记了四年的事。后来,日记本上不能再记第三年的事,到1943年冬季,日记也就中断了。
杨西孟提到的消耗早先的各种储蓄,除去健康和生命外,我一项也不缺少。首先是我带来的几件“来路货”(当时人们这样称呼外国的进口货),由于昆明地处偏僻,很受欢迎,容易卖出,还可以取得较高的售价。于是照相机、留声机、跋涉千里未忍抛弃的几件玻璃器皿、外国朋友送给我的女儿的玩具等等,都相继与我们含泪告别。其次是从有限的衣物中拣出几件暂时可以不穿的衣服交给寄售店,从舍不得出卖的书籍中挑出几本目前不需要的书卖给旧书店。写文章换点稿费,自然不在话下。妻在赣县重病之后,得不到适当的营养,体温长期在三十五度左右,我则不断生病,回归热、斑疹伤寒、疟疾,以及背后的疽痈,女儿患百日咳和不起免疫作用的各种麻疹,却都没有导致付出最后的资本“生命”。出乎意料,每次病后,反而换回来新的健康,上课、写作、与朋友和学生交往,好像更有精神。妻的体温恒低,仍然坚持教学和家务工作,不感到疲劳。在这一点上,我们跟杨西孟所开列的最后要销蚀的“资本”,就略有不同了。“新的健康”和“更有精神”的由来,分析起来也并不悖乎常情,一来我们那时正是三十几岁的壮年,二来是抗日战争在鼓舞着我们。
四 空袭警报
初到昆明时感到的好处,一是生活便宜,二是比较安定。如前所述,“便宜”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紧跟着与“安定”相反的不安定也接踵而至。在战争时期,全民族生死存亡之秋,本来不安定是正常的,安定反而是反常的。自己想过安定的生活,是没有出息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