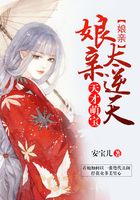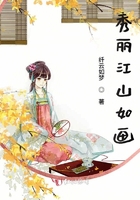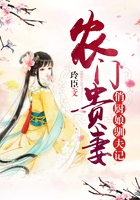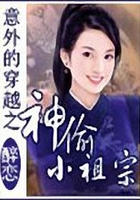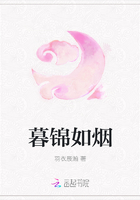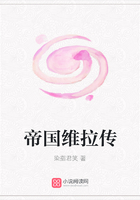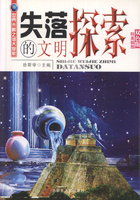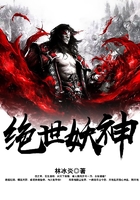转过放生活水源,又过雨清台,允谚他们便到了滴水观音殿了。
此处台基很高,青天映下,白云霁彩。庭中有一泉台,清水蜿下,苍石空润,泉台下有着露净瓶,水自瓶口入,又自瓶底出,恍如众生烦恼,贯流而周始。庭院两旁植着滴水观音,绿掌悠低,向日奉十,清枝亭亭,覆蔓交垂。合殿以清水杨木修成,梁柱简洁,只浮雕以飞花祥云,佛手万变。
允谚与饮秋走近了,只见两边的滴水观音前还各支着一块小木牌,提醒游人香客这仙草有毒,不可妄食妄抹。
“饮秋,果如你所说呢。”允谚笑着,便轻捷地向殿中跑去了。
“允谚!”饮秋唤了一声,含着无忧的喜笑,住步于庭中,未肯向他走去呢。
“饮秋。”允谚回过头来,笑道:“现在天已热起来了呢,你可将斗篷解了?”
饮秋拉了拉颈上的系带,终是未解。明亮的晴光照了下来,不甚柔软,有些灼灼地烧人。一抬头,却见允谚已跑回到了她身边。她望着他,一霎明媚,自将篷帽揭了去。露出那垂云千回的绛仙髻和轻铅薄黛的素秀容颜。
“饮秋,我听我父王说,这滴水观音的法相始现于东晋时,那时中原为五胡所据,战乱连年,民不聊生。后来,来了一个西域胡僧,法号叫昙无谶的,他治好了北凉国主沮渠蒙逊的重病,又劝其诚颂《法华经普门品》,以慈爱之心度国。终北凉六十余年,河西一带终成善土。后柔然攻破高昌,国君安周被杀,北凉遂亡,战乱又起。但佛法已固人心,黎庶流民们依照着《法华经普门品》的指引,于危亡烦恼时念诵‘观世音’,其时,世人多谓于恍惚呼唤中遥见观世音法相浮于空中,一点慈泪,垂掌零露,见之者,便得妙法解脱。”允谚望了望饮秋:“佛在人心,妙法解脱,饮秋,你信么?”
饮秋点了点头:“我信。”
那时的兵戈与乱世,也同她见过的一样吧。从容戮死辈,无生无惧,无有恐怖。
“父王说,这就是滴水观音了。我后来也粗查了几本经籍,却是没看到过。”允谚笑了笑,超脱似地:“我父王是个书痴,文痴,金石古物痴,他同我说过的许多故事都是别处看不到的呢。”
“你说的话,也都是别处,听不到的呀。”
长风乍起,吹动了他们的衣摆环佩,饮秋举目望天,青云融和,却不见慈悲浮屠。
两人说着,已行到了殿外了。殿中香客不多,清雾自莲烛中徐徐升腾,缭绕着雾帐缓幔,直攀向那滴水的佛掌,垂泪的佛眼。殿中悬着一匾,上以青墨书着“慈航竞度”四个笔走徐迂的没骨字。
饮秋悄声一笑,顽道:“还记得我同你说的么?我是妖,不知会不会被菩萨收压了。”
“你是精灵!”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慕予兮。
允谚低压温情的声音缠在清烟中,引向冥冥,轮回空里。
“君思我兮然疑作,路幽杳兮不得归。”她已合掌,仍自滟波顾盼。
这滴水观音的法相由琥珀冻石铸成,高约两人,是一副清秀端蔼的女相。一掌粲若拈花,一掌指尖滴水,双眼闭却,眉目稍低。
“我也听过一个传说,观世音菩萨是自苦海中生出的。”饮秋说着“苦海”,心中已无了惧痛,只余晦淡的追忆,怨慕摇曳,空自殇美。
“苦海生出的慈悲,这传说很美呢。”允谚望着眼前的滴水观音,脑海中浮现出了腥红色的苦海,遥接着西天的极光,无边无际,无望慈悲。
不知道,他想中的苦海,与她所见的,可是一样的。
“是很美啊!”二人相契一笑。
“噗”的一声,火折便在莲烛上点燃了,青烟袅袅,缕逝空中。寺僧们管佛前的供奉称作“长生”烛,长生的明光,清虚摇若。
二人出殿时,敲木鱼的老僧缓缓抬头瞧了二人一眼。
“行深般若,露水朝暮。来来去去,夕花夕落。”老僧说罢,木鱼又是一响,回音无际,沉鸣心底。
饮秋怔住了,思量平生所闻,不知何时何地何语成谶。
“走吧。”允谚扶住了饮秋,细声呵护道。
“因汝为缘,缘生缘灭。”木鱼又是一响,却叫殿中一个正在拜忏年轻的僧人听到了,那僧人立起身来,惊痛似地一回头,却瞥见了饮秋清渺的背影。他忙追了出来,终未能追上。
这僧人便是聂胜琼的爱人,柴王府的公子,柴与俊。
路尽隐幽处,香远茜裙归——遥怜臂上梅痕新,却东风,别啼筠。望着饮秋与允谚远去的身影,柴与俊忽泪下不止。
这一幕,恰被路过的赵允谊看见了,赵允谊走在殿侧的廊道上,识出了柴与俊,而后阴幽地一笑,窃生欢喜。
“无牵无离,不远不近。莲花生泪,泪落成莲。”
木鱼声回荡在滴水观音殿中,长生烛的光晕明明灭灭,青帐随烟慢拂,拂过俯照众生,大慈大悲的佛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