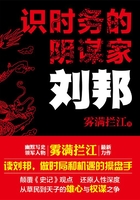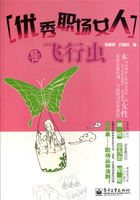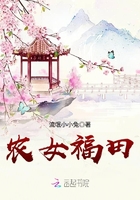《诗经·小雅·大东》中有这样的句子:“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其实,启明与长庚都是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金星的别名。金星是大行星中跟地球最接近的一颗,自东向西逆转。因金星运行轨道所处方位不同,人们将黄昏见于天际的金星称为长庚,将凌晨见于天际的金星称为启明。鲁迅不到一岁时,曾拜绍兴长庆寺龙师父为师,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后来也偶尔用作笔名。说来也巧,鲁迅二弟周作人的字,叫作启明。据许钦文的四妹许羡苏回忆,鲁迅的母亲曾对她说:“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
这种说法当然带有迷信色彩,但用“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比喻周氏兄弟的失和,则不失为一种形象的说法。
鲁迅与周作人青少年时代“兄弟怡怡”的情景早为人们所熟知;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并肩战斗的业绩,也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查阅鲁迅和周作人的日记,直到一九二三年上半年,他们还维持着兄弟之间的正常关系:他们在八道湾一起生活,共同指导北京大学春光社的文学青年,多次与中外友人聚餐品茗……当年六月,他们一起在日文《北京周报》上发表了题为《“面子”与“门钱”》的谈话;他们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以周作人个人的名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直至当年七月三日,兄弟俩还同去东安市场和东交民巷买书购物。七月十四日,《鲁迅日记》中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周作人同日日记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七月十七日,周作人日记记载:“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七月《小说月报》收到。得玄同函。”周作人承认,这则日记原来还有大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后来被他“用剪刀剪去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池上来诊。”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癔病,经常歇斯底里大发作。周作人同年一月七日日记中,就有“信子发病,池上来诊”的记载。二、鲁迅当天日记中毫无与家庭矛盾有关的内容。七月十八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全文是“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7月18日,作人”。这天晚上,淫雨霏霏,给八道湾院落增添了几分凄清。七月十九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的记载。鲁迅当天日记记载:“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当晚,“大雷雨”。原来“兄弟怡怡”的鲁迅和周作人从此决裂,恰如杜甫《赠卫八处士》诗中描写的那样:“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由于鲁迅与周作人曾以“周氏兄弟”的合称蜚声“五四”文坛,他们的失和自然引起了广泛的议论。但是,对于这件事,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持“不辩解”的态度。他的借口是:“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做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么。”至于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乔峰),正巧在当年五月十四日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庭纠纷,事后鲁迅也未跟他谈过。这样一来,就更给鲁迅与周作人失和这件事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鲁迅去世之后,有人陆续在回忆录中提及此事,试图从不同角度揭示这一事件的真相。据我手头掌握的资料,最早谈到此事的是郁达夫。一九三九年,郁达夫在《宇宙风乙刊》上连载了《回忆鲁迅》一文。文中写道:“据(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弟兄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一九四二年,曾经与鲁迅编辑过《莽原》周刊的荆有麟,在《文艺生活》的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鲁迅眼中的敌与友》一文。文中说:“据先生讲,他与周作人翻脸,是为了这样的事情——他们两个人,有好些共同的朋友。即某人是鲁迅的朋友,也是周作人的朋友,所以有时候朋友写信来,虽然信是写给两个人的,但封面收信人姓名却只写一个,鲁迅或者周作人。因为他们弟兄,本来居住在一块,随便哪一个收信,两人都会看到的。有一次,一个日本朋友写信来,而且是快信,封面写的是周作人,鲁迅自然知道是谁写来的。恰恰送信来时,已是晚上,周作人已经睡了。鲁迅先生看是他们共同朋友写的快信,怕有什么要事,便将信拆看了,不料里面却是写的周作人一个,并没有与鲁迅有关的事情,于是第二天早上,鲁迅将信交与周作人……却不料周作人突然板起面孔,说‘你怎么好干涉我的通信自由呢’,于是两人便大吵起来,鲁迅终于还搬了家。”一九四七年,鲁迅挚友许寿裳在上海峨嵋出版社出版了《亡友鲁迅印象记》,书中《西三条胡同住屋》一章写道:“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一九五九年,许广平在撰写《鲁迅回忆录》一书时,专门安排了《所谓兄弟》一章,披露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的矛盾。一九八三年六月,周建人撰写了《鲁迅和周作人》一文,发表于《新文学史料》同年第四期,介绍了他的两位兄长的关系的始末。因后两种资料容易觅得,故不一一引述。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曾经指出:鲁迅与周作人决裂的问题,是经常被读者问起的问题,是千千万万研究鲁迅的人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一般人所不易了解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弄清这一事件的真相,显然并非是多余的事情。加之近年来,海外有人对此事妄加评议,甚至武断地认为此事“可能涉及鲁迅人性方面的弱点”,这就更有必要澄清事实真相,以消除一些人的误解。
在对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的种种回忆中,许寿裳跟郁达夫的说法是比较可靠的。鲁迅兄弟失和时,许寿裳曾以同门学友的身份从中调解,当然洞察内情。郁达夫提供的情况得之于张凤举,而张凤举是八道湾的常客,跟鲁迅、周作人双方都过从甚密(仅《鲁迅日记》中,关于张凤举的记载就有近八十处)。在这场冲突中,周作人夫妇多次向他述及鲁迅的“罪状”,争取他成为“援兵”。所以张凤举对于这场纠葛的内幕,也是有所耳闻的。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三点:一、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不是源于他们双方的直接冲突,而完全是由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挑拨所致;二、羽太信子给鲁迅捏造的罪状——也就是周作人信中所谓“昨天才知道”的那件事,即诬蔑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三、鲁迅起初对羽太信子的造谣毫无所知,而周作人却“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
为了证实上述判断,我们还可以提供三个旁证材料:一、鲁迅有个笔名叫“宴之敖”,十分奇特。他本人解释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敖,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可见鲁迅本人也认为他被“逐出”八道湾是羽太信子造成的。二、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移居西三条新居的鲁迅重回八道湾“取书及什器”,跟周作人夫妇发生一场剧烈冲突。鲁迅当天日记写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明及其妻突出詈骂殴打,又以电话召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明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可见捏造鲁迅“罪状”的是羽太信子,周作人扮演的是“妇唱夫随”的角色,其内容下流,故语多污秽。三、一九六四年六月,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了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一书,其中收入了《鲁迅与周作人》一文。这篇文章篇幅不长,主要是征引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文中写道:“许寿裳曾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周作人收到了鲍耀明寄赠的这本书。他在同年十月十七日致鲍耀明的信中说:“昨日收到《“五四”文坛点滴》,谢谢。现已读了十之八九,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同月三十日在致鲍耀明的信中,他说:“《‘五四’文坛点滴》据我所知道的来说,大抵去事实不远。著者似尚年轻,唯下笔也还慎重,这是很难得的。”同年十一月十六日在致鲍耀明的信中又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唯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笔者认为,周作人基本肯定《“五四”文坛点滴》一书中对兄弟失和一事的说法,也就是从基本事实上肯定了鲁迅日记中的有关记载,肯定了许寿裳关于“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的说法。四、关于羽太信子从中挑拨的具体内容,当时跟鲁迅和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川岛先生曾经谈过。一九七五年,川岛先生曾对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解释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木。”(见鲁迅博物馆保存的章川岛谈话记录)基本弄清了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的起因,人们自然还会追问:“羽太信子为什么要凭空诬蔑鲁迅呢?”不同的知情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相同的。郁达夫在回忆中已点明根子在经济问题。川岛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指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俞芳在追忆鲁迅母亲关于这一问题的谈话时写道:“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贷,是不好的。”许广平回忆,鲁迅曾对她说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也明确指出:鲁迅与周作人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造成兄弟失和”。“鲁迅在教育部的薪水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钱不够用。”
鲁迅曾经感叹道:“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白。”这里所说的“亲族”,不仅包括了周作人,而且包括了周作人的日本亲属。为了供养尚在日本留学的周作人和他的日本亲属,鲁迅毅然中辍了他的留学生活回国谋事。待周作人归国之后,鲁迅不但负担全家生活的绝大部分费用,还要继续资助周作人的岳父、岳母、妻弟、妻妹。一九二五年十月七日,在鲁迅与周作人绝交两年之后,周作人的妻弟羽太重久还在致鲁迅的信中说:“上月蒙兄长给予及时补助,非常感激。长期以来,有劳兄长牵挂,真是无言可对。对您长年以来的深情厚谊和物质援助,真不知说什么才好。”可见鲁迅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的程度。在鲁迅遗物中,保存了三册《家用账》,起于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即鲁迅从八道湾移居砖塔胡同的第一日,止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一日,共两年零六个月。据统计,一九二三年八月至一九二四年二月,平均每月生活费为三十九元四角三分;一九二四年二月至一九二五年一月,平均每月生活费四十八元零六分;一九二五年二月至一九二六年二月,平均每月生活费六十六元六角五分。从这个账目可以看出,鲁迅跟周作人失和之前,他收入的绝大部分都被羽太信子挥霍了。毕生清苦的鲁迅不满于羽太信子这种暴发户的作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料羽太信子不仅不听从鲁迅“花钱要有计划,也得想想将来”的规劝,反而恶意中伤,玷污鲁迅的人格。无怪乎鲁迅与周作人闹翻之后,周老太太对人说:“你们大先生和二先生不和,完全是老二的过错,你们大先生没有亏待他们。”不久,周老太太也愤然搬出八道湾,跟他的长子一起生活了。
由于受了种种诬蔑委屈,鲁迅搬出八道湾后大病了一场,但他“不喜欢多讲”,直至临终前一个月才写信告诉自己的母亲(鲁迅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致母亲的信)。对于羽太信子的凶悍,鲁迅十分愤慨;对于周作人的昏聩,鲁迅深表痛心。然而,自从兄弟失和之后,鲁迅没有公开对周作人进行过多的批评,反而时时默念着尚未泯灭的手足之情,唯恐周作人步入歧途。
一九二五年十月,鲁迅用抒情诗的语言写出了著名的小说《伤逝》。作品中的主人公涓生和子君是“五四”时期为婚姻自主、恋爱自由、人格独立等新思潮所激荡的青年男女的典型,并不是影射比附现实生活中任何人,这是无可争议的。然而鲁迅选择“伤逝”二字作为篇名,的确蕴涵着他某种情感的瞬间波动。同年十月十二日,也就是鲁迅写成《伤逝》的九天之前,跟鲁迅关系极为密切的《京报副刊》上刊载了罗马诗人卡图路斯的一首短诗,译者“丙丁”(系周作人笔名),题目就叫《伤逝》,全文是:
我走尽迢递的长途,
渡过苍茫的大海,
兄弟呵,我来到你的墓前,
献给你一些祭品,
作最后的供献,
对你沉默的灰土,
作徒然的话别,
因为她那运命的女神,
忽而给予又忽而收回,
已经把你带走了。
我照了古旧的遗风,
将这些悲哀的祭品,
来陈列在你的墓上:
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
都沁透了我的眼泪;
从此永隔冥明,兄弟,
只嘱咐你一声“珍重”!
这首诗在《京报》副刊上发表时,有特意说明:“这是诗人悼其兄弟之作。”诗的右侧配了一幅比亚兹莱所作的插图:一个人举起右手,“表示致声珍重的意思”。无怪乎周作人读了小说《伤逝》之后,会觉得这篇小说“乃是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