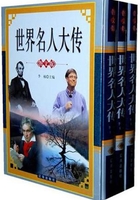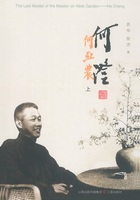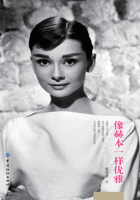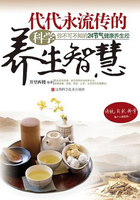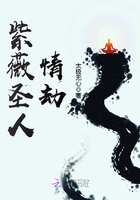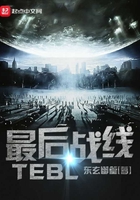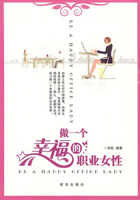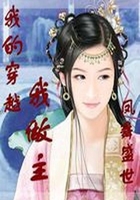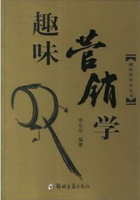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两点钟,在上海北四川路的一间咖啡馆里,鲁迅一家人亲切地会见了两位东北流亡青年:萧军和萧红。这间咖啡馆只有一间门脸儿,座位不多,光线有些昏暗,因此顾客颇为寥落。但鲁迅却常到这里来,一边喝红茶或咖啡,一边跟左翼文化战士聚谈。店主不知是犹太人还是白俄,胖胖的,听不太懂中国话;而且顾客一到,他就习惯地打开留声机放起唱片来。这种环境,对于过着半公开半隐匿生活的鲁迅是十分适宜的。
萧军和萧红都是对于温暖和爱怀着美好憧憬和执著追求的人,但他们的身世又都充满着悲凉和凄楚。萧军原名刘鸿霖,六个月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他从小醉心于武术,一心想要闯荡江湖,除暴安良。十八岁那年,他开始了戎马生涯;三年后,考入了张学良主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这一时期,他刻苦地自修文学,并发表了处女作《懦……》,控诉军阀蹂躏士兵的罪行。一九三〇年春,萧军因反抗学堂步兵教官的辱骂而被开除。“九一八”事变后,他密谋组织抗日义勇军,不幸失败。此后,他逃亡到哈尔滨,开始了坎坷曲折的文学生涯。
跟萧军比较起来,萧红的命运则显得更其不幸。萧红原名张迺莹,本是一个活泼而聪慧的姑娘。她的腿肚很细,跑起来脚尖向内,活像一只小麻雀。一犯困、一打哈欠的时候,她的泪水就浮上了双眼,俨然是一只小海豹。一遇到什么惊愕或高兴的事情,她的两只手就左右分张起来,跟一只小鹅一般。她的童年寂寞而黯淡。萧红二十岁那年,家里将她许配给了一个富家的浪荡公子,以图获取两千元的聘礼。萧红十分鄙弃那种锦衣玉食、一呼百诺的少奶奶生活。她斩钉截铁地回绝了这门亲事,逃出了她的故乡——号称“花都”的呼兰小城,流落到了纸醉金迷的哈尔滨。一九三一年,在未婚夫汪某百般无耻的纠缠和欺骗下,萧红被迫跟他在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同居了半年多,积欠旅馆食宿费达六百多元。汪某托言回家取钱,把即将临产的萧红作为“人质”留在旅馆,自己逃之夭夭。旅馆将萧红幽禁起来,准备伺机将她卖进妓院押身抵债。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萧红给当地的进步报纸《国际协报》写了一封凄切动人的求援信,该报副刊的编者委托萧军去核实一下情况。一九三二年夏季的一天黄昏,萧军在旅馆的一间霉气冲鼻的房间里找到了萧红。当他看到这位刚满二十二岁的女子头上竟长出了明显的白发,粗瓷碗中只剩下了半碗坚如沙粒的红高粱米饭的时候,便暗自决定竭尽全力拯救这晶莹美丽的灵魂,用自己的臂膀为萧红遮蔽暴风雨。当时正值松花江水位暴涨,洪峰呼啸着冲垮年久失修的江堤,淹进了市区。趁旅馆茶房忙于堵塞洪水的时候,萧红从窗口爬出,逃上一只柴船,逃离了虎口。这年秋天,萧红和萧军在哈尔滨的商市街结婚,开始在荆棘塞途的文学道路上携手并肩地跋涉。当东北文坛上充斥着歌颂“王道乐土”的汉奸文学和《长相思》《十二金钱镖》一类言情武侠小说的时候,萧军和萧红以其具有革命倾向性和鲜明时代性的作品揭开了东北革命文学新的一页。由于他们的创作活动跟中华民族的反帝爱国斗争息息相通,身穿长袍马褂、故意把帽檐压得很低的日伪特务在暗中盯上了他们。一九三四年六月,萧军和萧红从哈尔滨秘密出走,乘“大连丸”邮船的四等舱流亡到了青岛。同年十一月,他们又挤在日本船“共同丸”的货舱里,与咸鱼和粉丝等杂货为伍,一起漂流到了上海。从此,他们得到了鲁迅慈父般的关怀和教诲。还是困居在东兴顺旅馆的时候,萧红曾经写过一首《春曲》,抒发她对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和向往之情:“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然而,萧军和萧红文学生活中的春天,却是在结识鲁迅之后才真正开始的。
萧军和萧红清楚地记得,就是在咖啡馆的这次难忘的会见,鲁迅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二十块钱,帮助他们维持稍微安定一些的生活。萧红接过鲁迅用血汗换来的钱,觉得内心刺痛。鲁迅写信安慰说:“……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元,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不久,鲁迅又对他们公开了自己的住处,使这两位看够了人间冷酷面孔的青年能够随时来访,感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萧军常常想,他好比是一缸豆浆,而鲁迅却是一滴卤水,这卤水一滴下去,他思想中新的、向上的东西就渐渐上升,而浊的东西就渐渐下降了。命运比青杏还酸的萧红,内心常有难以排遣的哀怨,就像用纸包着的水,不可能不让它渗出来。但在鲁迅面前,她长期压抑在心底的郁闷常常会被驱散,如同阳光冲出了阴沉的乌云。最使萧军和萧红铭感不忘的,是鲁迅对《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这两株文苑新苗的精心扶植。
《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都是一九三四年初冬时节完成初稿的。同年十月底,萧军、萧红在青岛将《生死场》的文稿邮寄给了鲁迅;同年十一月底,他们又把《八月的乡村》的抄稿交给了鲁迅。一九三五年春,鲁迅开始认真审阅这两部字迹潦草而又细小的稿件,订正错字,修改格式,肯定优点,指出不足,并亲自撰写了序言。鲁迅热情地肯定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是一部很好的小说,因为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揭露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显示着中国的一部分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这部作品不仅驮载着作者个人过去的苦痛与欢情,也烙上了我们古老民族的耻辱和光荣的印记。审阅萧红的《生死场》时,鲁迅更吃惊于“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就手法的生动而言,《生死场》似乎比《八月的乡村》更成熟一些。一位纤弱的小辫子姑娘,居然能把“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描绘得“力透纸背”,这是多么令人欣喜的事情啊!
《生死场》本来是准备争取“合法出版”的。但是,“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为了打破国民党政府对革命文艺书刊的查禁,萧军、萧红和另一个左翼作家叶紫找到一家可以欠债的印刷所自费印行他们的作品,除《生死场》外,还印行了《八月的乡村》和叶紫的短篇小说集《丰收》。当书开始装订的时候,叶紫向萧军提议:“我们的书虽然是‘非法’出版的‘私书’,也应该大大方方像本‘公书’的样子,譬如有个‘社名’,有个发行的‘书店’,采用‘私盐官售’的战法遮掩敌人的耳目。这于买书和卖书的人都方便些。”萧军欣然赞同。于是,叶紫虚构了一个“容光书局”的名字;萧军从《国际歌》的歌词“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中受到启发,取“奴隶”二字作为社名。萧军解释说:“我们本人和广大人民今天所处的境地还不正是这种‘奴隶’的境地吗?奴隶和奴才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奴隶要反抗,奴才要顺从……”萧红和叶紫对于是否确定这个社名感到举棋不定,大家决定还是请示一下鲁迅先生。鲁迅说:“‘奴隶社’这个名称是可以的,因为它不是‘奴才社’,奴隶总比奴才强!”于是,“奴隶社”这一名称就正式确定下来了。从一九三五年三月至十二月,《丰收》《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作为奴隶社出版的“奴隶丛书”先后问世。他们在《小启》中豪迈地宣布:“只有战斗才能解脱奴隶的命运!”
“奴隶丛书”出版后,在进步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初版很快就销售一空。鲁迅还将这些作品介绍到国外,使国际友人从中了解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向世界显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战绩。与此同时,“奴隶丛书”也受到了来自敌对营垒和左翼文艺阵营内部的攻击。首先跳出来狺狺狂吠的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潘公展主办的上海的《小晨报》。该报在用化名发表的文章中,诬蔑叶紫的《丰收》内容“过火”,萧红的《生死场》内容“芜杂”。他们还造谣说萧军新近“自苏联归国,为共党走卒”,妄图进一步施加政治迫害。鲁迅对于敌人的攻击极为藐视,他在致叶紫的信中说:“……他们只管攻击去,这也是一种广告。总而言之,它们只会作狗叫……”但是,鲁迅又提醒叶紫等人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他在同一封信的附言中说:“狗报上关于你的名字之类,何以如此清楚,奇怪!”
鲁迅的怀疑并不是多余的,长期的斗争实践使他懂得,正面的敌人固然必须提防,但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敌对势力之所以能了解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些内情,看来跟混进“左联”内部的“蛀虫”有着密切的关系。就在《小晨报》上的文章发表三个月之后,一个化名“狄克”的人在《大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跟“狗报”的“狗叫”遥相呼应。这位“狄克”先生首先对《八月的乡村》勉强作了几句虚情假意的肯定,而后就阴阳怪气地进行含糊的指责,使人以为这部作品坏到了茫无边际的地步。他还力竭声嘶地呼吁批评家对《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执行自我批判”,并且危言耸听地说,不这样做,就是“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
《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艺术上不无粗糙或幼稚之处,这本来是毫无疑义的。鲁迅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八月的乡村》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比不上法捷耶夫的《毁灭》。他主张删减小说中那些“说明而非描写的地方”,因为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主观议论以少为是。鲁迅还曾公开批评《生死场》“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换而言之,就是认为萧红描写人物的技巧不及她叙事写景的技巧。但是,鲁迅洞察到,“狄克”的所谓“自我批判”,并不是出于善意的批评,乃是盗用革命口号打击新生力量,用“求全责备”的手段扼杀进步文艺。这无异于在坦克车和烧夷弹尚未制成的情况下,就首先折断了对敌斗争的投枪。为了反击“狄克”之流的挑战,鲁迅专门撰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揭露“狄克”在“正确”或“公平”的假象掩盖下,向国民党献媚或替他们缴械。《三月的租界》这一篇名,正与《八月的乡村》书名相对,辛辣地讽刺“狄克”之流躲在上海的租界里,一边“住洋房,喝咖啡”,一边干着扼杀革命的民族力量的勾当。无怪乎“狄克”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指责《三月的租界》题目很伤了他的“感情”。一九三六年四月,“狄克”又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为了表示“最高的轻蔑”,鲁迅没有直接答复,而是在《〈出关〉的“关”》一文中再次揭露,“狄克”之流对于“新作家的努力之作”是“群起而打之,唯恐他还有活气,一定要弄到此后一声不响,这才算天下太平,文坛万岁”。鲁迅就这样顺手一击,用论战的方式保卫了生机勃勃而一时还有些荏弱的文艺幼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