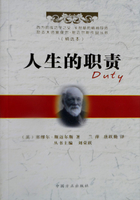虞战抱着男童和他们玩的开心,太后欣慰的看着虞妁,对男童的母亲道,“若水~仲儿被你教育的也是极懂规矩。”
若水笑了笑,“皇祖母过奖了,仲儿是皇嗣,自然是极聪明的。”
太后点了点头,拍了拍若水的手,没再说什么。
众人玩得起兴,正巧南伯沉、南伯文麟和大司奉赶来。三人原本正低声讨论着什么,刚进宫门便愣在了原地。
南伯文麟定睛看了看,才看出来是虞妁几人,皱了皱眉,道,“上熙?妁儿?你们这……”
正在打斗的几人问声一愣,接着立马站了起来,下意识的咽了口口水。
“狐若?”大司奉睁大了眼睛看着狐若,他这个傻儿子!
仲儿伸出小手抓着雪朝南伯沉走来,然后把雪全都洒在了南伯沉衣服上,众人都被吓了一跳,生怕惹南伯沉不快。
不料他不仅没气,反倒是将仲儿抱了起来,笑道,“为何洒我?”
仲儿伸出冻得通红的小手摸上南伯沉的脸,咿咿呀呀的说,“姑姑、叔叔砸姑姑。”
南伯沉朝虞妁看了过去,虞妁朝坑里伸出手,结果坑里也伸出一只手抓住了虞妁的手臂,着实吓了南伯沉一跳。
“逸、逸风?”南伯文麟此刻脸已经黑到极点,对一旁的北宫倾岚低声道,“你怎能任凭他们如此胡闹!”
“是臣妾失职,还望圣上恕罪,”北宫倾岚急忙行礼认错。
“父皇,这皇宫可是家?”虞妁问道。
南伯文麟犹豫了一下,道,“这是自然。”
“自然是家,为何不能玩雪?本就天家富贵的地方,孩子们竟然连最起码的童趣都没有,这种地方,又怎能称之为家?”
“那你想怎样!”南伯文麟咬牙问道。
“无拘无束,此乃天家富贵。”
南伯文麟看着她没再说话,南伯沉认真的上下打量着虞妁,开怀大笑道,“所言极是,没有人性的地方,又怎能称之为家?你们尽情玩便是!”得到了太皇特许,众人都高兴的跳了起来。
虞妁看着南伯沉没有说话,南伯沉问,“你可知我为何同意你的说法?”
虞妁笑道,“因为我是第一个敢把这皇宫当家的人!”
南伯沉认可的点点头,道,“说的好,不过先说好,玩归玩,这饭还是要吃的,除夕还是要热闹的!”
虞妁朝他笑着,道,“皇祖父所言极是,您请。”
南伯沉抱着仲儿笑着朝后殿走去,虞妁逸风几人在后边跟着,自然是暗自庆幸。
众人后殿落座,可是却迟迟没有等来佟妃和南伯云湘。
仲儿在南伯沉怀了已经说了好几次肚子饿,南伯沉也有些微怒,北宫倾岚见状赶忙圆场,笑道,“这仲儿是父皇的第一个重孙,父皇亲得很呢。”
南伯文麟也笑道,“那是自然,桓儿儿时也是与父皇最亲近。”
“桓儿是我第一个皇孙,他儿子是我第一个重孙,哈哈哈,这父子二人当长子还要继承?哈哈哈~”南伯沉的话惹得众人都笑了起来。
“不过话又说回来,其余的皇子们也该努力重视皇嗣一事才对。”太后正色道。
南伯逸风和南伯上熙对视一望,都憋着笑,反倒是南伯胤自嘲道,“皇嗣一事虽是重要,可也不是我等能做主的,连自己能活多久多不知道,又何必再搭上几条人命?”
南伯胤此言一出,惹得南伯文麟十分恼火,道,“若是你觉得活着为难,那朕便送你下地府!”
南伯胤也觉得自己有些失言,讪讪的没再说话。
“祖爷爷~仲儿肚肚饿~”仲儿小奶声一出,虞妁几人心都软了。
“仲儿乖,来娘亲这儿,别吵着祖爷爷。”若水冲仲儿笑道。
“我不,我要跟着祖爷爷~”仲儿拒绝了若水,然后死死的抱住了南伯沉,惹得南伯沉大喜。
“没来的是哪个?”南伯沉不悦的问。
“佟妃,还有她女儿。”太后面无表情的答。
“让她们二人来到以后殿外跪着!用膳吧。”南伯沉语气坚决的吩咐。
南伯文麟想要阻止,但是看到南伯沉黑着脸,也没再说什么。
用膳过后各自回了宫,等夜里在梅园看烟火。天气严寒,大司奉陪南伯文麟回了承乾殿,狐若无奈,只好厚着脸皮和虞妁挤在一个撵上,所幸狐若体态轻盈,但也不太拥挤。
晚膳梅园相聚,朝中重臣自然是一同参加,虞妁和他们打过招呼便找了个角落坐下,却又被逸风和狐若拉回了最前边~
晚宴热闹的很,歌舞升平,特别是最后一曲舞,女子一袭白衣从天而降,美得不可方物,一曲舞毕白衣女子朝南伯文麟款款走来,摘下面纱,竟然是南伯云湘!
南伯文麟有些吃惊,目不转睛的看着南伯云湘。
“祝父皇身体康泰,洪福齐天。”南伯云湘给南伯文麟敬上酒,然后一饮而尽。
虞妁给逸风使了个眼色,逸风端起酒杯笑道,“既然三姐带头,那不如所有皇子公主都敬父皇一杯,如何?”
“儿臣祝皇祖父和父皇万寿无疆,江山永固!”南伯桓说完将酒一饮而尽。
“儿臣祝皇祖父和父皇福如东海,寿与天齐。”南伯景笑道。
“儿臣敬皇祖父和父皇,福如东海,万世英明!”四皇子南伯胤和六皇子南伯亦举杯相敬。
狐若端起酒杯笑道,“那我就借花献佛,也敬圣上一杯!”说完便拈着杯子和虞妁一同来到南伯文麟面前。
刚要开口,却被拌了一脚,猝不及防的摔倒在地,酒杯摔得粉碎!
“司呈这是什么意思?这洒酒的敬法,可是对父皇不恭?”南伯云湘语气中的挑拨和陷害之心昭然若揭,只不过没有理由反驳她而已。
众人看着跪在地上的狐若,心都揪了起来,虞妁看了南伯云湘一眼,深吸一口气,抬手把酒杯狠狠的摔在地上,然后跪在狐若身旁,朝南伯文麟和南伯沉行了大礼,道,“祝圣上和太皇千秋万代,碎碎平安!”
逸风和上熙对视一眼,也上前一步,酒杯举过头上,猛的摔碎,行大礼道,“祝圣上和太皇名垂青史,碎碎平安!”
“好!”南伯沉忍不住拍手叫好,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笑道,“我南玄有尔等后生,实乃我南玄之福!普天之下,皆同兴!”
不过这小插曲并没有影响众人的心情,虞妁和狐若喝的酩酊大醉,到最后,竟称兄道弟起来,北宫倾岚抱着虞妁,怎么劝都劝不住,无奈之下,只能由上熙陪同回了秋斓宫,狐若也跟着逸风回了啸风殿。
除夕过了数日,热闹气氛过后,一切也归于平静,虞妁和逸风上熙借口出宫查看府宅的修盖情况,出了宫门狐若便像脱了僵的野马,怎么拉都拉不住,看哪儿都新鲜。
逸风和上熙去看了新宅子,虞妁和安青度芊寒芜一路行驶,绕城一圈后,在一家茶楼前停下。
虞妁抬头看了看茶楼的招牌,笑道,“一杯春露暂留客,两腋清风几欲仙~归一?有意思!”
“姑娘,您二位喝点什么?”店伙计热情的问。
“一壶上等的碧螺春!配绝好的砂瓷!”虞妁笑道。
店小二笑道,“一看您就是行家,您楼上雅间儿等着,茶水这就给您送来。”
虞妁点点头,上了楼,环视一圈,茶楼的装饰格局都雅得很,二楼雅间,每一间都相聚甚远,雅间内说话外人绝对听不到。
雅间内还可看到一楼的看台,台上一女子带着面纱正专心抚琴,琴声袅袅,引人入胜。处处弥漫着茶香,同样也是高朋满座。
虞妁和安青坐在雅间里说着新宅子的事,门外响起敲门声,刚才抚琴的白衣女子进门笑道,“两位姑娘的碧螺春。”
虞妁满目笑意的看着她,道,“真是一见如故,怎觉得姑娘如此眼熟?”
白衣女子笑笑,道,“姑娘真是好眼力,你我不仅见过,还同榻过夜,姑娘莫不是也忘了?”说完女子摘下面纱,竟然是夕迁。
度芊恍然大悟,笑道,“我说公主怎么不带你入宫,原来是让你在这儿做老板了?”
夕迁低头笑道,“我算哪门子的老板,戏时才是老板!”
安青环视一圈,问道,“说到戏时,怎么未曾见他的踪迹?”
“我们在城中买下了一家酒楼,我看着这边,戏时便去那边忙了。”
“你们二人也真真是发达了?”度芊调笑道。
“何谈什么发达,都是替公主做事罢了。”
四人正聊的起劲,楼下看台上却响起惊板声,往下看了看,说书先生一身蓝袍坐在台上,拱手道,“多谢诸位捧场,书接上文,咱们今日继续!”
“好!”
“来啊,接着说……”
“平日里都说些什么?”虞妁好奇的问。
“大多是些道听途说的故事,也没什么太实在的东西。”
虞妁思虑了片刻,道,“待我回了宫,将故事写给你,你交于说书先生,便让先生按着我写的说,如何?”
“那自然是极好的!”夕迁兴奋的说。
“掌柜的,戏老板回来了。”
夕迁朝虞妁笑笑,道,“戏时回来了!”又对门外的伙计道,“让戏老板上来,就说有贵客来到。”
不多时戏时便来了楼上,伙计打开门,道,“戏老板里边请。”
戏时惶恐的拱手,“多谢多谢。”
待戏时进了门,度芊便打趣,“戏老板,别来无恙啊?”
戏时一看是她们,立刻跪在虞妁面前,激动的说,“主子您可来了!奴才以为您不要我了!”
虞妁苦笑的看着他,笑道,“我怎会不要你,你与夕迁在宫外我也是日日挂念。”
几人许久不见,自然是有许多话要说,直到夕阳西下虞妁才离开,临行之前夕迁将一摞账簿递给安青,笑道,“这是这几个月来的账簿,请您过目,”
虞妁笑着摇了摇头,“我信得过你!”
夕迁真诚的看着虞妁,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虞妁心照不宣的一笑,转身进了马车,马车朝宫门驶去,安青叹了口气道,“夕迁办事,咱们倒也安心的多。”
虞妁闭着眼睛,轻声道,“若是让我提心吊胆的人,我自然也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