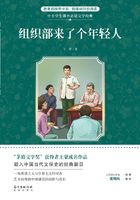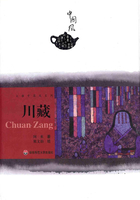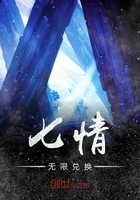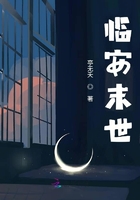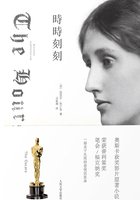朱自清的文字中提及刘延陵先生的有多处,即见他俩交谊深厚,如《我所见的叶圣陶》的开首:“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民国十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到了那边,他就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接着写他们三人过了一段“实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朱后来说到办《诗》月刊事云,我们“几个人里最热心的是延陵,他费的心思和工夫最多”。又比如,1924年到1925年的那一本日记中(1924年11月30日项)云:“到甬,晤延陵,甚快!”说的是朱自清从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回到宁波省立四中上课,碰到刘延陵,感到甚为快乐。其时,他俩都在宁波教书,只是刘未去春晖兼课,朱则碌碌于两校。此事刘也在《湖畔忆旧》中说及:“朱兄离开杭州以后,与我在宁波的浙江省立四中同事二年。”
刘延陵先生虽未到过春晖中学,然他依然是白马湖文派中人。从《诗》月刊创办到“浙一师”的“后四金刚”,乃至在宁波省立四中的同事以及其在《我们》的编务中的出力与劳绩,皆足以说明刘是该派中的一员。他们的“同志集合”,显然不是党派或有形的社团,内部也没有富于宗派或团体意识的文件,纯粹是志同道合相凝聚。他们之间过往密切,友情笃实,通信读来令人如沐春风。他们或定期举行例会,茶聚酒会;或相约碰头,三五夜话。叙别相迎送,华诞相庆贺。他们之间有和谐的切磋,激烈的争论,既相濡以沫,又相忘江湖,却很少有钩心斗角或落井下石之举。白马湖文派“同志的集合”,其主要价值似乎展示了这特定时代、特定群体的特定人群——新文化运动中一群可敬可爱的文化人。刘在《我们的六月》里,发表了他的散文《巡回陈列馆》。俞平伯的《城站》云:“读延陵君的《巡回陈列馆》以后,那三等车厢中的滋味,垂垂的压到我睫下了。在江南,且在江南的夜中,那不知厌倦的火车驮着一大群跌跌撞撞的三等客人归向何处呢?难怪延陵说:‘夜天是有限的啊!’我们不得不萦萦于我们的归宿。”两文同样笔涉夜归,刘文一味写江南夜中三等车厢里之滋味,俞文则离情客愁都写,微苦与微甜杂糅。白马湖派散文家似乎多关注过火车之三等车厢,他们执教于春晖中学,又在宁波省立四中兼课,一周之中,三天在白马湖畔沐浴“山间明月”,三天又在奉化江边任凭“江上清风”吹拂,碌碌然欣欣然做着“火车教员”。难怪乎丰子恺有兴创作漫画《三等车窗内》揭载在《我们的六月》,它以焦墨作成的黑白画面,生动地画出两女子自玻璃门窥视头等车厢之状。朱自清在其创作的诗里也提及三等车,《依恋》云:“坐到三等车,/模糊念着上海的一月,/我的心便沉沉了。”
刘延陵的《〈蕙的风〉序》,与胡适与朱自清的是同题散文。三篇比照之,窃以为,刘文最有新意。胡文徘徊于题材、形式尝试的自由的论题,提出诗的评判标准三等说:“浅入而浅出者为下,深入而深出者胜之,深入而浅出者为上。”倒也有意义。其意义在于文章的表述要飞跃式的“含蓄”,如胡适之云:“古人说的‘含蓄,并不是不求人解的不露,乃是能透过一层,反觉得直说直叙不能达出诗人的本意,故不能不脱略枝节,超过细目,抓住了一个要害之点,另求一个深入而浅出’的方法。”所谓“脱略枝节,超过细目”,是说用笔时要能“飞跃”,“不能一步跟一步走”,即一切与主旨关系较远的枝蔓都要删节,反之势必冲淡主题,使得线条不清晰,主旨不突显。这样一种飞跃式的含蓄,是需要慢慢体味的。当然此谓题外之言。朱文直陈文学之为人生的信奉,颇感两难。刘文则批评太人生的倾向,针对“文学为人生”中过度强调其诅咒批评功能,申说广义的“为人生”。他说:“因为我们是为的善良的生活而生,义务与享乐皆所以‘善’我们之生。若说我们只当工作,不应享乐,这是一种宗教式的stoical的人生观,实在不敢闻命!”毅然坦然地为自然、爱情乃至享乐正名,直言人生尚需要充满诗意,可谓独抒己见。而且刘延陵是贴上门去作序的,他的未受邀约而自告奋身,表明他急切地想表白他的精辟的观点:“能启迪人的美感,宣达人的感情,而非诅咒批评的文学,既也能助成人的善美的生活,所以也就与人生有关系了。”此即是广义的“为人生”观。
作为白马湖作家,他与朱自清的序文在审美情趣上是趋同的。即皆已感到汪静之自然题材的诗,不是描写自然,而是以礼赞的态度赞叹大自然的美。故都用了“赞颂自然,咏歌恋爱”和“以赞美自然歌咏爱情的居多”来概述《蕙的风》的题材。然亦有相异之处,朱更多关切的是为人生,多写血泪的文学;刘则为人生又为艺术,认为不该因为“太人生”与“太不人生”之两端而抹杀生活与艺术的趣致。他又进一步说,关于文学之“为人生”与“为艺术”的价值虽然受时代的影响,不过相对的轻重却没有固定的标准。
刘延陵编过《明清散文选》,对古典散文颇有体悟。他的《散文的起句》,仅就“起句”便发表了十分精到的意见:“散文的起头似乎更需要精警。”文之例证古今杂陈,论述要言不烦,以“简明清畅”为原则,枝蔓之辞是一点没有的。《诗的用词》的开篇,曲径通幽,引人入胜。在未入题前,先讲诗与文之用词的区别,讲此则不可不讲诗与文的区别。随后又引出理智的文字与情感的文字。而理智的用怎样的词、情感的用怎样的词,最后入题。而本题之论述,是谓最早运用修辞格来表述,时在1921年。比之陈望道在1923年讲修辞学还要早,比之新加坡学者郑子瑜研习修辞学则要更早。刘延陵的《诗的用词》是篇演讲词,先在浙一师作过演讲,由范尧深记录,刊行于1921年1月10日的《浙江第一师范十月刊》第七号上。后又在宁波省立四中演讲过。陈望道也在四中作过《修辞学在中国之使命》的演讲,由方光焘记录,该文发表在1924年7月28日《文学周刊》第132期上。
刘延陵在宁波四中时,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的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白马湖作家纷纷登台作讲,刘讲《小诗的流行》(其时周作人在北京作《论小诗》与《日本的小诗》的演讲),他说:“短诗必须文简而意精,否则也必须有特殊的风格。像泰戈尔《飞鸟集》里所作的诗,大部分可算好,但有二三十首我还是觉得是一种理智的格言。”是时,正赶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小诗运动”的勃起,它受着外来文学(主要是日本短歌俳句和印度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刺激与影响。日本小诗自不消说,即以《飞鸟集》中三言两语的短制,它那睿智的无处不在的哲理,最能消解五四文青在探索人生途中的苦闷与寂寞,它那温婉、凄美的情调,最能引起落潮期的小资的心灵共鸣,它那比日本俳句自由活泼得多的形式,亦最易把握和移植。“小诗运动”时间虽然不长,但刘延陵把泰戈尔的小诗介绍进中国诗坛,开阔了人们的艺术视野,活跃了人们的艺术思维,白马湖之群此举与北方的语丝之群互为呼应,为小诗的兴起推波助澜,倒也兴奋了当时的诗坛。
传统的文会以文人雅集或诗文荟集为基本运行方式,现代文学流派则以现代传播媒体为基本运作载体。白马湖派显然是以出版物为中心,以出版物为价值载体运作的。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诗》月刊,而该刊正是刘延陵主其事。他在《诗》里发表诗文近二十篇,又为湖畔诗人刊发诗歌三十四首。从我国第一本“诗刊”《诗》到第一本同人刊《我们》,刘延陵都参与其中,可见他是白马湖派中人。刘延陵晚年为《〈诗〉月刊影印本》所写的序,回忆了这段历史——《诗》月刊筹备与出版的经过(虽然未涉及在宁波四中的乐群亭与朱自清商榷《我们》的编辑事宜,此乃主题所制约)。文中提到编入《诗》第一卷第4号(1922年4月5日出版)的叶圣陶《诗的泉源》,他记得十分真切,诗是生活的反映,没有生活也就没有诗。这是简明的道理,一种不容忽略的常理。进而加以发挥:“一个人必须与生活接触的方面很广,从生活上感受到的也很深,然后他所经历的非常的事故和日常的事情才都可以成为他写诗的资料。”刘的回顾,表明生活是诗的泉源是我国新诗的优良传统。重温《诗的泉源》,在当今似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是否可以这样说,它与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说的“生活是文艺的源泉”一节,以及习近平2014年10月15日提出的“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从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科学论断,皆是对五四以来新文艺理论的概括与总结。《诗的泉源》说,生活有两种:“空虚”的生活和“充实”的生活。“空虚的生活是个干涸的泉源,也可说不成泉源,那里会流出诗的泉来?”“唯有充实的生活是汩汩无尽的泉源。有了源,就有泉水了,所以充实的生活就是诗。”至于“生活空虚的人也可以写诗,但只是诗的形罢了……所以到我们眼睛里的诗有满篇感慨,实际却浑无属寄的,有连呼爱美,实际却未尝直觉的;情感呢,没有,思虑呢,没有,仅仅具有诗的形而已。汲无源的泉水,未免徒劳;效西子的含颦,益显丑陋”。这席话,洵可谓一部“诗美学”的缩影,对近来那些脱离人民、疏远生活,以歌唱“自我”为中心并自诩为著名的诗人以高视阔步者,不正有一点警示作用吗?须知,“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诗源于生活,文艺源于生活,唯有立足于时代与生活之真的,才能昭示心灵的善,开启艺术的美。故诗、文艺离不开人生,离不开社会,更离不开人民。
应该提及的是,白马湖同道对于诗的源泉是生活的作诗理念颇为一致。《诗》里刊载血与泪写照的诗篇(如徐玉诺之作)便是佐证。刘延陵晚年还清晰地记着此事。朱自清其时直呼,我们现在需要最切的,自然是血与泪的文学,是呼吁与诅咒的文学。叶圣陶认为,一个耕田的农妇或是一个悲苦的矿工的生活比一个绅士先生的或者充实得多,因而诗的泉源也比较的丰富。俞平伯则说,在《诗》第四号上登着叶圣陶《诗的泉源》一文。这篇短文的论点和风格,就叶圣陶来说,也可以说是有代表性的……他积年的梦想,目前早已成为现实了。
刘延陵晚年的散文写得很散淡。无论叙事、议论、抒情、状物,皆以闲谈方式向你吐露内心感受,袒示真挚意绪,不事掩饰。《忆诗人易君左》《湖畔忆旧》诸篇,意主浅显,不涉玄虚,行文也不为格套所拘,不为章法所役,可谓信笔写来,娓娓而谈,又是顺理成章。他长年侨寓海外,熟谙英文写作,晚年操起汉文仍畅达自如,所作随笔书评如《谈新诗》《我对中国新诗的杂感》等,旁征博引,挥洒自如,毫不枯涩,极有学术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又如关于诗的“明朗与朦胧”观点,作者不厌其烦地用娓语式笔调,通过好几篇文章来表述,言简而意明,这大抵为清逸散淡人生所致。因为能够散淡,才能不失自我,保持本真,写作能够直抒胸臆,绝无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之态,这就自然能够写出别人爱看的好文章来。一言以蔽之:白马湖派散文家本色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