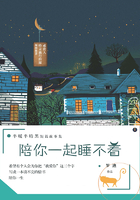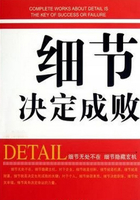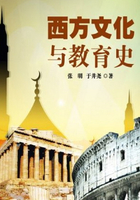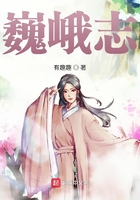郑振铎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和实际领导者,这已为人所公认。但他也系白马湖派散文家,似鲜为人知。郑的散文“像《海燕》《山中杂记》的文字,清新细腻,写景与抒情都有独到的成功”。作品集中创作于1925年至1928年间,恰巧这几年也正是他与其他白马湖派散文家频繁交谊的时段。不是吗,朱自清在白马湖时出版的第一本诗文集《踪迹》,郑振铎评价道:“朱自清的《踪迹》是远远的超过《尝试集》里的任何最好的一首。功力的深厚,已绝不是‘尝试’之作,而是用了全力来写着的。”在白马湖时期,朱自清十分留恋白马湖文派的聚集,说:“约两个密友,吸着烟卷儿,尝着时新果子,促膝谈心,随兴趣之所至,时而上天,时而入地,时而论书,时而评画……时而剖析玄理,密诉衷曲。”郑振铎当是其中之一。难怪乎,对于丰子恺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他不无感慨地道:“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芦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我的情思被他带到了一个诗的境界。”
郑振铎的《山中杂记》于1927年由开明书店印行。该书摄录了郑氏在莫干山避暑的见闻。“这些散文依旧保留着‘真率’和‘质朴’的艺术特点,随着他写作技巧的渐趋成熟,文笔更为秀丽,写得细腻委婉,清新动人”,很有“白马湖的韵味”。书中《蝉与纺织娘》即有这样的味道。对于“味”,唐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特别强调,诗要“辨于味”,把“味”放在诗的首位。不辨味,则不足以言诗。这种味,既不是酸味,也不是咸味,而是味在酸咸之外的味之旨,韵之致。郑之此作,即兼具浙东土味的自然质性与白马湖风韵的清淡隽永。他流连于山中,倾听蝉与纺织娘之鸣声,书写自我的见闻,寄托深刻的寓意,使文章之“味”之穷。兹录存一段堪殊玩味:
虫之乐队,因季候的关系,而颇有不同:夏天与秋令的虫声,便是截然的两样。蝉之声是高旷的,享乐的,带着自己满足之意的;它高高的栖在梧桐树或竹枝上,迎风而唱,那是生之歌,生之盛年之歌,那是结婚曲,那是中世纪武士美人的大宴时的行吟诗人之歌。无论听了那叽——叽——的曼长声,或叽咯——叽咯——的较短声,都可以同样受到一种轻快的美感。秋虫的鸣声最复杂;但无论纺织娘的咭嘎,蟋蟀的唧唧,金铃子之叮令,还有无数无数不可名状的秋虫之鸣声,其音调之凄抑却都是一样的;它们唱的是秋之歌,是暮年之歌,是薤露之曲。它们的歌声,是如秋风之扫落叶,怨妇之奏琵琶,孤峭而幽奇,清远而凄迷,低徊而愁肠百结。
作者如是赞誉蝉之鸣声,如是憎恶秋虫之声,形象对比鲜明之至。读之不难看出,作者的寓意是对光明的讴歌和追求,对黑暗的不满和厌恶。然这并没有着意经营的痕迹,而是作者情致的自然流露,只是把心之所感,“坦白无饰地表现出来”,践行了他在《雪朝》短序中所说的,我们要求“真率”,有什么话便说什么,不隐匿,也不虚冒。我们要求“质朴”,只是把我们心里所感到的坦白无饰地表现出来,雕琢与粉饰不过是虚伪的遁逃所与“真率”的残害者。
郑振铎襟怀坦白,与虚伪世故无缘,他写散文不隐匿、不虚冒。他的《猫》与夏丏尊的《猫》,写的都是平平淡淡的家常事,皆赋予人的感情。丏文可谓是一曲深情的挽歌,写的是猫,实为借猫写人,写人的感情。郑文低声细语、闲话家庭琐事,表露心灵深处的感受:猫之可爱的死去,有能者遭劫,不幸者被冤,正是那不公正的社会的写照。这些文字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们把深挚的情愫,包容在平常的生活场景中。以清疏平淡的文字出之,有几分动情就陈述几分,既不回避,也不强为渲染,故作多情,甚或滥情。
郑振铎写过一篇《悼夏丏尊先生》的纪念文字,对夏丏尊的为人为文知之甚深。他说:“‘文如其人’,我们读他的文章,确有此感。我很喜欢他的散文,每每劝他编成集子。《平屋杂文》一本,便是他的第一个散文集子。他毫不做作,只是淡淡地写来,但是骨子里很丰腴。虽然是很短的一篇文章,不署名的,读了后,也猜得出是他写的。在那里,言之有物,是那么深切地混合着他自己的思想和态度。他的风格是朴素的,正和他为人的朴素一样。他并不堆砌,只是平平地说着他自己所要说的话。然而,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不诚实的话,字斟句酌,决不急就。在文章上讲,是‘盛水不漏’、无懈可击的。”这是知人之论。知人之深,才会有论文之深。同样对周作人,他的《惜周作人》,立论最为公允。特别是周的附逆的原因,他的分析最令人信服。这是因为其“真率”:“他实在太可惜了!我们对他的附逆,觉得格外痛心,比见了任何人的堕落还要痛心!”这较之梁实秋的隐约其词(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原名苦雨斋,后改为苦茶庵,不离苦的味道……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么掉进了泥淖一辈子洗不清!)来得痛快。真率是散文创作的生命线,它所要求的高度的真实性,主要是指必须具有真情实感,必须具备内心和感情的真挚与诚挚。如是出于真挚和坦率的流露,才有可能打动读者的心。
郑振铎的散文,唯《山中杂记》诸篇具有山野风趣,诚如王哲甫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里所作的印象式评述:“那明媚的山色,葱郁的树林,以及纯朴的居民生活,及他自己的山居生活,都写得十分美丽有趣。”也最具“白马湖的清淡韵味”。这是因为白马湖文学中既有水的柔情,又有山的风骨和海的胸襟。郑振铎的“五卅”诗文,即是“山的风骨”。1925年的五卅运动正发生在白马湖时期,白马湖派散文家皆拿起笔杆当钢枪,奋起斗争。朱自清的《血歌——为五卅惨剧作》,刊在《我们的六月》的扉页,特别吸引人眼球。他指导宁波四中学生刘沧海写的《洒泪吟——并慰沪上惨死的同胞》,揭载在《四中之半月》上,在浙东很有影响。朱自清的《给死者》、叶圣陶的《五月卅一日急雨中》、郑振铎的《街血洗去后》发表在同一期(第179期)的《文学周报》上,更是反响巨大。郑的这篇散文质朴地叙述了血洗后的南京路的实况。作者在这种质朴的描写中,透露出满腔的愤懑与沉痛,践行了他的“只是把我们心里所感到的坦白无饰地表现出来”的创作理念。就在“五卅”发生的当天下午,郑乘车到南京路浙江路口。他走到现场观察,看到大摊大摊的血被冲洗去了,英国巡捕乘着高头大马,闯到人行道上,用皮鞭殴打行人,给他以“至死不忘的印象”。他的热血沸腾了,写了好几篇诗文,控诉帝国主义的罪行,呼唤着:“为中国,我们携手向前!为中国,我们呈献了一切!”这些直抒胸臆、激越高亢的诗文,计有散文《迂缓与麻木》《六月一日》,以及诗歌《墙角的创痕》。其中《六月一日》那篇,散文评论家林非在其《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中云:“这篇散文的感情实在激越和深沉,文笔质朴而又流畅,节奏铿锵,富于变化,很有艺术感染的力量,是当时出现的一篇优秀的散文。”
郑还在其主办的《文学周报》上出了“五卅”特刊(第180期),在他编辑的《小说月报》上出了“五卅”特辑。又与沈雁冰、叶圣陶、胡愈之合办了《公理日报》。他觉得上海各报“对如此残酷的,足以使全人类震惊的大残杀竟不肯说一句应该说的话”,便自己动手编辑了一份爱国报纸出版。发行地址在自己的家里,并且亲自参加了发行。
白马湖派散文家传承着清淡与激越的两个传统,时而清淡,时而激越,流贯于“剑”“箫”之间。他们固然对“山水间的生活”很感兴趣,时有清淡之文传布,但因多为人生派作家(郑振铎即是),更关切的是现实,一旦现实生活发生剧变,便即刻表达义愤与抗争,文风显得激越与峻急。郑振铎的“五卅”诗文诚是如此。它与《山中杂记》刚柔相济,彰显着“白马湖文学”的精神。
郑振铎虽未到过白马湖,但对于白马湖畔友朋云集,心向往之。尤对丰子恺作于白马湖的漫画,“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其“情思被他带到一个诗的境界”。郑后来又说,“当我坐火车回家时,手里夹着一大捆子恺的漫画,心里觉着一种新鲜的,如同占领了一块新高地般的愉悦”。郑振铎到过宁波,1922年暑假,与沈雁冰应四明暑期讲习班之请前来讲学。他俩在县学街孔庙明伦堂分别作《儿童文学的教授法》(其时郑正在编辑《儿童世界》周刊)和《文学上各种新派兴起的原因》的演讲。郑、沈二人给宁波新文学的火种增添了一把柴火,使新文学之烈火熊熊燃烧在浙东大地。由于这次演讲,王任叔便由郑振铎介绍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因而也就有了文研会宁波分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