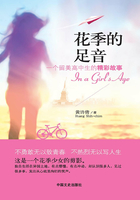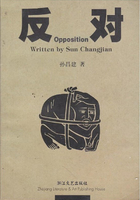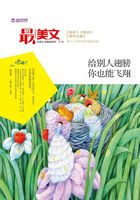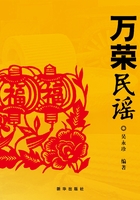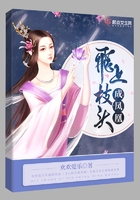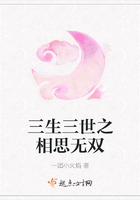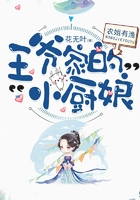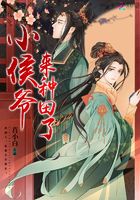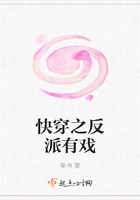里三份有20多户人家,住在一个大道地中,有长辈、平辈,也有晚辈。邻里们十分相爱,像隔壁的弟媳陈国芬,夫妻俩相敬如宾,尊老爱幼,是一个和谐相伴的家庭;又如堂前的陈台良,儿孙满堂,阖家欢乐,从不争吵。梁丽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在这个大家庭的熏陶下,她坚持“邻里和睦相处”,一直以来,她对人从未红过一次面,争过半句言。大家一提起梁丽丽,都会竖起大拇指。
好村民
“家齐村治”。一个村庄,不论大小,同样有“村规民约”。一直以来,梁丽丽遵纪守法,做到爱村如爱家,成了村民的表率。
一次,梁丽丽在溪坑里清除垃圾,村上一位82岁的陈昌法老伯看见她,就弓着背,走到她身边,脸上像吃了蜜糖一样笑着,说:“丽丽,你真好!大家都像你一样,什么事情都能做好!”梁丽丽一本正经地回答:“这点小事情,算得了什么?不过,一个村好像一个家,环境卫生靠大家!”
梁丽丽的故事,是古村龙宫“义行天下”精神的写照,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写照。
搜集整理:陈志清
2015年2月
邻居好,好靠老;田邻好,好种稻
龙宫冷水洞有两畈田,一畈有水,叫烂湾;一畈没有水源,叫燥畈。陈锡语家居燥畈,种燥作;陈锡诗家拥烂湾,种水稻。两家人上一辈由于相邻,上落多,七上八落就落下不少“肚作病”,所以一直以来,人相近田相邻,心隔远不相往。到了陈锡语、陈锡诗这一代,两家人都想要改变这样的状况,于是通过几件小事来打破僵局,后来分水续田,最后成了出了名的好邻居、好田邻。
身是同根生,相邻处处有。“低头不见抬头见,相逢无语各避让”的局面总得有人先打破。陈锡语想:我为兄长应为先。于是在一次收工回家时,他就试着打了声招呼:“锡诗,你今天做什么活啊?”“我到烂田湾斫田岸。”这一招呼马上得到了回应,打破了僵局,从此,两家上山下地经常同出归,关系渐渐好转。这年农忙季节,陈锡语家人多,体强力壮的,倒也不觉忙;陈锡诗家人少体弱,起早落夜也忙不过来。有一天,陈锡诗把秧打到田里,突感身体不适,第二天还是下不了田,第三天硬撑着想把打着的秧种掉,可到田畈一看,满畈青苗全都种好了。这时他特别感动:一定是陈锡语家帮的忙!于是回家收些铜钿准备付点工钱,可是陈锡语家说什么也不肯收,并说:“就算外人,如果碰到这种烂秧误季节的事也应帮忙,何况我们是邻舍隔壁呢。这是应该的。”从这次进门之后,两家就有了往来,有了往来后,帮忙就成了正常事。这使得陈锡诗经常牵肠挂肚,不知如何报答才好。
这年盛夏,久旱无雨,陈锡诗独自一人坐在水洞边乘凉。他看着绿油油的一片秧田禾苗茁壮,听着淙淙流泉低声吟唱,想着黄灿灿的稻谷,又是一个丰收年!可是,当望着田邻旱地作物叶子倒披、干涸枯黄时,就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心想:燥畈也能种上水稻,那该有多好啊,既省力又高产。于是,陈锡诗决定分水,当晚就把这个决定告诉了锡语,叫他们把旱地改成水田。锡语全家听了,不知有多高兴,于是齐心协力,一冬改出了大田三丘,足有一亩。第二年,陈锡诗亲手翻开大界放水过来。陈锡语家种上水稻,当年收稻谷一千多斤。这下,陈锡语家高兴得不知该如何感谢锡诗家了,于是抬去一箩筐谷,放到锡诗家中。可是陈锡诗不高兴了,把谷抬回来,跟他们说:“你们帮我好几年,从来不要谢,我要收谷就是无情无义之人。上辈过失,我们下一代来弥补。记住古人言:‘邻舍好,好靠老;田邻好,好种稻。’让我们做好邻居吧,相互帮助,不要言谢。”此后,两户人家又合力挖掘水源,把整片燥畈改成了水田。有了这样一畈田,陈锡语家很快就成了富裕户。为不忘分水情,牢记好邻舍,他们把这畈田改名为“诗邻畈”,最高一丘取名为“分水丘”。
后来,陈锡诗由于身体不好,长期患病,儿子做生意又蚀了本,欠了好多债,心想,隔壁老大陈锡语一直事无巨细地照顾他家,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去麻烦了,于是瞒着老大将烂湾田押了出去。锡语得知后,心想,我家富裕全来自于他家分水,有情有义之人受人滴水之恩,应以涌泉相报。所以,他不声张,默默地将田赎了回来,并一如既往地照顾着,直到锡诗家重新兴旺。
经历此事后,两家人好得如一家,相互间上可寄老,下可托小,心相通,事相商,同富贵,共荣辱,他们这“邻居好,好靠老;田邻好,好种稻”的事例成了教育下一代的典范。
搜集整理:陈宝相
2015年2月
“小脚婆”逛街
“小脚婆”名叫朱仙凤,小时候裹得一双特别小的小脚,后来由于年龄高,辈分大,就以“小脚婆”代名。年轻时,她去过上海,见过高楼大厦,游过十里洋场,算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乡下女人,后来回到乡下,总也难解城市情结。但由于自己没有生育,弟媳早逝,留下了一群孩子,于是她义不容辞地负起了照看孩子的责任,侄子大了带侄孙,就这样,她一直没有离开过龙宫。改革开放后,时常听人讲城市发展有多快,宁海的马路有多宽,楼房有多高,公园有多漂亮,但是她总是不太相信,还是讲着她的老见闻——上海……上海……后来,她的一个侄子陈成志到宁海发展,侄孙陈庆华也到宁海学艺,这时,她曾有过心动,想到宁海去看看。可是仔细一想,他们住的还是出租房,条件都不好,于是就又收心了。再后来,侄子开起了宾馆,侄孙也开了店,她非常高兴,以往请也请不去的她,偶尔露出了想去宁海看看的意思。这种意思很快就被经常来照看她的陈庆华发现了,于是跟小阿叔一商量,马上就把她接到了宁海。这一去,就引发出一个“‘小脚婆’荡街”的故事来。
第二天,一色孙子辈的六七个人陪着阿娘(奶奶)去荡街。这年朱仙凤九十五岁,身体康健,耳不聋,眼不花,所以出门时一定坚持要走走看看。孙子们顺着她,簇拥着她上了马路。不多时,他们发觉马路两边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们这里,时不时传出啧啧的称羡声:“这个太婆多健啊,介大的年纪还会荡街,侬相多有福气啊,一群孙儿女围着她说说笑笑、蹦蹦跳跳。”由于小孩子一跟跟了一大班,年轻人开车到旁边放慢了车速,电动车骑到旁边干脆推着一起荡起了街。于是,交通就发生了拥堵。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是太婆的形象装束太不一般了。她久居乡下,勤俭节约,一切守旧,于是成了时代的“老古董”。看她,灰白头发挽在一起形成一个结,结上插着一根红得发亮的毛竹簪,又套着一圈陈旧的黑色包头;一张历经几个朝代的老脸干瘪生斑,沟沟坎坎,爬满了深深浅浅的无数皱纹;身穿大襟布袄,右边腋下的布纽扣像几只无翅的蜻蜓排列着,腰系一条卷起一半的青布拦腰,着一条大脚裤,脚踝处绑着蚂蟥绳,特别是一双“三寸金莲”,像直锤豆鉒一般,人们不觉奇怪,这是怎么站牢的,而且百岁老人走起路来还这么稳当。这些,不管在乡村还是城市,都是很难看得到的,所以引起了人们的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