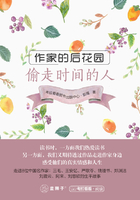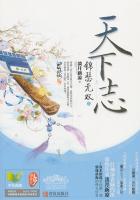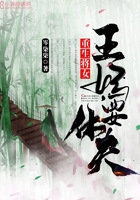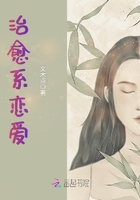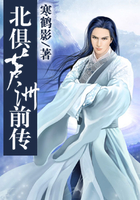在万州闲逛,你成了局外人。你的局在水下,或已被江水冲走。你的局早已经散了,也未可知。在万州闲逛,孤零零寻找着墟中人、水中人。我已走进废墟,或还在过去的时日?
到处都是陌生人,尽管这里很熟悉。我熟悉的人一半已经离世,一半正逐渐远去。在万州闲逛一上午,终于在偏石板背后,黑压压打牌的人群中遇见一位布衣老汉,身背白布口袋;他也在人群里闲逛,在看别人打牌。我上前问候,并问师傅从哪儿来。老人家说:“密溪沟。”
密溪沟,我居然没听说过,而且就在附近,也属于淹没区。我问那里的情况,老人说不清。我请老人家留下姓名、地址:谭明武,万州江南新区旅密4组1号;然后我问:“我跟你一起回去要得不?”
“要得么。”谭师傅说,并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我说:“走么,没有不去的道理。”
就这样,我跟着刚认识的谭师傅来到码头。谭师傅心里还有些忐忑,他要去我的身份证看了又看,然后又说:“你要骗我,有点难。不过,人头上也没有写好人坏人。我是退休工人,你不信,我邀请你到我家去。我可以给你找人,懂得多的、八九十岁的老人还有……”
无论如何,我渐渐赢得了他的信任。一路上,谭师傅又告诉我:“我十八岁就离开家,在各地修铁路,参加过成昆线,还有川黔、滇黔、京九铁路的工程建设;全国走的地方也不多,就11个省市。那时候,国家也没有正式手续,修铁路也是跑江湖,现在退了休。这一次来万州,是看一个亲戚,他的脚杆给汽车撞断了。”说话间,我们已来到万州码头。
下午四点,“万州轮渡1号”驶离万州,船上也没几个乘客。船长何兴国沿途指给我看:“高桅子——上溪角——桃子园……本来是很好的地方,全都淹没了……”而船只经过,隐约还能感觉到桅杆在山涧漂移,桃子园中的桃子已结成石头。
前面山坡上出现一座宝塔,“这是洄澜塔。”船长何兴国说,“原先的洄澜塔在前面那个座桥墩下50米左右,那里淹没了。宝塔拆除之后,所有原材料都堆放在上面一百多米的一所学校里,后来搬到上面重建。现在看见的这座宝塔,完全用的是原先的砖石和原材料,只是宝塔的铁尖尖在存放期间被一个中学生偷去卖了,后来被派出所捉到,但那个铁尖尖已经被斩了卖了,现在的塔尖是后来照原样重做的。这一点除了我们,没哪个知道。”
“长江这一段原先都是风调雨顺的,只有中滩子那一段总打劈船。”船长接着说,“你看那道红石梁,叫红蛇下山吃克玛[76],后来涨水,克玛跳到了水里游走了,红蛇还在。”
果然,我看见一道蛇形的红石梁仍在水中扭动,而克玛(石)已不知去向。
说话间,密溪沟到了。密溪沟又叫密溪峡,峡口像一道弯曲的石门,半开半阖。顺着一条小河进去,过一道小石桥,里面就是密溪沟。下船转弯,跟着谭明武师傅穿过寨子一队,进入旅密村,一路上不时停下来,弯腰拾捡埋在泥土中的石宝。这里的石宝小巧玲珑,五彩斑斓。
绕过一道溪谷,走进田野。青苗之间,我发现了一座小土地庙:几块石板搭建的小小庙堂,里面刚好放下一只白瓷碗,一束红香和一尊小土地菩萨。我给他照相的时候,小土地菩萨脸上就露出微笑,活灵活现。谭师傅告诉我:“这座小土地庙是一个名叫穆惟全的年轻人自己建造的;土地菩萨也要移民。现在是枯水季节;等水位涨到175米,这里,连身后这座桥、这片田地、这个小土地庙都要淹没。在密溪沟,签了(移民)协议的,都搬走了;留在这儿的,都还没签协议。”
在不远的溪水边,一位戴草帽的渔翁正独自垂钓。而就在谭师傅跟他寒暄之际,一只大蝴蝶翩翩飞来,是黑色的花蝴蝶,翅膀上像是睁着两只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我们;顺着蝴蝶飞来的方向,只见一个被江水淹没的岩洞,只剩下小半个月牙形的洞顶,其余都浸在了水中。我问那是什么地方。谭师傅说:“原先是个天然岩洞,有十米多高,从前有个彭大老爷就在洞子里居住。”而彭大老爷何许人也,谭师傅也说不清。
我正沿路打听,谭明武师傅已将我领到何贤功老人家里。
何老师1929年出生,身体还好,可惜记忆有些模糊了。问及往事,只回忆起“祖上都是种庄稼,十二岁出门,去万州拜师学艺,学做毛笔。解放后就在国家开的多业社做毛笔,后来在本地的翠屏文具厂工作到退休。别的想不起了……”而这时,来了几个老邻居,大家一同回忆起“彭大老爷”。据说这个“彭大老爷”曾是同盟会成员,从前与孙中山一起革命,后来被通缉,从广西逃到万州,躲进密溪沟隐居并隐姓埋名,人们只知道他叫彭大老爷,没有人能说出他的真实姓名。
“彭大老爷当年就看好这个岩洞,冬暖夏凉,洞子里好宽好高,可以摆几十席。彭大老爷在洞里建了三层楼,还利用流水发电。一条瀑布悬在洞口;外墙门窗都镶的玻璃。现在全淹没了……”老人们回忆道,“百年之后,彭大老爷还是葬在这里,他的后人后来都离开了。”
“解放后,彭大老爷已经不在了,他的财产都充了公。那个洞子被一些娃儿打开,我们也跟到进去耍的,里面好多书哦,还有老字画,其中有一幅画的老虎,上面还写的‘唐寅’两个字,我们小时候看见过的,全烂完了,书都撕了,扔得满地都是,地上还有好多碎玻璃……”一位在一旁劈柴的老汉回忆道。
“密溪沟当年的马路都是彭大老爷修的,”老人们又说,“他还出资办学,开设渡船,从密溪沟,到对门的红砂碛,穷人都不要钱;还开设渡口,把山里的桐油装船运出去……”
“解放前,密溪沟开的有饭馆、烟馆、茶馆……照老话说:‘好个梁义绅,掌旗张虚之。钱粮是胖子,管事惹不得。’说的都是当年那些能干人……”
“彭大老爷专门为穷人主持公道。”一位名叫黄开清的老邻居又说,“抗战时期,国民党的部队组织搬运汽油,一些军用物资就藏在密溪沟里……你也抬,我也抬,抬到天黑还不让人歇。彭大老爷就过去跟他说:‘你们不让他走,那就要找地方让人歇夜哦——凡是下力的人,两个人一床铺盖。否则我就告你。’后来那些部队官兵只好让民工回去休息了。”
说起彭大老爷,老人们不胜唏嘘。忽想起洞口飞来的大蝴蝶,黑翅膀上睁着眼睛——蝴蝶蝴蝶,您是哪位老人家?古往今来,山水间飘荡着多少逝者的英灵!
而这里是旅密村5队、6队,见到这些老人家好不容易,何况大家又聚在一起。我只有用心询问,仔细倾听,试图将密溪沟的涓涓细流汇集成河。
据黄开清老人回忆:“解放前不兴说公社,是说乡政府。大地主魏少柏每年要收好几百石租子;他们家原先就住在高头,旅密4队,现在没有人了。他反正是剥削穷人,对老百姓不好——请人挑煤炭、挑柴只管饭,不给钱。解放后没有枪毙,给斗死了。这个魏少柏,在万县街上的房子比在农村还要多些。解放后,土地、房子全都分了,他的两个女的也都走了,大婆子姓秦,是上海人,后来去了涪陵;小婆子姓崔,后来不晓得去了哪里……”
旁边的老人们又说:“解放后,在密溪沟还是枪毙了几个地主:魏守之两爷子[77]都枪毙了(老的七十几、儿子四十几);还有教书匠魏延九,原先他还办学、教古文的,罪行是‘反革命一贯道’;还有文峰村宝塔乡的陈静安,是开药铺的……一齐枪毙的,就在江家桥二完小(第二完全小学,后来的翠屏二小)打的。公审大会一开,群众喊口号,乡镇府朱笔一勾,判处死刑,抽出去立即枪毙……”
“还有保长姜润之,没有枪毙,他心术不正:别人到他田里放水,他就在那个缺口放了好多玻璃,把人家脚划了,后来判了刑……”
“1958年大办钢铁的时候,”黄开清老人接着说,“我们这里男的女的,各人背着铺盖,都去了新田的广头山,走去花了一天,在那里住了两三个月;住宿都没有安排好就去了,老百姓的房子住不下,露天坝坝里都可以睡;挖来好多矿石,还是炼不出铁来。周围的松树、柏树都砍了,砍来烧‘黑棒槌’,还是搞不赢,又到新田农民家里去收东西,把衣柜、散谷子的风车,还有埋人的木头都装上船,运来烧,投到高炉里面炼铁,还是没炼出铁来……后来高炉垮了,又回来种庄稼……”
就在何贤功家门前,老人们断断续续回忆着,直到下午,天色渐暗,老人们才逐渐散去。我又跟着谭明武师傅,穿过一人多高的野草,经过泥泞的山间小道,回到他们家,万州江南新区旅密4组1号,见到谭师傅双目失明的妻子冯天英。
而回到屋里,关起门来,谭师傅这才跟我说起他的伤心事:“那是1979年7月11号中午12点,当时大儿子才九岁,我们一家人都在湖南怀化——因为是在成昆线上生的娃娃,就给他起名叫谭永昆。当时我还是好不容易求人家,把娃娃带上读书的,他就在鸭嘴岩公社铜锣小学。那是热天,中午几十个娃娃一起放学回家,在河边洗澡,因为大河涨水,小河涨满了,他掉到那个凼凼里淹死了。遇到这种事情,我们男同胞还可以喝个酒,打个牌,他的妈妈就想不开,后来眼睛瞎了,跟这件事绝对有关。”
说话间,谭师傅的妻子从里屋走出来,她双目失明,却很健谈。问及往事,她先从家乡说起:“我的老家在万州凉水乡红冲沟,离这里二三十里。当地老百姓说:‘好个红冲沟,三年两不收。要不是两束香把把,眼睛都要饿落抠。’就是说那里多么穷,幸亏靠的烧香拜佛,才得到点儿收入。”
“怎么会?”我问。
“我们那里有个活佛,叫谭世珍,是个农村妇女,她好大的本事哦,说神扑到她身上去了,人们都信奉她。她是个好人。你哪里不好去找她,她就给你说些草药……她结了婚的,男的叫向秀炳。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遭整,说她是‘四类分子’,牛鬼神蛇,把她看管起来,叫她喂猪,我们当娃娃的时候还给她打过猪草。后来她死了以后,就埋在茶店子转过来,一碗水那个庙外面;那里有个凼凼,好像一碗水,天干也不会枯竭。她的坟多么红火,立了好多碑,每年都有人给她烧香、挂红,还有的烧整猪整羊……”
“你问我自己么,我姓冯,叫冯天英,1947年出生在红冲沟的锅灶湾,家庭娃儿多,穷得不得了。我妈妈四十多岁就害病死了,没得钱医,要落气的时候还在说:‘我要吃药,我要吃药……’她得的是肺气肿。那时候,家里人生病,肚子里长虫,就弄点石灰水来喝。我读书只读了两册,十一二岁就下地干活,当时伙食团刚刚成立,没什么吃的,那个菜汤就拿来喝,也没有油,没有盐的,那些生菜野菜、梧桐树皮皮、观音米都吃过,那真是遭孽……”
“到1959年下半年,我的脚肿了,路都走不起。”谭师傅接着说,“我大嫂的前夫徐仁富就是饿死了的,还有那些老实的农民,像周兴禄、冯文秀、刘克云、谭世福也饿死了,谭世贵差点儿没饿死。当时,我们旅密4队有个村支书叫冉启元,不抽烟、不喝酒,就是对当官的好,对下面凶。我去打点儿胡豆充饥,他就看不得,说‘给猪吃,也不给你吃’。就有那么凶。我的继母熊兴珍偷了一个红苕给她儿子吃(当时我十三四岁,她儿子还要小些,姓陈),就被他们用绳索吊起来,吊在伙食团屋里……别人先把她整惨了,后来她又整别人,揭发大队领导,说他们瞒产……”
而这时,大嫂还在一旁打趣说:“当时就听说:毛主席的政策差不多,大鸣大放紧我说……”
这时,天已经黑了,谭师傅去厨房做晚饭,大嫂话题一转,又跟我说起惨烈的往事——
“我是1969年从红冲沟嫁过来的,当时我妈妈就觉得离开红冲沟怎么都好;密溪沟是要比红冲沟好些,但还是遭孽。那一年丈夫不在,我一个在家,谷子熟了,我忙着去收,忙忙慌慌,加上累晕了,一头撞在门框上,本来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另一只眼睛也撞瞎了……”大嫂冯天英说,而对于自己夭折的亲生儿子,她却只字未提,我也没问,怕太伤心。
而后,她又说起“文化大革命”,还是伤心事——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红冲一队,说是地主要反扑,要当家做主(其实是造谣,没那回事),那些青年积极分子就行动起来,要斩草除根;他们就把地主向惠民、张泽法……总共十几个人关到一个屋子里,那是原先地主住的板壁砖屋;(天)黑了就用绳索把他们捆起来,拉出去,用钢钎拗下去,拗到生产队装红苕的那个凼凼里,用炸药包炸……”
“炸药包炸响了没有?”我问。
“啷个没炸响呢?炸药包炸响了的,底下的人还没炸死,他们又把那些大石头抬起扔下去……后来又把那坑坑填起来,在上面种上庄稼。那些地主的子女就来问:‘我屋爸爸、妈妈都到哪儿去了?’他们就说:‘你莫问,你屋爸爸、妈妈有饭吃!’”
“算了,老娘,不说了!”谭师傅回屋说道。
大嫂停了下来,而谭师傅自己又叹道:“那是无法想象的十年。”
我试图解释,却又说不出什么。在密溪沟,时光仍停在另一个维度。
而大嫂一笑,两只突出的眼睛都在颤抖,她还接着说:“‘文化大革命’,红冲大队死了人,芭蕉大队就没有死人——那些人已经把地主押起,要枪毙的时候,那个枪一抠不响,二抠还是抠不响。那些地主还说:‘要不你给我,我来试试。’——‘给你?!’他们说,后来还是没法,就把地主都放了……”
晚饭相当丰盛,但我是素食者,也不饮酒。他们尊重我的习惯,而这个习惯我刚刚养成,不到两个月,无他,心有戚戚焉。
本想今晚就住在谭师傅家里,可面对昏暗的房间、艰辛的生活、荒凉的密溪沟,我感到不堪重负,执意要走。就这样,晚饭后,谭师傅送我走过一段黑暗的羊肠小道,来到有街灯的大路边,叫了一辆摩托车,一路狂奔逃回云阳。
是夜,密溪沟又成密溪峡,从窗外黑沉沉的江面蚌壳似的张开。我只有在精神上继续前行,深入那些在现实中去不了的地方。我确信那里的存在。我的船,我的诗歌正缓缓接近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