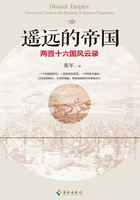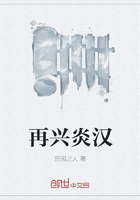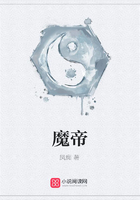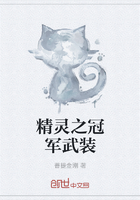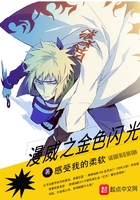本书于2016年2月首次付梓。那时,我曾在开篇写道:全球史风头正劲。但是,眼下的情形是否依然如昨?全球史是否依然如日中天?每位历史学家是否依然都是世界史学家?自彼迄今,仅略略一年有余,有些读者或许不以为然,但这个世界确已今非昔比。欧美地区出现了民粹主义和旗帜鲜明的反全球化运动,多地推行保护主义和限制移民的举措。面对这股抵制全球化的强流,全球史的盛景是否已时日无多?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首先,民族主义的重新抬头,包括“美国优先”此类口号的出台,都不能视为对全球化的反抗。自19世纪以降,民族主义就与跨国性的全球力量紧密相联。从多个方面而言,民族主义是日渐增强的跨区域互动的一个结果。因此,2008年以来民族主义议程的复兴,并不昭示着全球化的终结,相反却象征着全球化的高歌猛进。
其次,有人猜测当前的反全球化潮流或许裁定了以流动和缠结为研究对象的全球史的命运。我认为这种观点缺乏远见。全球史学者或曾迷恋于运动与关联,但很多关于全球进程的论述都极具批判性,指明了市场一体化和殖民主义的社会成本,以及各地区发展水平的不均。左派抑或右派对全球化的批判,并不等同于对全球史这种研究取径的批判。
最后,我们无法单凭内部冲突和国内因素,来理解政治领域里对民粹主义的吁求和仇外情绪的高涨。看似自相矛盾的是,尽管从字面意思而言,民粹运动意味着决然孤立,但世界各地的民粹运动却相互影响。另外,如果我们意识不到全球冲击带给它们的影响,将难以解释这些运动的同步发生。近年来的诸多变革性事件,从金融危机到“阿拉伯之春”,再到眼下的民粹主义大潮,无不呈现出跨国之势。换言之,为了认清当前这个时代,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全球取径。
本书大部分内容最初以德文版本面世,那时我心目中的阅读对象是德语读者。尔后我主要针对英语读者,以英文进行了改写,本书方有了现在这个版本。本书被译为多种语言,比如中文,但正文内容并未做出改动,亦即并未因中国的国情而调整内容,也未专辟段落论及中国题材以及中文史学。这无疑是一个缺憾。不过,我坚信这种改写将会发生。即便不是由我亲自操刀,也会有中国的下一代全球史家接手此事。他们将从自身立场出发,运用并改进全球史这种取径,进而推动学术交流。那时,此类学术交流不仅在内容上关乎全球,交流活动本身也将真正是全球性的。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
纽约,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