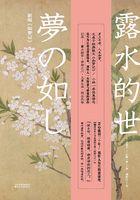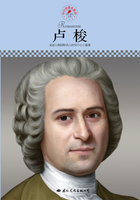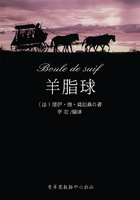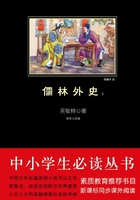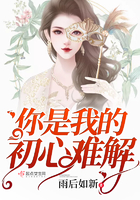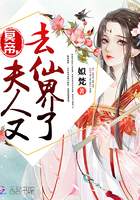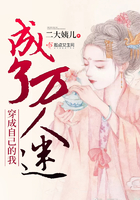钱振文
一
1924年9月15日,在搬入宫门口西三条21号新居不到四个月的时候,鲁迅写了后来出版的散文诗集《野草》中的第一篇《秋夜》。开首第一段就是:“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秋夜》后来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个奇特的句式给所有的中国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鲁迅的学生许钦文就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说:“‘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已成为大家爱颂的句子。”(许钦文《在老虎尾巴》)
鲁迅搬入西三条那年的冬天,年轻的李霁野在同样年轻的小学同学张目寒的带领下去看早就崇拜的鲁迅先生,在漫长的聊天中,鲁迅告诉他们说:“他的文章里找不出两样东西,一是恋爱,一是自然。”(李霁野《忆鲁迅先生》)在鲁迅的文章中,对鲁迅说的“自然”即现实环境中的风景的描写,大家熟知的只有两处,一个是《〈呐喊〉自序》中那个S会馆里曾经“缢死过一个女人”的槐树,另一个就是西三条21号院后墙外的两株枣树。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两处地方的槐树和枣树都在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时候就消失了。这两处早已不在场的风景都在北京的西城,距离并不远。几十年来,无数慕名参观绍兴会馆和鲁迅博物馆的游人,在走进著名的“槐树院”和“西三条21号院”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寻觅那个在脑海深处贮藏许久的大槐树和两株枣树。当他们得知大槐树和两株枣树早已不复存在的时候,无一例外都会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惋惜和叹息。在得知这个令人扫兴的事实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无可奈何地表示接受。毕竟,树木也是生命,也有生老病死。但有的人对这个事实难以接受甚至表现出痛苦和愤怒。毕竟,槐树和枣树不是什么珍稀植物,而是北京的常见树种。在北京老城区的四合院中和胡同边上,到处都可以看见百年树龄的老槐树和老枣树。为什么偏偏消失的是鲁迅先生看见的那两株枣树?
四五年前,一位外地的鲁迅迷潘卫华先生在第一次访问鲁迅故居并得知那两棵枣树“早已枯死多年”后,就曾经“痛心疾首,扼腕叹息”,在此之后,三番五次专程到北京,研究和考证鲁迅在《秋夜》中所写的两株枣树,最后写出了很长的文章《谁动了鲁迅故居的枣树?》。在这篇文章中,潘先生得出的结论是:“我要大声地告诉人们,先生笔下的那两株枣树并没有枯死,它们仍然健在!仍在倔强而茂盛地生长着。”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是,当潘先生踯躅在鲁迅故居后小院时:“回头望去时,分明有两株高大的枣树,映入我的眼帘。一株位于前园的西墙外,一株位于过道的西墙外。‘那最直最长的几枝’,分明正‘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潘先生发现的两棵枣树,一棵位于从前院通往后院的夹道,另一棵位于故居的西邻院,当年住在这里的是曾经帮助过鲁迅的姓白的木匠。这两棵枣树的确是潘先生请植物学专家论证过的“树龄至少应在百年以上”的老树。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每年都会在大枣成熟的时节上树打枣吃,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两棵枣树的存在。当然,把这两棵枣树当作是鲁迅看到的“两株枣树”的并不只有潘先生一人。鲁迅博物馆的老专家叶淑穗就曾经发现,2013年6月23日《北京晚报》上的一篇文章《北京名人故居中的古树》,也同潘先生一样把这两棵活着的枣树当作是《秋夜》中的两株枣树。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河北日报》的记者原付川先生(他前些日子来鲁迅博物馆采访鲁迅收藏正定隆兴寺观音像的事情)还打来电话,询问《秋夜》中的那两株枣树到底是不是现在院子里的这两棵枣树。实际上,故居前后院夹道里的这棵枣树的确引人注意。早在1949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纪念日也是鲁迅故居对外开放的第一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记者柏生的文章《访鲁迅故居》,文中写道:“大门里是一个小而雅致的院子。院子当中有一株枣树,在前院通往后院的门外墙角边还有一株枣树。一九二四年,鲁迅先生在这所屋子写了《秋夜》一文,提到在他的后园墙外有两株枣树。所以这两株枣树是很令人注意的。它们端庄地矗立着,它们的枝干仍像往日一样地刺向天空。”文里所说的院子里的一棵枣树大概也是鲁迅先生搬来之前就有的,因为,1925年初,作家章衣萍的年轻妻子吴曙天第一次来这个新落成不久的小院访问鲁迅,在随后发表的文章中就提到“院里有一棵枣树,是落了叶子的”(《访鲁迅先生——断片的回忆》)。很显然,当时,鲁迅故居院子里还没有现在枝繁叶茂的鲁迅在1925年4月亲自栽种的丁香树。这棵在前院更显眼位置栽种的枣树鲁迅故居上年岁的工作人员也是见过的,当然,也在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时候死掉了。关于北京人的爱在院子里种枣树,郁达夫的一篇文章《回忆鲁迅》也可以为证。1923年鲁迅从八道湾11号搬到西四砖塔胡同61号租房居住的时候,郁达夫在这一年的冬天正在北京大学做经济学教授,有一天去看鲁迅,就发现:“一个三四丈宽的小院子,院子里长着三四棵枣树。”现在,如果你去鲁迅博物馆外西二环路边上的街边公园转一转,就会发现许多棵比鲁迅故居院子里的枣树还要粗大的老枣树,这些枣树肯定也是原来的四合院拆迁后保留下来的。
二
但是,所有的这些枣树都不是鲁迅在《秋夜》中所看到的枣树,那两棵枣树的确是在很早的时候就没有了。
的确如叶淑穗老师所说:“这两株枣树,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枯死。1956年10月鲁迅博物馆建馆后几经补种,均未成活。现今从鲁迅故居后院的墙外,已看不见这两株枣树了。”(叶淑穗《〈秋夜〉中的两株枣树》)就在《人民日报》记者柏生的文章中,也写到了这两株枣树:“有人问起后院墙外的两株枣树,现在已经看不见了,许先生用脚踢着一根已经干枯了的枣树根说:‘这里原有一株枣树,不知后来被谁锯掉了。’我们已经看不见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些野草,更看不见小红花在那里做梦了。”(柏生《访鲁迅故居》)文里的“许先生”就是许广平,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在百忙当中积极进行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北京和上海两地鲁迅旧居的整理和对外开放。两地旧居中的许多事情,她都是当事者和见证者。1950年3月,许广平把宫门口西三条21号鲁迅旧居和全部鲁迅遗物捐献给国家,文化部文物局给她颁发了“褒奖状”。5月,文物局派人去故居进行文物清点工作,许广平亲自指导。在清点工作的最后一天,许广平说到了这两棵枣树,“最后,她无限深情地来到了后园,仰望着后墙,良久,她说:‘很可惜那两棵枣树没有了,1946年我来时,就没有了。’当年,我们在‘老虎尾巴’与鲁迅先生谈话时,确实看见墙外的这两棵枣树。”矫庸也补充说:“‘观众中不少人都问这两棵枣树到哪里去了?’”(罗歌《我要把一切还给鲁迅》)这里说的“看见”墙外的两棵枣树的“当年”,应该是1925年,从这年的4月,许广平开始和鲁迅通信,12日,许广平第一次到鲁迅家探访。许广平肯定在此之前已经看过了鲁迅在几个月前发表在《语丝》上的《秋夜》,因此,在16日许广平给鲁迅的信中说:“‘尊府’居然探检过了!归来后的印象,是觉得熄灭了通红的灯光,坐在那间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是时而听雨声的淅沥,时而窥月光的清幽,当枣树发叶结实的时候,则领略它微风振枝,熟果坠地,还有鸡声喔喔,四时不绝。”
不知道是许广平的这次清点工作中对两棵不在现场的枣树的观望发生了作用,还是故居管理员矫庸对不少观众“都问这两棵枣树到哪里去了”的重视,总之是在这不久,故居后院院墙外就补种上了两棵枣树。鲁迅博物馆前副馆长王士菁回忆自己1951年7月第一次参观鲁迅故居时说:“故居前院的丁香是鲁迅手植的,后院的一簇簇丛生在井边的刺梅也是鲁迅亲自买来的,墙外两棵生长在邻家院内的枣树,那是后来补栽的。”(王士菁《杂忆》)但显然是这次补栽并没有成功,因为,根据叶淑穗老师和鲁迅博物馆当年的记载,都说明在1956年鲁迅博物馆建馆的过程中又补栽过一次,但根据当年的记者孙世铠在1956年10月19日鲁迅博物馆开馆前的报道,这次补栽的两棵枣树中的一棵还是没有成活:“文中所指的枣树早已被邻人砍去,1956年又补种了两株(一株已死,现剩一株)恢复了往日的情景。”(孙世铠《鲁迅在北京住过的地方》)不知道这次补种之后是否又曾补种,但根据曹聚仁编辑的《鲁迅年谱》,可以肯定的是到十年后的1966年,这里仍然生长着两棵补种的枣树。在《鲁迅年谱》中,编者说:“编者最近去看了一回,那两株枣树,原已砍去了,而今又补种出来了。”(曹聚仁《鲁迅年谱》)至于后来这两株枣树是什么时候怎么没有的,就没有说法了。
三
几十年来,人们对找到散文诗《秋夜》中所描述的两株枣树的对应原物的审美冲动一直没有消停。最近几年,鲁迅博物馆围绕鲁迅故居风貌复原的话题,不断产生再次在原址补栽《秋夜》中两株枣树的想法。但到了时过境迁的今日,补栽的意义其实并不大。即使有两棵年轻的枣树生长在原来的地方,也早已经不是当年许广平他们看到的枣树,更不是鲁迅在那个秋夜看到的那两株枣树了。
其实,在鲁迅故居周围的各个地方并不缺少枣树,但“野渡无人舟自横”,并没有人对这些普通的自然物多看上几眼,更不会产生文化的联想。鲁迅所看到的那两棵枣树本来也只是普通的枣树,只是因为鲁迅把它纳入到了自己的主观观照和意义框架中,才让它们产生了符号的动能和象征的意义。
当然,如果那两株鲁迅观照过的枣树还在的话,它们肯定也不是普通的自然物,而是充满意义的符号。只是,由于符号和意义之间距离遥远,我们普通人对它的欣赏,不一定能够解读出鲁迅所说的“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经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倒是20世纪70年代,在没有了实物的情况下,画家周元亮、陆燕生等根据鲁迅作品创作的画作《秋夜》等中的枣树,更接近鲁迅所看到的那两株枣树。
其实,那两株枣树在鲁迅写完《秋夜》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虽然不在现场,但当许广平和所有来鲁迅故居参观的人们,在后院向后墙外眺望的时候,脑海中分明涌现出两株桀骜不驯、冷硬不屈,和其他在场的枣树迥然不同的枣树。正因为不在现场,才让人们几十年来持续不断地对它述说和描绘,以填补两株缺席的枣树所留下的空白。
“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
那两株枣树其实没有死,它们就在那儿——在鲁迅的《秋夜》中——活着。
(原载《博览群书》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