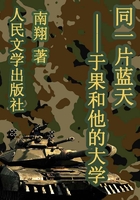Fear
杰西是神经性厌食症患者,抑郁症在厌食症中很常见。杰西觉得她被困在了无法理解的事情里,他很害怕如果她开吃的话,体重会增加。她觉得她不能冒这个险,她看不到出路,把来医院看病当作是会威胁道她控制现状的事情。她害怕失去控制。
紧张会让我越来越恐惧和焦虑。而当我觉得好像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时,绝望就会立刻袭来。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感觉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然而,我也知道,这种保持控制的需求会阻止一个人在他真正需要帮助时向他人寻求援助。因为接受帮助也同样被他们看作是放弃对自己生命的掌控,是屈服,是失去个人自由。这确实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感觉。
孱弱瘦小的杰茜不明白人们都在担心什么。“你看,我什么毛病都没有,我一切都好。我不想待在这里,我只想回家。”她告诉我,“我妈妈会担心我去哪里了。”
“我想护士长已经告诉她你来这儿了,你妈妈很担心你。她希望你留在这儿。”
“不,你弄错了。我是告诉过医生我会留下,但现在我已经改变了主意,我需要回家照顾我妈妈,难道你不明白吗?”
她用一根瘦骨嶙峋的手指擦去了眼角的一滴泪水。她的双手看起来透着蓝色,但不是特别冷的那种,鼻子蒙着忧郁的紫色阴影。她看起来很脆弱,但意志坚定、充满决心。
杰茜是我在爱丁堡大学学习精神医学时接诊的病人之一。她17岁,身体状况极其糟糕。
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当一名医生,15岁左右的时候我才突然有了这个想法。那时我意识到我不再想当一名生物学老师,虽然我曾把它当作我前进的方向。原因很简单,我当时擅长理科,也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如果我不那么焦虑的话,我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努力成为一名生物学老师。问题是,很多时候我的确为此焦虑不堪。焦虑成了我的常态。
有些人认为焦虑和恐惧是可以互换的概念,它们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那么清晰。我倾向于认为,恐惧是由一个特定的刺激诱发的消极情绪,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出是什么激发了这些内在的情感和情绪;而当我们感到人身安全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威胁,却无法确定原因时,我们经历的则是焦虑。焦虑时,我们只是感受到身体上的一些不愉快的感觉,并开始不明所以地担心日常琐事。我们恐惧的可能是一些生活中我们还不熟悉或尚在沉思但还说不出名字的事情。
在爱丁堡大学接受医学训练的那5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从未考虑过以后会从事心理疾病方面的工作。我的朋友简将成为一名精神病医生,而我会当内科医生,关注身体的疾病。
简成了我最好的朋友,虽然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也是她最好的朋友。她是个身材矮小、极其聪明的南方人,有着一头长而凌乱的深色金发和刺耳的笑声。第一年简和我穿着被用来保存解剖尸体的甲醛浸得湿漉漉的棕色工装裤,一直在同一具“尸体”上一起工作。被部分肢解的躯干和四肢的油腻气味,渗透了我们的衣服和头发,晚上回家也挥之不去。我们都生活在对一位解剖学老师面试的集体恐惧之中。她是一名头发灰白的年长女性,梳着一头紧绷的盘发,一只手装着弯钩假手,她就用它来指着解剖体上的肌肉和神经。她对离我们几张桌子之外的一个女生咆哮着抛出她的问题。
“她怎么回事?”我问,被她用弯钩假手操作尸体的灵巧敏捷惊得目瞪口呆。
“她摔断了胳膊,”简低声对我说,“急诊室的工作人员处理得一团糟。血液供应被切断,然后不得不截了肢。”简转身紧紧凝视着我,又说:“她喜欢把女同学弄哭。”
“因为……”我知道她接下来要说什么。
“急诊室工作人员就是位女性。”
学医的5年基本上是学习如何建立起信心去谈论你知之甚少的事情。我的问题在于,我一直信心不足。在爱丁堡我觉得格格不入。我没有像大部分同学(包括简在内)那样的背景:我母亲在一家工厂工作,组装晶体管收音机,我父亲在一个游乐园上班。
“你不开心。”一个晚上我的朋友斯蒂芬说道。斯蒂芬是爱尔兰人,非常聪明。一周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在一起喝酒,幸好我一直保持清醒,才能在他喝下了半瓶格兰杰之后将他翻身让他侧躺保持复原姿势。
“我应该感谢你,因为你救了我的命。”斯蒂芬喃喃地说,换了个话题。
“你说‘我不开心’是什么意思?”我问道,把话题又换了回去。
“分离焦虑——我想是这样。”那时我们刚刚开始学习“行为科学”。在他提出这种可能性的时候,他看上去有点紧张,不敢看我的眼睛。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问道。
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它听起来令人不安却又形容准确。我想念家里的什么东西,但我无法弄明白那是什么。家里没什么事是我觉得必须急着赶回去的。爸爸和我已经疏远了,在我叛逆的少年时期就彼此生气,我都不明白是为了什么生气。我申请读爱丁堡大学就是为了远离家乡,学期结束前我不能回家。
“分离焦虑”,斯蒂芬重复说,“我想我说对了。”
第一学年末时,我父亲心脏病发作。六周后我才得知此事。我在苏格兰度过了我的第一个暑假,在西部高地的一家酒店打工。我外出的时候经常给家里打电话,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出事的暗示。我回到爱丁堡时,从朋友公寓街对面的电话亭里再次给家里打了电话。
“你爸爸一直住院,”母亲语气平淡地说,“他外出游泳后胸口痛。我们当时都在车上,当我们回到家时,他已瘫倒在路边的草坪上。”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真不敢相信。”
“他不想毁了你的假期。”
难道我们之间如此疏离,他竟然不想让我知道他得了重病?
我记得在某一次考试前,也就是上大学之前的一个夜晚,气候温暖,微风吹过大海。
“把书收拾起来,我们去海滩!”爸爸说。
“雷,你之前说过你今晚要整理这些保险单的。”妈妈反对,但是爸爸对她的不满置之不理。
“我要继续复习。”我试着拒绝。我无法不去想即将来临的考试,还有我担心考试失败。
“雷!”母亲再次试图改变他的想法。
“明天我会整理出来,别担心。”爸爸一边接着说,一边瞧着我。“你甚至集中不了注意力,我们去放松一下。”
“那就随你便吧。”妈妈大声说道,“砰”的一声关上后门。
当我们到达海滩后,我尽情享受着脚趾缝里温暖的沙子带给我的触觉,我脱掉衣服,穿着泳衣淌入凉爽的水中,看着爸爸自信地快速游向与海岸线平行的沙丘。我不会游泳,我从未学过。北海通常看起来是灰色的,但在夕阳下当海浪退去时海水看起来几乎是蓝色的,退潮在平坦的海岸线上留下了一道道像蕾丝褶皱边一样的泡沫。在海浪中我蹲下身,让冰凉的海水冲刷掉我的疲劳。爸爸游回来,抓着我的手让我漂浮一会儿。然后,我突然感到一阵害怕,我挣扎着在满是淤泥的海底站起身来,扬起的沙子搅浑了之前清澈的海水。
“相信我,我不会松开你的手。”
但我做不到。我还没有信任他到敢让我的双脚离开海底的程度,然后我察觉到他对我极其失望。
在爱丁堡最后一学年的某个早上,我终于意识到我永远不会成为一名成功的内科医生。当时我站在皇家医院的一张病床旁,床的四周拉着帘子,我手中握着一只注射器,弯腰朝向一位惊恐的仰面躺着的妇女。
高级住院医师站在床尾,吩咐道:“赶紧扎进去!”
当我逼近她的胸部从她的胸骨处采集骨髓样本时,这位妇女的脸部表情几乎完全映出了我的表情。我可以感觉到额头上的汗珠子在聚集,顺着我的鼻子向下淌,最后滴到了她的脖子上。
“没错,就是这样子。你感觉得到针扎进去时针头轻微地弯曲吗?”老师问。
“当然感觉到了,”躺在床上的妇女回答道,“我以为你真的打算杀了我。”我希望没有人告诉她,去年一位医科生确实杀死了一个病人:在学习如何采集骨髓样本时,这位学生直接把针扎进胸腔,戳破了一条动脉血管。
我点了点头,但是我不确定我的感觉。我的手由于害怕而汗津津的,结果费了好大劲儿才把无菌手套脱下来。
我现在明白了,对我这样的一位大四医科生来说,结婚是一种试图控制自己不再增加焦虑感的方式。不知为何,婚姻让我对未来感到更安全,更有保障。我是在大一的一次戏弄新生的电脑约会游戏中(简拉我进去参加游戏)遇见我男朋友的,他叫吉姆,当时正在完成他的物理学博士论文。我们在违背父母意愿的情况下结了婚,在一所合租公寓的一个房间里同居了两年,这件事让他们感到震惊。嗯,那是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伦理道德与现在大相径庭,尤其是在苏格兰地区。
我的生活开始围着坐落在新城区出租公寓楼一楼的这个房间打转,它既是我们的卧室、客厅,又是书房。在这个房间里,在某个潮湿阴暗的爱丁堡式的下午,我总是瘫坐在单人沙发上,凝视着被之前的租户恶作剧地漆成了白色的大理石壁炉中的煤气取暖炉,倾听着破裂退色的炉子里的火焰发出的嘶嘶声。我们继续过学生生活,和其他人一起喝酒、聚会,竭力弥补收入上的不足。但是与此同时,几个月过去了,我们渐渐适应了婚姻生活:周六购物以及为我们将来的家制订计划。
我拟了一份详细的期末考试复习时间表。第五学年已经过了一半,可以说医学培训暂时已接近尾声。那年的一段时间里,我试图继续自欺欺人,假装一切完全正常,我只不过是在应付工作上的压力。我像以前一样害怕考试失败,但也有一种可怕的焦虑感,担心某件我还说不出名字的事情即将发生在我身上。我说服自己,世界上最好的控制自我的办法就是在考试来临之前绘制某种包含一切在内的思维导图。我在纸上划掉一行行的句子,创建了一幅支配我以后几个月里每天日程的图表。我不想承认这与我弟弟当初痴迷般地试图控制自己焦虑的方式之间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我安慰自己说我的这种行为是完全理性的。
几个星期的时间在没完没了的只工作不玩耍中浑浑噩噩地过去了。在1979年初春的某个下午,离期末考试还有两三个月的时候,精神科专科医生戴夫,发现我坐在精神科病房治疗室的角落里。我头天晚上没睡着。我的心怦怦直跳,我试图让它跳得慢一点,却没有成功。
“你还好吗?”他问。
我避开注视着他的目光,不愿泄露任何东西。“是的,我很好,只是有点疲倦和紧张。”
“你要向老师作汇报,是吗?精疲力竭,对吗?”
L教授是一位杰出的精神病专家,但是对一名渴望给人留下印象的医科生来说,他是位可怕的听众。当他灰蓝的眼睛不动声色地扫视整个组的人围坐成一圈等着他查房的房间时,他的脸上一直都面无表情。那时,我正跟他谈论我头天见过的杰西。
“那么你的诊断是什么?”L教授问道。
“神经性厌食症。”我回答,“但我认为杰西还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她说过有时她感到很绝望。”
“抑郁症在厌食症中很常见。”他解释道,停了一下后又问,“你在担忧她什么?”
我深吸了一口气,回忆起杰西极度痛苦的脸。“我认为她觉得被困在了她无法理解的事情里,她很害怕如果她开吃的话,体重会增加。”事实上,她说的有关尝试正常饮食的原话是:“我不能冒这个险,因为一旦我开始吃东西,我永远都不会停下来。”
“确实如此,”我说道,从我写的记录上抬起头,“她看不到出路,把来医院看病当作是在某种程度上会威胁到她控制现状的事情。她害怕失去那种控制感。”
我停了一会儿,看向另一边的戴夫,他坐在房间的尽头,为了安心,早在病室巡诊开始之前我就和他一起彻底测试了我的想法。他点了点头,微微一笑。
我接着说:“目前,我认为杰西觉得可以控制自己的饮食,但是仅此而已。”对于她本人,她对家庭和未来有着更深层次的恐惧和担忧,而她至今无法承认这些。教授点了点头。“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亲自给她看过病。你做得非常好。”
教授几乎不易察觉地强调了“非常”这个词。我感到了一丝满意,但转眼即逝。我能够想象自己轻而易举地进入精神病患者的精神世界里:焦虑,抑郁,甚至偏执。我觉得我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不仅因为我似乎有某种精神病学方面的天赋,而且因为病房里的生活与我内心的某些东西产生了共鸣。然而,这也使我担忧,因为我可以充分感受到病人所描述的一些经历——不是作为一位客观的观察者,而是从内心深处去感同身受。
所以,当戴夫发现我独自一人在查房后待在治疗室时,我可以看出他十分担心。“你确定你不想谈谈吗?”戴夫坚持道,伸出手仿佛想触摸我。
“不,老实说,我很好。”我一边说,一边摆脱他。“只是有点担心期末考试,仅此而已。”
但我知道这不是事实。由于筋疲力竭,我感觉心脏好像要停止跳动了,这是我现在很熟悉的一种感觉。
桑德拉是另一位我还在精神科实习时就渐渐开始了解的病人,那是在期末考试前几个月。她有严重的躁郁症家族病史,这意味着她不仅经历抑郁症的发作而且有时候兴奋异常、过分活跃和兴高采烈。桑德拉已开始电休克疗法(ECT),这种疗法现在常被当作治疗与厌食症有关的严重抑郁症的杀手锏。这种治疗需要让电流通过大脑而诱发癫痫发作来作为挽救生命的措施。这种治疗听起来很野蛮,事实上在过去情况的确如此,而且许多人通过电影《飞越疯人院》而知道了这种治疗手段。现在,使用WCT是在全身麻醉和使用药物让肌肉无力的情况下进行治疗,以便几乎察觉不到痉挛,但是它仍然是有争议的,有时会出现问题。
桑德拉如同以前一样在逐步好转,但我知道ECT导致她的记忆力出现了问题。我进去她的房间,在她身旁坐下,片刻之后,她慢慢地、几乎是机械地转过脸来看着我。她的眼睛里充满了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那是一种似乎哭泣都无法减轻的痛苦。她眼底的痛苦如此之深,让我莫名地明白了她为何无法谈论它。这是一个凄凉寂静的世界,所以我陪着她,一言不发,我们不时地交流一下眼神,但仅此而已。
几周后,桑德拉告诉我,当她情绪非常低落时,她认为她不应该活着。她告诉我:“我当时不想和你谈话。我想让你离开,让我一个人待着,但是我又无法忍受你离开我,我很害怕将会发生什么。我很害怕再次接受电休克疗法,但不仅仅如此。我想死……我同时又非常怕死。你能理解吗?”
这是可怕的困境——接受帮助或保持掌控自己生活的可怕的矛盾心理,即使它最终意味着失去生命——在桑德拉的眼睛里我读出并认同这一点。
几周过去了,我每天一大早就醒了,听着送牛奶的马车沿着爱丁堡的鹅卵石路发出卡嗒卡嗒的声音和远处的上下班高峰期交通开始拥堵的声音,害怕新的一天的开始。我的生活是按照图表上标出来的时间段安排的,每个时间段都规定一个我必须实现的目标。如果未能达到每天的目标,我就可能会耗费更多的时间,纠结于如何重新制定时间表。可以说,我被铺在地板上的白纸控制着。早上我开始花费越来越长的时间在起床上。有时如果不需要出门的话,我会忘记梳洗或穿衣,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情况常常发生。我悄悄溜进复习讲座的教室,但避免与任何人交谈。我远远地观察着同学们在密谋的圈子里进进出出,起起落落,变幻莫测。我确信他们知道所有我不想让他们知道的有关我的事情。我相信他们知道我会考试失败。当然我们中的几个人会考试不及格。晚上我绕着公寓踱来踱去,担心我弟弟童年时遭受的心理问题也开始让我品尝苦果。
与此相反,吉姆在理性和逻辑的科学世界里忙碌着。我越来越古怪的行为让我的丈夫感到困惑,如同我想象着他的一个实验未能按照预测进展而让他不知所措。
“你到底在做什么?”一天晚上他问道,我当时正坐在炉火旁的单人沙发里,前后摇摆。
“我正试图摆脱痛苦。”我咕哝着。肠道的某种压力让进食变得困难,我在夜里被绞痛折磨得醒来,只能通过摇晃来减轻疼痛,就和小时候我弟弟感到沮丧时的举动一样。
“你不觉得你应该去看医生吗?”他问。
“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毛病。”我尖叫着反击,尖叫声响彻了整个房间。但他可以看出我很害怕。我现在知道那是什么,虽然我那时候努力地想给它取个名字:对失败的畏惧在阴暗中不断纠缠着我。
有一次我终于坚持不住了。我头痛欲裂,努力保持清醒。我不记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坐在公寓里,纠结于时间表如何制定以及自己能否遵守时间表,与此同时我倾听着人们在公寓楼梯间的喧哗声。他们来回走着,互相聊天,谈论天气以及轮到谁来打扫楼梯,好像一切都很正常。我清楚地听到邻居们进出通往街上的大门时哐哐地关门声,新月街交通的嘈杂声,窗外的鸟叫声,滚滚红尘与我擦身而过。我没在睡觉或工作,只是在哭泣。
最后,我屈服了,并约好去看医生。我去看了家庭医生,他让我去找一位心理医生(我叫他P医生),他在医学院的健康中心上班。这更让我难堪,因为P医生立刻认出了我。
“你刚刚……”
“没错,”我说,“我在你的工作小组进行过精神病学实习。”
同一周的晚些时候,他让我去见他的同事,另一个教授(我叫他M教授)。他着装优雅,身穿一套灰色西装,胸前的口袋露出一个粉红色的手帕。这种打扮让人难以集中注意力。我发现自己试图去猜手帕被折叠了多少下,以及如果病人开始哭泣,他是否会掏出手帕递给病人。我确定他极有可能不会这么做。
“你在担心什么?你害怕什么?”他以一种要求回答的方式问道。当有人想进入我的世界,我本能地进行抵制并保护自己,以便保持控制。这感觉就好像在自我的已破裂的外壳下面,他正试图刺穿最后一层脆弱的薄膜。也许他的意志比我坚强,因为我不仅告诉了他关于考试的烦恼,而且还跟他谈了有关我弟弟的事情——他得的精神疾病,以及弟弟在只有七岁的时候开始的古怪行为。
“你担心同样的事情正发生在你身上?”他问。
“是的。”我说。我知道这是我最深处的,最隐秘的恐惧,这是我现在仍然面临的恐惧:我会失去对大脑的控制,我会疯了。
“我想让你住院。”
我凝视着窗外爱丁堡医学院18世纪的建筑,我在这里度过了过去五年里的许多光阴。那时候我才知道,我不想成为精神病科的一位病人,那感觉就好像待在一个极其安全却众目睽睽之下的金鱼缸里——在我所有同学的注视下,在我最近刚实习过的地方的楼上。我们同年级的几个同学已经成了那儿的病人。
“我想通过这些考试。”我说。“我现在不能住院。”
他草草地在我的病历上写着,我立刻感觉到他的恼怒,我不是一个听话的病人。我知道即使我感觉不正常,我也必须装着。
“服用这些药。”他说,然后递给我一张处方,再引导我到门口。
“我要再来见你吗?”
“不,没有必要看我,但你应该去看P医生。”
“我怎么了?”
“你很不快乐,很苦恼,但你没有和你弟弟同样的问题,我认为你的病情会转好。”
回想起来,我想我可能更受益于服用了抗抑郁药而不是安定药,但安定药是当时唯一出售的药。与现在的情况不同,我那时无法获得特殊的心理治疗,除非我准备入院接受集体治疗。我尝试了学生心理咨询服务,但觉得不是特别有帮助,不过是有人听你倾诉,然后重复你说的最后几句话罢了,令人感到既奇怪又沮丧。我现在确实认为,当很清楚病灶是什么并且双方共同致力于同一件事情时,咨询是适宜的,但是在当时,我无法说清楚我的恐惧以及我的问题是什么。我只是想得到不断的保证,但除了被告知考试会及格之外,我又不能确定别的保证。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感到焦虑并且很严重,然后这种焦虑感变成了别的感觉。我几乎肯定已经陷入一种抑郁的心态,在一个人不停地感到焦虑,并且确实觉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抑郁症可能会发作。然而,我的身上充满不畏艰难的精神,往深渊的边上看过之后就折了回来——我仍然能够做出选择。我在P医生的支持下设法通过了期末考试。
几个月后,我在内科病房开始了做住院医生后的第一份初级医生工作,午饭的时候,我撞见了戴夫——我在精神科实习时认识的精神科专科医生。他在走廊那边的自残科工作。
“杰西怎么样了,得厌食症的那位女孩?”我问他。
“她的体重增加了一些,出院回家了,她已经开始心理治疗。但是她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因为她还没有真正承认她的病情有多么糟糕。”
“那桑德拉呢?”
当我结束实习时,桑德拉已经离开了病房,我没找到机会和她说再见。
“她真的很好。我只是有点担心,她可能太好了。我上次在诊所看到她,她的情绪似乎在高涨,但她坚持说她很好。”
像许多躁郁症患者一样,桑德拉很喜欢情绪升高或轻度躁狂时(狂躁的较轻程度)的阶段,因为她做事可以更有成效,精力更旺盛和需要更少的睡眠。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是一位这方面的专家,同时也患有躁郁症,描述了当她情绪高涨时,她是如何高效地写了那么多的论文的。然而,她还描述了当她陷入精神错乱的漩涡并且与现实失去了联系时,她在写作过程中所经历到的非常偏执的恐惧,既忍受了可怕的妄想又遭受了令人恐惧的幻觉。当严重的焦虑转成抑郁症并引起焦虑不安时,治疗起来难度更大。在躁郁症的情况下,焦虑也会增加自杀的风险。
“她在服用锂吗?”我问。锂能稳定情绪,但具有一些令人不愉快的副作用。
“不,她停止服用了。她说这药让她感觉不真实,感觉不到真正的自我。”
后来我明白了桑德拉的真正意思。当我服用这药时,我觉得好像我的个性被压制住了。我觉得乏味、扫兴,但至少我没有感到抑郁。
戴夫的目光从他的炸鱼薯条盘子抬头瞟了一眼我,说“你看起来筋疲力尽。”
为了给她进行一些静脉输液,我曾花大半个晚上试图给一个严重脱水的十几岁的女孩的脚部插管,她患有糖尿病酮酸症——一种由高血糖引起的危及生命的症状。我的指导老师认为她的荷尔蒙导致她缺乏控制她的血糖的能力,但我对此没有把握。我开始告诉戴夫有关她的病情。“她喜欢呆在病房里,她和父母相处不好。我只是认为可能是心理因素使她失控。我的意思是说,她服用胰岛素的方法正确吗?”戴夫看着我,笑了。我很尴尬,以为我说错了什么。
“你瞧,你真的应该学精神病学。”
我鼓起勇气给P医生打电话。我想知道他对我的诊断的看法——他是否认为我能应付它的压力,我是否是一个尝试去做这件事的合适人选。
“你还好吗?”他问。
“我很好,上班了,真的好多了。”我停了一会,“我想谢谢你,”我说,“我还想问你是否认为在我今年发生了这一切之后,我不可能接受精神科医生培训?”电话那头几乎察觉不到地停顿了一下。“不,”他说,“我认为这不是完全不可能。”
我对这种可能性感到很兴奋,但我意识到,焦虑以及我对这样的决定会对我的余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感到的真正的恐惧削弱了我的兴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