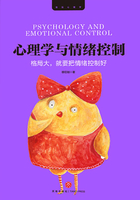1
看见李玉花耷拉的眼皮,懒散的神态,周玉燕明白星期天又到了。
这么三个徒弟,叶云琴离家远,一般不容易回去;周小芬是本地周家湾人,与周玉燕同村,离得太近,平日也懒得回去。李玉花家距玉田有二三十里的山路,说远不远,说近又不近,因此必须每个星期请好假,正正经经回去一次,拿米,拿菜,到父母家人面前撒撒娇。听说李玉花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大约自幼宠坏了的。
一般情况李玉花星期六下午动身回家,星期一清早再骑车赶到玉田上班,这些周玉燕基本默认了的。可李玉花思家心切,得寸进尺,往往星期六上午,甚至吃过星期五的中午饭,她那神情便开始不对劲,眼皮耷拉下,目光涣散,一对本已嫌大嫌重的屁股磨盘那般牢固地搁着,因而更见其重,也更见其大了。此时任你问什么,她都是一个懒洋洋爱理不理,手下还常常出错,让人哭笑不得。有次她将一件衣服的领子连到袖口上去了,另一次她给人垫了衣袋布却忘记收钱,做了一个结实的赔本生意,弄得周玉燕大光其火。以后每到周五周六,周玉燕说话派活会格外小心,发现势头不对,即刻将她从机子上撤下,让到一边打打下手,做做杂事之类。
近几天铺里忙,为后村一户做喜事的人家准备衣物嫁妆。那人家好脸面,派头摆得大,要求高,时间又限得紧,原说要到县城定做的,周玉燕托亲戚找熟人,好说歹说,算把生意揽下了。周玉燕提前同徒弟们打过招呼,说这个星期不比寻常,谁也别提请假回家的事,要回家等交了货以后回。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好钢用在刀口上,大家齐心协力加把劲。周玉燕强调道,我已把丑话说在这里了,到时别惹我发急。
都知道周玉燕的话针对谁的,李玉花也知道针对谁的,铺子里一时沉寂下来。姑娘们躬身伏案,手脚并用,埋头工作,似乎真的很忙了,几对眼神都如纷乱的蝴蝶在机头机尾,在飞舞的衣料皮尺之间递来渡去。
傍晚,周玉燕让李玉花到厨房准备晚饭。周玉燕问:“玉花,晚上我们吃点什么?”
李玉花说:“不晓得。”
周玉燕说:“前两天买的那菜,还剩得有吗?”
李玉花说:“不晓得。”
“你这张嘴巴怎么了,是不是让舌头塞住啦?”周玉燕好气又好笑,有心拿她逗着玩。“讲话连声音也出不来了。”
李玉花不吱声,歇了机子从工作台那边绕过来。两人擦肩而过时,周玉燕伸手拈去她肩头的一根白线,顺带着到那板结的脸腮上轻轻拍一下。李玉花一点也不准备接受她的友好与善意,脑袋一偏,不动声色闪开了,径自到厨房去。周玉燕心下不快,倒好似你在拍一个谁的马屁,结果拍在马蹄上一样。
几个人围着灶台吃过饭,把碗筷一推,匆匆到前间接着忙。李玉花跟着把饭碗一推,也到前间来忙,捡捡布料,拉拉抽屉,煞有介事着。周玉燕几次用眼睛暗示,她都装作一无所见。周玉燕忍不住,说:
“玉花,那边散了一灶台脏碗,你说该谁去洗?”
李玉花说:“我不晓得该谁洗。”
“今天这事真正新鲜了,自己吃过的碗不晓得该谁洗,是不是该我给你洗?”周玉燕道。“你要回家,你吵着回家,行啊,回去把你妈叫来,把你爸叫来,让他们说清楚这碗该谁洗!”
李玉花说:“又不是我一个人吃的碗。我包了煮饭,包了做菜,又让我包洗碗,我是从哪里请来的丫环哪。”
周玉燕说:“你是什么丫环,谁吃了豹子胆敢让你做丫环。人家想叫你做太太还来不及呢!”
叶云琴、周小芬扑哧一笑。李玉花见周玉燕真有些急眼,心下不安,也跟着咧嘴笑了笑,磨磨蹭蹭到厨房洗碗。
2
杨大力到达玉田时,已是夜晚七八点钟,河谷里黑得很实在了。镇那头远远的山脊上,有绒线那般细长的一点红红山火在蔓延,忽明忽暗,忽高忽低,只有形而无声,不像真实的东西。杨大力在玉田生活多年,每到这样的季节,山梁上那火便在镇后高处出现,惹人眼目。火一烧几日十几日,不见大,也不见小,不知几时燃起,也不知几时熄灭。白天踪影全无,夜晚到了,才发现火仍在那里烧呢,且烧得异样明,异样亮。就在人们停步观看时,火又忽然暗下去。杨大力至今没弄清那火是人们开荒垦山所放,或无意间失手引燃,或干脆是什么天火。街上居民们个个安之若素,没人惊讶,更没人上前过问。
镇头有几个人聚在暗处聊天,嗓门大,语意却不甚清晰。杨大力侧耳倾听,声音较熟,发出声音的人也应该很熟的。脚底下加足劲,从人堆旁一晃而过。偏偏车轮辗压之处凹凸不平,车身发出剧烈的哐哐啷啷,吓得那堆人呆立作一处,自己也几乎从车上给颠落。
“窜死吧你!”
身后传来响亮的叱骂。杨大力懂了,人堆里并没谁认出他。
玉田镇用的是山里小水电,水压不足,晚饭前后用电量大,电灯的光如阴雨天墙角的霉菌,一律黯淡而短促。人们迎着或背着这样的微弱光线在镇街上踽踽而行,已经不像了有血有肉有重量的人,而成了人的影子,一举手一投足都似是而非,若有若无。樟树边那家商店干脆不对头顶的灯泡存了指望,另点起两支蜡炬。有一些发亮的东西,如装食品的瓶瓶罐罐,如包装盒上的塑料亮纸,刺戳着路人的眼目。杨大力因此模模糊糊忆起了某一件事,准确说,那应该是一个梦,前不久做的。梦中的杨大力与今天一模一样,也骑车从县城赶来,也天黑了,也在樟树下这家小店门前,他看到他的女儿杨斯了。
“天黑成这样,一个人怎么还不回家?”杨大力记得他踉踉跄跄跳下车,大惊失色地问。樟树下的小店与周玉燕的缝纫铺处于镇子的两头,中间的街道几经曲折,人来人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夜里跑这么远,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得了?
杨斯手抓一件黑乎乎的物件,站在柜台前有滋有味玩着,抬头认出店外是谁,跑过来亲热地叫一声爸,让杨大力牵她回家。杨大力担心里加进了更多的怜爱,问女儿一个人摸黑跑这么远,回去不怕吗?
“妈妈不过来接我,怕又能有什么办法?”
女儿像个小大人那般,极力模仿着父亲的口音,把话说得老气横秋,饱经沧桑。玉田离县城不远,口音上却存在明显区别,那些年杨大力作为镇上的居民,话头句尾一直带有略显怪异的县城腔调。没承想这腔这调什么时候已让女儿学会,并且跑到他的梦中说出。梦中的女儿将父亲的话语模仿得生动而滑稽,让人心疼至极。
女儿倒腾着两条短腿,尽量跟上杨大力的步伐,结果一不小心,一家伙踢在路面的石块上。女儿哎哟一声要把伤脚提起,仓皇间目标弄反了,提起的是没受伤的脚。女儿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却硬不知道应该先把手中的脚放下,才能提起那只伤脚。她哀哀地一个劲让伤脚在地面去痛,而抱了没伤的脚在怀中兀自不放。女儿滑稽而娇憨的模样逗得杨大力大笑不止,于是从梦中一笑而醒。
缝纫机的声音嘀嘀嗒嗒传出老远,周玉燕同她的徒弟们以某种固定的姿态忙碌着,见到杨大力眼皮也来不及多抬,简简单单招呼过了,偏过身子让他进去。徒弟们在发出哧哧暗笑。徒弟们清一色的小姑娘,或坐或站大约有六七个,脸面都在熟悉与不熟悉之间。杨大力明白了这些并非真正的徒弟,多半是街头巷尾人家的姑娘大嫂,趁夜晚到铺中串串门,赶赶热闹。周玉燕口中衔一段白线,肩头又挂了一段白线,一块咖啡色布料在宽阔的台面上给拖过来撂过去,皮尺、角尺、剪刀随着她手臂的晃动四处翻飞。杨大力忽然有些紧张,站在那里不知进好或者退好。
“从县城来这一路上,你看到什么热闹没有?”叶云琴笑着问。
杨大力有些吃惊,问:“看到什么热闹?”
“天黑成这般,他能看到什么,”周玉燕道。
杨大力问周玉燕:“她说我看到什么?”
“没什么,”周玉燕脸色淡淡的。“上午到县城的一辆中巴车翻了,他们说伤了不少人,你没听说这事?”
“哪里的中巴车翻了?在什么地方翻了?”
周玉燕问:“晚饭吃过了吗?”
杨大力说:“吃过了。我吃了晚饭动身的。”
周玉燕忽然把双眉皱起,声音也不由提高许多:“碗柜里还有剩饭剩菜,你自己端到锅里热热,不需要别人帮忙吧!”
杨大力讪讪答应着,转身到厨房找吃的,心下甚是懊恼。夫妻之间这是什么人之间,的确没必要过于拘谨的,吃了就吃了,没吃就说一声没吃。他知道周玉燕讨厌这点,他自己其实也讨厌这点。
跑过几十里山路,还真叫饿了,几碗冷饭连同锅巴锅屑填下,仍有些意犹未尽的。他重新收拾好碗筷,舀了热水洗脚洗脸,然后给周玉燕打过一个招呼,独自来到房中。
女儿不在,墙角扔了一只小得可笑的球鞋,杨大力捡在手里,仿佛看见女儿又圆又嫩的小腿小脚了。他四下搜寻,想找到配对的另一只鞋。铺里过于忙乱,周玉燕像个大男人一样不知收捡,女儿也托在周家湾她外婆处照管。杨大力打开电视,有一眼没一眼看着。由于电压不足,画面一会清晰一会模糊。透过屏幕盲目地轰响,他有时能听到外房机器的嘀嘀嗒嗒,及姑娘们有一阵没一阵的嘁嘁窃笑。他紧张地侧耳倾听,笑声霎时又隐没了去。
毋庸置疑,周玉燕的生意越来越兴旺,人也越加成熟了。周玉燕为人泼辣能干,手艺好,人头又熟,在玉田镇总算打开了局面。杨大力欣慰过,顿感肩头的压力卸去许多。不可思议的是重压卸去的同时,他却感受到另外一种更大也更沉重的压力。眼前所有的忙乱与兴旺都是周玉燕的,不是他的。他的位置不在这里,他的位置在县城,在城角那狗窝一般的修车铺。尽管结婚多年,他和他的妻子周玉燕仍是不很相干的两个人。他不止一次让自己真诚地为妻子高兴,向妻子表示祝贺,说我们的处境确乎有了很大改观,照此发展,我们的前景应该不会差到哪去的。但是杨大力清楚,他反复强调的所谓“我们”是假的,他的高兴,他的笑容与乐观同样很虚假,很虚伪,话说到后来,连自己也无法压抑内心的酸楚。于是他省却了多余的话不说。
周玉燕一点也不掩饰读懂了他的目光,读懂了他的未尽之言。周玉燕没有吃惊,依旧埋头忙自己的,似乎在说这种男人,犯不着多作计较,犯不着同他七歪八缠。她忙,好忙,没精力没空闲的。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杨大力记起一句古话。所谓夫妻,其实真的没什么意思。感情有多么脆弱,感情能算什么东西。坐在电视机前的杨大力,脑袋里塞满这样一些阴暗而颓败的声响。杨大力是阴毒的,且从这阴毒中感受到奇特的畅心快意。
3
十来年前,玉田镇头的大樟树下有一家缝纫店,店里有一位小头小脸小身子的微型美人,沉着脸坐在当门边,将一部机器踩得呜呜直响。镇里镇外一伙半大小子,无业青年,苍蝇闻到屎臭那般聚在小美人身边,你叠着我,我倚着你,挤挤挨挨,说说笑笑。你娘个东西!狗,蛆,滚你的!小美人用各种脏话骂他们,赶狗一般赶他们。青年人不生气,照样嬉皮笑脸,挤挤挨挨,店中一应事务,劈柴,担水,洗碗,乃至送衣取料,买油买盐,整个让他们包揽了。
这个时候杨大力在玉田乡政府上班,后来又到红极一时的柴油机厂当操作工,当质检员,上班下班从樟树下经过,缝纫店里的一切对于他,只能算得远处的一道风景,或什么戏台上串演出的热闹。杨大力与周玉燕的交往要推到几年之后,即周玉燕让远方的一位小军官抛弃之后。杨大力很有些犹豫,此刻的微型美人可以称得上一朵几近凋败的昨日黄花。杨大力一遍又一遍这么问自己:别人不要的我就要吗?杨大力的家人得知风声,也表现出从不具有的坚决态度和统一意志,他们不能让自己的独生儿子找一个农村户口老婆。儿子的老婆吃农业粮,儿子的儿子永远成为吃农业粮的人了。
那些年杨大力性格乖戾,喜怒无常,他始终愤愤不平于两大具体问题:一,农村户口;二,别人不要的我要吗?与此相对应,有了微型美人那边的察言观色,百依百顺。婚前的微型美人很快两次怀孕,两次流产,这份伤害实在达到小头小脸小身子所能承受的极限了。微型美人几乎变成了一个纸人,消瘦而苍白。这时的杨大力等于冲毁了闸门的大水,一路激荡澎湃,遏制是全无可能的。眼睛血红的青年摸索着,试探着,同时颤抖着。他问:“怎么办?”
周玉燕说:“还不随便你?”
周玉燕摆出一副不管不顾的架势。
从某方面来说,杨大力当真有些亏。他过于亏待了自己。他从身上,从口里抠出一分一厘的钱聚敛着。他有他独到的快乐:他的钱是留给妻子和女儿的。每次骑车到玉田,将一张一张钱票数过去递给周玉燕,周玉燕同样一张一张接在手上,他的眼睛,他的脸膛,同妻子的眼睛和脸膛一样,散发出明亮的光。他整个变做另一个人,逛市场,逛商店,买衣,买鞋,买鱼买肉。他为她们大手大脚。周玉燕受到感染,大概以为这钱来得容易吧,跟在他后面同样大手大脚起来。这正是他需要看到的。他只愿看到她们的欢笑,她们的轻松,看她们大手大脚,让她们以为他的钱来得容易。不平的地方便在这里,他的自苦是他所愿,他不怪谁,也不能怪谁。但周玉燕作为一个妻子,多少也应该觉察到丈夫背后的那种苦,那种抠。就算一种直感吧,夫妻之间,这种知痛知痒,知冷知热,照理应该存在。
“你数数。”杨大力说。杨大力递钱过去时,习惯这么说。
后来周玉燕兴旺了,忙乱了,再没心思数那几张可怜的钱票了,随随便便接过,往旁边一放。杨大力一颗心悬起,他想提醒一句,这都是钱,尽管少,但挣来的确不容易,你应不应该收起来藏好?铺里人多,人乱,不要弄丢了。
杨大力说,现在到了赶紧刹车的时候了。他不能如此傻下去,这种女人是不知感激的。一个人当真傻透了。杨大力说,恩断情绝,恩断情绝。杨大力心情激动,躺在床上不停地翻来覆去。
夜已经很深,山风在很远的谷口那边低低耸动。铺里的机器一如既往嘀嘀嗒嗒,然后停住,然后又嘀嘀嗒嗒,针头带着白线黑线在布面上快速走动,进,退,拐弯,嘀嗒,停住。又长又直的巨型剪刀贴紧木台切割布料,发出咯咯咯咯让人迷醉的清脆声响。有一会工夫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四周寂静得吓人,外间的灯光猛然明亮,成矩形地投射到睡房地面,发出碎玻璃一样的哧啦哧啦的声音。杨大力疑惑着,姑娘们的工作已停,各自回家安歇了?那么周玉燕又去了哪里?
噗——
有人含了满满一口水喷开,其声其响撼人心魄。然后又是叽叽咕咕的说和笑,机声嘀嗒,硕大的剪刀咯咯咯震动布台,针头牵引着白线黑线进退,拐弯,走动不止。原来外间仍拥挤着一大屋子人。
有一个事实再清楚不过了:杨大力正专心等待周玉燕早点进房睡觉。在过去的日子里,杨大力经常这样早早上床,用体温一点点把被子焐热,然后侧身以等,等周玉燕躺下,他拥了被子整个盖上去,软软地,又是牢牢地扑住,将两个人做成了一个人。周玉燕大约患有轻微的肩周炎,双膀不能见风,见了风会咳嗽的。可周玉燕偏像一个不懂事的顽劣孩童,睡梦中不是伸胳膊便是踢腿,总有这里那里露到被外去。于是杨大力夜夜要无数次醒来,清晰地或模糊地醒,在醒与非醒中忙着替妻子遮肩,拉被头。杨大力的夜晚是给糟践得一塌糊涂的夜晚。
后来有了孩子,杨大力回了县城,所有的亲热一变而为遥不可及的往日回忆。类似今夜的感觉,今夜的等待,对杨大力来说委实过于陌生,也过于新奇了。这是怎样一个夜晚,女儿去了两三里路外的外婆家,剩下的是纯纯粹粹的两个人,和两个人所面对的纯纯粹粹的夜晚。属于这个季节的野火犹如半空中掠过的雁行,在镇外的山梁上蔓延,忽明忽暗,似是而非。水流随风声在山间漂浮,流淌,脚下的大地倏忽隐遁而去。杨大力清晰地感受到与身子同在床铺上翻腾的别一种企图。
4
几个徒弟陆续离店,回了她们的租房。周玉燕卸下布台,将桌椅板凳一一归拢,桶里的残水轻轻泼开,然后开始打扫卫生。杨大力听到搬弄自行车的声音,不由从床上爬起,出外帮忙。
周玉燕说:“这搬都搬好了的。”
杨大力挪开墙角的门板,按序号一块块榫上去。周玉燕见他穿得单薄,催促着他赶紧回房。杨大力说:“今夜是不是太晚了?”
“天天这样,有什么晚不晚的。”周玉燕掩住嘴巴,憋好久,打出一个长长的呵欠。
周玉燕问:“还没有睡着?”
“睡着了的,刚醒。”
周玉燕洗漱后仍不急于上床,这里翻翻,那里看看,又从梳妆台抽屉取出一沓纸单,摸出圆珠笔写写画画起来。杨大力虚眯了一只眼睛,从被隙间往前探看。又故意弄出些响动,让人觉察他的等待。
杨大力道:“还不打算睡吗,明天又说要早起的。”
“我理理近几天的账,免得到时又忘了,”周玉燕的声音笼罩在台灯的光圈里,有些模糊不清。
周玉燕不会打算盘,日常需要划拉个什么,加减乘除的,算式摆了一道又一道,草纸涂过一张又一张,同时口中念念有词,把笔下的人名、数目及具体的运算过程反反复复读出,不熟悉的人会以为她在同谁讲话,争辩。她说不这么念着,脑子里空空洞洞,一般的东西还真不容易记进去。念叨停了,手中的笔也不由停下,头微微歪斜,双唇紧紧抿住,一心思考着什么呢。
杨大力说:“明天一早我到周家湾接杨斯。”
周玉燕嗯了声,仍歪了头用劲思想,毛发映着灯光闪闪发亮。杨大力猜测这是笔什么账目,莫非就没有个算完的时候?她明知旁边有一个人正一心在等着。杨大力忽然意识到,今天晚上他是否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忽略了问题的关键:周玉燕所谓的忙碌纯属装腔作势,面前这个女人实际上一直在敷衍他,回避他。她在千方百计拖延时间。
恩断情绝,杨大力说。有什么意思,恩断情绝。
床板咯咯直响,杨大力重重地翻身向里。可周玉燕半点也没觉察他的翻身,没觉察他满脸的意气。杨大力咯咯地重把身子翻回来了。
“今夜你真不打算睡觉吗?”
周玉燕说:“叫你先睡你就先睡么,有什么等的?没看到这边忙?”
杨大力说:“你那灯光刺人家眼睛!”
周玉燕给台灯调了个方向,又将灯罩按低,光圈集中到桌面,却始终没转身看看床上的人,没听出这人话语里的东西。也许听是早已听出了,正因此她才懒得搭理的。
周玉燕给身后一阵巨大的响动吓住了,她吃惊着回头,见杨大力一身内衣内裤,手脚斜撑住床沿,另一只手缓缓地按揉弯曲而绵软的右腿,面呈痛苦之色。
“好好一个人,睡着睡着这是怎么了?”周玉燕终于离开桌椅走上前,“从床上摔下来了?”
杨大力歪着身子,从床里找过毛衣,两臂比画着伸进袖筒,扯顺,由头顶向下一套。他开始穿衣服。
周玉燕问:“穿衣做什么?”
杨大力说:“我走,回去。”
“你要回哪?”
“我回县里,回县城。”
周玉燕愣怔着,没弄清他的话意。
“不是刚过来吗,怎么又急着回去?”
她问他回县城有什么急事。
杨大力说:“没什么急事,就是要回去。”
周玉燕说:“没看几点钟了,大半夜快过去了,这还回哪里?”
杨大力不做理会,继续一件件穿衣,动作沉着,平静,目光坚定,不容置疑。
“你是在这里找我发神经吧,要走可以,先把话说清楚!”周玉燕一张脸涨得通红。“你说你什么意思,来也是你要来,回去也是你要回去,吃饱了饭没事跑来拿别人开心开胃是吧?以为我们这班人活得好自在是吧?狗日的什么东西!”
周玉燕连骂带喊,一句快似一句,同时涕泪交流了。
“你回去就回去,我不留你,我留不住你。你回你那个好家,回你的县城去。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你快走,快滚,别慢吞吞让我心烦……真是一头猪,猪一样的东西!”
杨大力双唇嚅动,满眼怒气,差不多也要喊叫着回敬过去。他没想到周玉燕会骂人,没想到周玉燕会如此歇斯底里,伤心欲绝。他知道,所有的伤心都因他而起。周玉燕真情流露了。杨大力惊讶地看着面前这张脸。这是怎样一张脸,在眼角、额角、嘴角,在鼻翼,在纵横流淌的泪水后面,散布一条又一条微小却密集的皱纹。这的确不是当年孩童一般依附着自己、小头小脸小身子的微型美人了,由于劳累,由于生活的重负,周玉燕成熟了,同时也憔悴着,老了。
周玉燕双脚比齐了立在床前,脑袋深埋进被子里,长时间低声饮泣。杨大力不加解劝,也不知如何解劝。他小心挨坐到一旁,轻轻抚弄她的双肩和头发。
“睡,睡啊,”杨大力问。
早先的日子,结婚前结婚后的日子,周玉燕有事没事,也喜欢像现在这样比齐了双脚立在床前,将脑袋深埋进被子深处哭泣。每逢此刻,杨大力并不解劝,只轻手轻脚上前,悄悄拽住她的裤腰或裙腰连着内衣用力朝下一拽,一对光溜溜的屁股瞬间滑稽地翘在高处。周玉燕大叫一声惶急着捞衣,捞了半天没捞住,无可奈何站在那里,扑哧扑哧笑得眼泪簌簌直掉。
那样的日子,眨眨眼已过去多久了呢?
杨大力将妻子凌乱的头发一根一根、一绺一绺捡拢,轻轻搁在肩背上,抚摸一阵,又从颈项那边放下去。
“把衣服脱了,睡,啊?”
上次来玉田,杨大力与女儿杨斯也闹过一次别扭。三个月前杨斯刚满四周岁,杨大力实在糊涂了,他到底搭错了哪根神经,和自己这么小的孩子闹气。可他恰恰闹了,且闹得认真,闹得投入。杨大力不能容忍,什么屁事不懂的一个小孩似乎也能狗眼看人,无论言语动作、表情神态上,对他这做父亲的总有些无所谓,有些小视,有些看不起。杨斯心里只有一个妈妈。妈妈长,妈妈短,妈妈让她干什么,妈妈不许她干什么。杨斯哭了,杨大力好话说尽哄不转,她妈妈一句话,一个断喝,立时能让她静寂无声,乖得像条狗一样。杨大力给她买了件新衣,一双鞋,一个玩具,她明明欢喜得紧,表面却装作不欢喜的模样,说:“妈妈会给我买的,买个好大好大的,好漂亮的!”有时杨大力陪她玩得入迷,周玉燕过来了,她即刻会抛下他,讨好地跑到母亲那边。周玉燕教女儿唱歌、认字,给女儿讲故事,两人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杨大力独自坐在一边看电视,表面不动声色,全神贯注,甚至对闹过了头的母女投去淡淡一笑,说上一句什么,但在内心深处,他感觉一切有多么无聊,没意思透了。
杨大力是容易得罪,容易伤心的。杨大力一边抚摸着周玉燕颤抖的肩,一边想。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到底?莫非整个世界都伤害了我,要与我过不去了?
第二天一早,杨大力到周家湾看了看女儿,随即匆匆赶回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