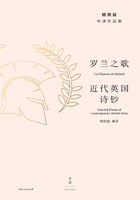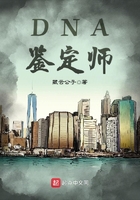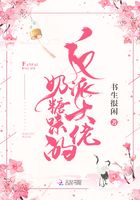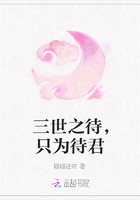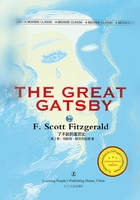以现今任意一颗不必太精英的头脑,来回顾中国于有清一朝的人口增长,或许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是一个缺乏远见的错误。后来众所周知的事实表明,那属实是一个错误,不过未必缘于时人的没有见识。实际上,举凡于历史中留下名字的民族或国家,在现代以前,或说在冷兵器时代,几乎都曾以人口的增长为幸事,在他们看来,繁盛的人口就是力量不竭的源泉。显然公正的说法似乎是:那是一个因时代的局限而导致的错误。
清代时期的中国,实在并不乏有识之士,他们对后期的人口增长及其带来的诸项弊端,都有较及时的认识,并策划出很多方法来试图解决这些迫在眉睫的难题,无论是否管用,心思都是尽到了。其中很有争议的一个人物,名叫汪士铎(1814—1889年),他是一位历史地理学家,不过好像终生都挺落魄,仙逝后也还被囚于历史冷宫至今不得烟儿抽,尽管也曾有并非不著名的学者,主张把“中国的马尔萨斯”之美冠,由洪亮吉那儿抢来转赠给他。
汪士铎的遗著《汪悔翁乙丙日记》,记载了很多他对人口及人地关系问题的洞见,虽然屡现偏颇之辞,却也不乏超前意识。比如他在控制人口增长的方案里,既号召采用溺婴的残酷手法,却也提倡了避孕药的介入以及晚婚晚育,甚至提出了独生子女和优生的主张;在人地关系问题上,尽管他不曾得出类如“递减规律”的科学结论,却也看到了“人浮于地者数倍”的现状,并指出了“人多则穷(地不足养)”的必然结局。特别有必要一提的是,对于人地失衡的后果,他动用了一个“乱”字——“世乱之由:人多”,相对于土地资源。
世乱的因由当然没有这样简单,起码社会制度是不该忽略的重大一项。不过,不管此论如何缺乏政治因素,它都确实道出了天下必乱的根本原因之一:人不足食。
“为政之要,首在足食”。当一届政府不能保证治下民众的饱腹,此政府就应当深感失责并为此认真自检;当一个政权的治下民众饥的饥饱的饱,且饱汉不知饿汉饥,这个政权就一准儿出了问题而有必要尽快修正,如果不想有麻烦的话。毕竟谁也不甘愿成为历史的牺牲品,哪怕他们只是一批饿汉——何况他们只是一批饿汉。
马尔萨斯在此问题上的观点,与汪士铎的大抵仿佛,亦是将社会的贫困和动乱之根源,过分局限地归咎于人口过剩。所以两者都期望事先将人口过剩的问题处理掉,以避免“世乱”之苦。不过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却又颇有戏剧性地均以战争——这“世乱”的重头表现之一为手段:汪士铎直截了当倡议启动战争机器来消灭过剩人口;马尔萨斯则含沙射影看好了战争机器天然可致人口锐减的特殊功能。
事态的发展似乎说明,两位学者的冥思苦想都有点儿多余之嫌。实际上根本不必劳烦人类煞费苦心地刻意经营,如果事情进展得不妙且愈加不妙,战争的机关自个儿就会在某一时辰自动开启,不可逆转地开启,跟人口的增长与粮价的上扬一样无法遏制。
土地的报酬递减规律,若说它是一条铁的定律,那么也就此向世人摆出了一个鲜明的态度:超负荷不是土地的常态。当并非常态的状况事实上得以发生,土地就会以报酬递减做出应急反应,也对土地的附属物——人类,做出明确警示;当这种警示被宣布无效,当土地的负荷依然超重且显然还愈来愈重,土地的报酬就会日益递减。或者可以把这种持续的递减现象,想象成土地的一连串抖搂动作,指望以此来减轻背上的超常负重,以期尽快得以恢复到常态之中。尽管无论土地如何抖搂,都无法把多余的人口卸下肩背抛出地球,却是能够不期然地导致世间的饥饿:人不足食。
在清朝时期的中国社会,当人不足食成为一种客观必然,由于社会制度的局限,也就并不意味着那将会是普天下所有人的半饥不饱,而只能演化成这样一个事实:以大部分人的不得食为代价,来保障少数人的终日饱食。这显然又糅进了浓厚的政治因素,却也是毫无回避的办法,也因此才说前头的两位学者跟时代一样有点儿局限了。
当饥饿袭击了社会的大多数人,这些饥饿着的大多数人,有没有可能在绝望中撑起饥饿的身体,操起手头能够抓得到的一应家伙,去抢夺那些少数人的碗中之食?谁能否认,生命之要不也是首在足食?有谁肯乖乖等着饥饿来收拾掉自己嶙峋的身体?
战争于是发生。
这种战争显然并非人为的制造,而且是不可阻挡的爆发,火山一样。若非具备了条件,世人如何怂恿都难说有效;若已具备了条件,世人如何阻止也注定无效。
无论之前业已暗中酝酿了多久,世道是自倒霉的嘉庆帝那儿开始乱起来的,打头阵的是白莲教。白莲教起义发生于嘉庆元年(1796年),辗转于四川、河南和湖北等5省,历时9年半,最终失败于清廷动用的16个省的兵力之下。这是康雍乾盛世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乱,也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最后一个繁华盛世就此成为明日黄花。
白莲教起义发起之后,途经各地之际,沿路农民“自焚其屋随去者”颇多,以致“自用兵以来,所杀无虑千万,而贼不见少”。起义军也还暗中得到了群众大力支持,使其“行不必裹粮,住不借棚帐”,几乎处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致使剿杀4年过后,也仍然是“辗转蔓延……遂不可遏”,也使太上皇乾隆最终没能怀揣盛世概念完美地离去,临合眼之际,还“亲执朕(嘉庆)手,频望西南,似有遗憾”。
“官逼民反”是白莲教动用的起义口号,似乎也曾翼求“日月复来”,含有一定量的反清复明意识。倒也不必指望每一个焚屋随去的农民,都怀有此类明确的政治理想,如果猜测只要从此有了可以吃上饱饭的前景,就已经很可以让他们拎起锄头去上阵,想来也不算为过。天理教在起义前招募教徒时,所做宣传是“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举凡习教之人“穿衣吃饭,不分尔我”,也果真有若干之多的农民随之而去,好像每一句都字字温暖了农民与小生产者的心,鼓动起他们为生存而反抗的想望,并坚定了他们这样做的意志。类似的宣传语言,白莲教也应当觉得有必要一再重申,毕竟发难于政府,实非安贫乐道的中国农民之常态,若非生存实在太过于尴尬而所绘前景又实在太过于诱人,想来他们不会生出惹麻烦添乱子的心思,即或曾暗自嘀咕过,也很难如此决然地付诸于实际。
无论如何,社会从此不再消停。
倘若细枝末节地深究,社会早在乾隆朝就已不大消停了。早在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寿张就率先鼓爆了一座火山,牵头者为农民王伦。这次暴动为期不足一个月,牵扯范围十分有限,却被一位公认为颇有见地的学者于回顾历史时指出:这次起义拉开了清代中叶以后各族人民大规模反抗清朝统治斗争的序幕。那么想来此次战争的意义,并不在于对清政权的实际摇撼程度,而在于它抢先撕开了这个世道的面纱,使其袒露了“外似升平,内实蛊坏”的实质。
接下来,也还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苏四十三于甘肃领导的撒拉族人民起义;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林爽文于台湾领导的汉族与高山族农民起义;乾隆六十年(1781年),吴八月与石柳邓等发动的波及到湖南、贵州和四川三省的苗民起义,持续有12年之久,至嘉庆十一年方被彻底镇压。这些起义除末一次外,其他持续时间亦均有限,相对于嘉庆年间的大乱而言,属实还算不上喧哗。
自白莲教起义之后,此类骚乱则愈加不能停止。嘉庆十八年(1813年),直隶、山东和河南的天理教起义,径直跑去扰乱了紫禁城,惊动了未来的皇帝道光;嘉庆十八年至十九年(1813—1814年),陕西岐山木工起义;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新疆回民起义;道光二年(1822年),河南新蔡起义;道光十一年至十二年(1831—1832年),湘西瑶民起义;道光十三年(1833年),四川彝民起义;道光十五年(1835年),山西赵城曹顺起义;道光十六年(1836年),湖南武冈瑶民起义;道光十七年(1837年),四川凉山彝民起义;道光十八年(1838年),贵州谢法真起义,等等。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当片片枯叶都纷纷零落,应该就是深秋已至了。这些相对小打小闹的折腾,最终催生了咸丰元年至同治三年(1851—1864年)期间的太平天国起义。
从这一点来说,咸丰帝看似比嘉庆还要点儿背些。此君1851年继位,1861年去世,在位11年,伴其始终的是洪秀全。洪秀全的不请自来与久驻不去,令“咸丰”二字的“普遍富足”之意,在其统治期间完全改变了内涵,尽塞动乱与饥寒。“三藩之乱”不过8年,白莲教起事也只有9年半,太平天国的烽烟却持续了整整14年。14年的战火,燃遍了中原14个省的城乡,势态之严重已迫使清廷破天荒起用了汉人曾国藩之勇营,其间所费周章与所耗心血也就可想而知。至1864年太平军终于匍匐倒地之际,战后的中原大地已是放眼之处“无不毁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破之富家,无不欺之穷民”。太平天国起义堪称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就双方杀戮的残酷性和对社会的破坏性而言,史上少有匹敌。
世界狼藉一片。
也还有对此状况加以补充的。掀起于咸丰三年(1853年)的捻军之乱,持续15年之久,在淮河流域诸省、直隶南部和山东西部,引动了一场浩劫。除此,咸丰四年(1854年),广州地区还有红巾之乱;咸丰十年至同治元年(1860—1862年),山东还有八卦教之乱;同治元年至十二年(1862—1873年),陕西和甘肃还有回民起义,此番12年的大骚乱,给甘肃省大部分地区带来了灾难性创伤,清政府的不接受投降政策,一方面延长了骚乱时间和创伤深度,另一方面也将那些不得不拼死而搏的人,更多地置于死地。大致与此同期,也还有被太平军与捻军的榜样力量激发起来的若干股对清廷的局部暴动。如此接三连四交错而来的大小乱子,对天生就胸中无甚格局的咸丰与同治而言,每一次都是一个灾难性打击,使这爷俩儿双双早亡,抛下一片荒凉的土地,一群饥饿的子民。
不过“同治中兴”的概念,也还是留在了历史书页之中,理由是“一个统治了200多年并且一度鼎盛的王朝,在以后衰败时仍能扑灭一次席卷全国的和难以对付的叛乱”,这被人们视作“历史中的罕见现象”,以为能与此并论的唯有唐肃宗时期(756—762年)的“唐代中兴”。“任何中兴的主要事件都是军事性质的,即必须打败叛乱者”,或者安禄山,或者洪秀全,哪怕为此付出杀鸡取卵或釜底抽薪的代价。然而胜利的狂喜毕竟转瞬即逝,历史也同时证明,任何一个“中兴”的接下来岁月,都只是于残喘中日复一日地延续。
战争机器,如此频繁启动的战争机器,果然消灭了大量人口。据多位治学严肃的学者统计,单只是14年的太平天国战争,就至少“直接导致了7000万人口的死亡”。7000万人,该是多大的一群?沈阳市辖1市、9区和3县,人口不过750万左右;二战时被纳粹以现代技术批量残害的犹太人,为数也只有600万。另有一个“数百万”的含糊数字,是左宗棠对死于甘肃回民起义战乱中之人口的大致估算。余者,不得而知。
太平天国的起义口号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为着这样一个完美世界的梦想,梦想者离弃了眼前的世界。
中国于有清一朝的人口增长,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保持了直线上升的趋势,直到太平天国战乱平息六年后的同治九年(1870年),才呈现出一个回落的曲线,由咸丰元年(1851年)的4.3亿,降低为4亿。这里当然有理由将其多半归功于战争。自这之后,有学者称,此线条又转而攀升,在1900年达到了4.5亿;却也有学者持另一种看法,认为直到1913年,中国人口还仍未恢复到1851年时的数量。
如果1870年的人口统计数字大致准确,则可推测即使在太平天国战乱以后,中国人口也还处于增长之中,至少需要增长4000万,方能符合这个4亿之数。
这样的增长实已未必出于人们的主观意愿,而只是缘于人口增殖所固有的惰性。人口增殖所固有的惰性,使人口无论是增长还是下滑,都注定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当有一个硕大的基数撂那儿垫底,即使社会不再提供清明的政治环境,土地不再供给相应的果腹食粮,人们也未必就不曾丧失生育的热情,它仅仅依靠自己的惯性,也足以将增长势头在一定时期内继续保持下去。那宛如一个下坡路,无论如何紧急叫停,都不可能瞬时驻足;无论如何不想再涨,都不可能生成立竿见影的效果。较长的生产周期,决定了人口增殖的惰性特征,也注定人口调节是一个急不来的问题,更是一个需要前瞻性的问题。
之所以将导致人口回落的功劳(权当它算一功劳吧),只肯给战乱以大部分而非全部,在于其中还有灾荒与瘟疫的部分贡献(可不是贡献么?)战争、灾荒与瘟疫向来是一组好搭档,三者针对的都是人,目的也都是置人于绝境。事实是,战乱、灾荒与瘟疫,在清末的中国大地上交错发生,轮番上演,它们相互地鼓动与督促。
对于灾荒和瘟疫在减少人口压力上的作用,有人将其称之为“天地调剂之法”,此人就是洪亮吉(1746—1809年)。洪亮吉是乾隆年间的进士,一位著名的经史文学家,他在1793年发表了一部论著《意言》,在其中第六篇《治平》里,对人口发展进行了中国有史以来的首次集中论述,亦因之被后人誉为“中国的马尔萨斯”。
对于人口的失控增长,洪亮吉在《治平》篇的一段自问自答中,给出了两条解决之路,一是天地调剂之法,二是君相调剂之法。后者的力量在他看来是微弱的,其法则不过是令野无闲田,民无弛力,移民,减赋,禁浪费和赈灾。野无闲田已圆满成为事实;民无弛力则太过理想,越往后来,农村失业者越多;移民和减赋及赈灾,无论效果如何,也都像模像样地努力做了并还在做着;禁浪费却有点儿不可能,乾隆的奢侈、和珅的贪婪已成历史为数不多的定论之一,由俭入奢易,由奢再俭可是难。这是洪亮吉对政府和社会的期望,效果应该有限。那么前一条呢?在他看来也是不怎么理想的。他说:“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意思明显是,对于现今如此之多的人口,只靠水旱之灾与疾疫之祸所能减损的十分之一二,显然太不够解渴了。
然而,若灾荒的破坏力空前可观呢?
后来的数字表明,灾荒的效用并不怎么令人失望,甚或还算很理想地达成了世人的期望也说不定。在一个人地失衡的生态系统里,灾荒的到来很不难为人,或许还当说是必然的。资料显示,从顺治元年至道光十九年(1644—1839年),近200年间,中国境内自然灾害多达28938次,其中水灾16324次,旱灾9189次,其他灾害3425次;在频生事端的1794—1853年这60度春秋里,全国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488次,平均每年高达8次之多。不过这若干灾荒之中,还并不包含最具毁灭性的“丁戊奇荒”。
那是一场发生于光绪二年至五年(1876—1879年)的大旱之灾,光绪三年(1877年)、四年(1878年)为灾情高峰期,故名“丁戊奇荒”。灾荒主发区域是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和山西五省,其中以山西与河南灾情最重,遂也称“晋豫奇荒”以及“晋豫大饥”。在那光明过头的数年间,连绵的烈日令广袤的土地大部分颗粒绝收,往昔油绿绿的田园里唯有“白骨盈野”;即使部分地区得以侥幸栽插禾苗且还偶有存留,亦被接连而至的蝗灾吞噬一空。如此的旱蝗交迫之中,不计其数的活人转成饿殍,或载于逃亡途中,或蜷于路边沟渠。据传部分地区已发展至人食人地步,亦更有很多人虽一息犹存,却是已无“割人之力”,倒地后反被“饿犬残食”。当土地干渴已极,当庄稼纷纷枯死,世人也就只有连连枯亡。
这还是在瘟疫到场之前的死亡。
瘟疫是一种强烈的传染病,由一些微生物如细菌、病毒等引发,很多时候紧踩着战乱和灾荒的脚后跟而来,个别时候也不拘此俗礼就来。中国人与瘟疫的交道可谓恒久了,清朝时期的华夏大地之瘟疫又尤其盛行,仅《清史稿·异灾志》记录的就有149宗,这又是极不完全的。很多事实表明,彼时发生的灾荒与疫情很难上达到朝廷,交通的困阻和信息的闭塞是一因由,无人关注也是因由,往往历来多出进士之省府,其灾疫的传布就较为顺畅,救助也较为及时。遂即使是壮如“丁戊奇荒”的大灾,消息传到北京之际,也已是“光绪三年后半年”。令人绝望的是,在北京终于得知消息,官方与民间也都纷纷采取紧迫行动之际,“却发现大批粮食无法从沿海地区迅速运往内地”。
相对于前朝而言,清政府对灾疫的赈济措施还较有章法,不过在实施过程中仍会受到客观条件的过分限制,援助之手往往无法确实伸给灾民,若碰到一个主观不努力的实施者,也就更不容易。故而那个时代的每一次大小疫瘟,都堪称对百姓的一次赤裸裸打劫,瘟疫来过之后,“一巷百余家,无一家幸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的状况,普遍存在。
“丁戊奇荒”之际,瘟疫也例行前来捧场,于1878年的春夏之交迅疾扑向了大部分灾区,致使河南“十人九病”,陕西“道殣相望”,山西“百姓因疫而死者十之二三”,已被旱蝗之灾蹂躏了一遭的大片田野,此刻更被趟得“赤地千里,白日鬼唱”。据《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记载,此期间山东、山西、直隶、河南和陕西五省,遭灾州县达955个;受饥荒严重影响的百姓在1.6—2亿左右。
对由于饥饿、疾病或暴力等因素死于这场特大旱灾与瘟疫中的总人数,显然无法做出精确统计,时下被普遍认可的最保守的数字是1000万左右。
另有这样一个数字,据称已被数位人口史学家的研究大体验证:在1850—1877年间,由太平天国和甘肃回民起义的战乱以及“丁戊奇荒”,总共“导致中国损失了1.18亿人口”。倘若这个数字的可信度更高些,那么对死于太平天国战乱中的7000万、甘肃之乱中的“数百万”,以及“丁戊奇荒”中的1000万,就该存有怀疑,显然它们统统估算得过于俭省了。
洪亮吉不曾看见“丁戊奇荒”的惨景,亦不曾得知这个数字,否则,想来他会因数字的太过理想而心痛的。此人的字里行间含蕴了足够量的悲天悯人之情,看似是个厚道之士。
相对而言,洪亮吉并不曾指望通过战争机器来减损人口,但并不代表他不曾意识到战争的必然发生。在他看来,尽管天下间没有谁不愿当安定社会的平民,没有谁不愿当长期安定的社会之平民,然而当社会长治久安,就不能不增加人口,可是天地用来养活人的东西又实在有限;当社会安定的时间久了,政府也不能不叫百姓生孩子,可是政府能为百姓考虑的,也不过是那些效用有限的“君相调剂之法”。事实呢,一家之中不听教导的子弟常有一两个,天广地阔,失业的游手好闲者又如何能够全都遵从上面的约束?况且住房已经不够了,吃穿已经不足了,如何不让人忧虑呢?
其实按照现代的眼光来看,人多不一定非得导致人地失衡,人地失衡不一定非得导致战乱灾疫,战乱灾疫也不一定非得导致社会动荡,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框架内,这样的因果链条注定无法打断。被历史给局限了的政治体制、科学技术等,都无助于消解时人对此的忧虑,尽管这些先天下的忧虑也并无补于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