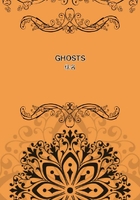南昌诸府。
诸养和盯着“小和尚”看了半天,扯掉他口中的布。
“小和尚”破口大骂道:“你们这帮浑蛋,光天化日之下胡乱抓人,我要告官!”
诸妻皱眉道:“老爷,是他吗?”
“小时候见过一回,看着挺像。”诸养和出门,找到管家,道:“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
管家信誓旦旦道:“错不了,我亲耳听见有人叫他‘王守仁’。”
诸养和点头道:“此事先不要让芸玉知道。”
“是。”
诸养和入内,走到“小和尚”近前,道:“守仁啊,你娘的病你不要有压力。舟车劳顿,先休息一下。”
“小和尚”气道:“我不是王守仁!”
诸养和迟疑道:“你是哪里人?”
“绍兴人。”
“这就对了嘛—”
“不对!”
下人进屋,禀告道:“老爷,外面有个自称‘王守仁’的求见。”
诸养和傻眼了,同妻子对视。待回过神来,问道:“你叫什么?”
“小和尚”没好气道:“钱德洪!”
夜里,诸养和设宴招待王阳明,举杯道:“闹了个大误会,守仁勿怪。”
王阳明与其碰杯,道:“舅舅见外了。”
管家入内禀报:“老爷,那个钱德洪走了。”
诸养和道:“银子给了?”
“死活不收。”
诸养和感叹道:“江浙多才俊,此言不谬啊!”
王阳明闷头吃菜……
夜深人静,诸府客房。
王畿端了盆水进来,供王阳明洗脸。
敲门声响起。
王阳明道:“哪位?”
诸养和道:“守仁啊,还没睡吧?后天便是婚礼了,舅舅想跟你碰一下当天的环节,看看哪些地方你不满意。”
“你们定就行,我没有异议。”
“那哪成?我在书房等你。”诸养和离去。
王阳明苦笑道:“你见过舅舅对外甥这么客气的吗?”
王畿想了想,道:“虽是表的,却也不多见。为什么呀?”
“因为权力—你过来。”
王畿走近,王阳明耳语。
半炷香后,书房响起了敲门声。
诸养和起身道:“请进。”
王畿推门而入,诸养和一愣。
王畿道:“婚礼的事小少爷说了算?”
“他想怎么操办?别的地方不敢说,在这江西的地界上,还没有我诸养和办不成的事。”
“好。小少爷说了,他想要的婚礼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诸养和呆住:“大漠?长河?这……”
王畿续道:“小少爷还说了,能做到他就结,不然……”
“不然怎么样?”
“打道回府。”
“啊?”
房门突然推开,诸芸玉出现在门口,凌厉道:“好大的口气!我诸芸玉是嫁不出去了吗?”
王畿被她的气场镇住。
诸芸玉道:“你回去告诉王守仁,五日之后见分晓。希望到时候他不要自食其言。”
王畿心虚道:“哦。”
次日,南昌城外的一个驿站,驿丞慵懒地靠着椅子,看驿卒们征收号草。一老翁缴纳的号草过完称后,驿卒开始报数。
“二十斤。”
老翁急道:“明明有六十斤的!大爷,烦劳再给过一次吧,可能称错啦!”
驿卒掌掴老翁,道:“混账,老糊涂了吧你!”
一披朱佩紫,贵气冲天的公子路过,看见老翁被打倒在地,白发飘萧,心下不忍,问身旁的随从道:“刘养正,这是……”
“回世子,驿站征收号草,就是给马食用的草料。”
刘养正口中的世子,乃宁王朱觐钧之子朱宸濠。
朱宸濠道:“哦?我听说朝廷拨有专款,由官府统一向民间采购号草,一文钱一斤。”
“世子明察。上面的钱根本到不了下面,这些百姓不但要无偿向驿站提供号草,有时还不得不贿赂驿卒,以免对方不收。”
“咄咄怪事!他强征别人的,还拿不收来要挟?”
“世子有所不知,如果谁敢不按时按量地缴纳号草,驿站就会打张欠条盖个印,卖给地痞无赖。真到了那一步,才叫永无宁日呢。”
驿卒仍在殴打老翁,朱宸濠义愤填膺地上前制止,刘养正阻拦不及。
朱宸濠呵斥道:“住手!你们眼里还有没有王法!”
驿丞蛮横道:“老子就是王法,怎么,你不服?”
众驿卒将朱宸濠团团围住,刘养正大惊。
突然,驿丞的左脸被石子击中,怪叫道:“哎哟,哪个不长眼的浑蛋?”
话音刚落,右脸也被石子击中。只见一女子身披翻领碧色长衣,足蹬红云靴,持剑走来,却是娄素珍。
娄素珍飒爽道:“《大明会典》明文规定,驿站经费,从州县田赋中拨给。为了你们这帮吸血虫,他们早就掏过一次钱了。而你们,打着号草的名义,从朝廷骗了第二笔钱,现在还想再捞第三笔,这算盘未免打得也太精了吧!”
驿丞怒道:“驿站事关国朝安危,还轮不到你饶舌。把她给我抓起来!”
众驿卒一拥而上,被娄素珍打得抱头鼠窜。
娄素珍的剑架在了驿丞的脖子上,把他吓得求饶道:“女……女侠饶命啊!”
娄素珍威胁道:“今日之事……”
“一笔勾销,一笔勾销!乡亲们,都回去吧!”
众百姓散去。
娄素珍轻蔑道:“算你识相!”
朱宸濠上前一步,道:“多谢襄助,请问—”
娄素珍打断道:“你知道布政司参议诸养和家怎么走吗?”
朱宸濠点头道:“知道,就在滕王阁的西边。”
“多谢!”
娄素珍远去,朱宸濠望着她的背影,目光久久不离。
这日,王阳明在书房提笔凝视,纹丝不动地盯着一张白纸。
王畿双手托腮道:“小少爷,你都快把那张纸看穿了。有你这么练字的吗?”
王阳明认真道:“化城寺的方丈让我去学程明道,你知道学什么吗?”
“学什么?”
“明道先生说他写字的时候非常恭敬。不是为了字好,而因这是一种心法。古人做什么事都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
王畿打哈欠。
王阳明搁笔,道:“我刚开始练字时,对着古帖临摹,却只能学到字形,收效甚微。后来便再也不肯轻易下笔,而是凝思静虑,拟形于心,直到贯通其法,才提笔落纸,于是乎如有神助。”
门外传来管家的声音:“王公子,老爷让您去前面一趟。”
“好,这就来。”
王阳明出门,来到花厅,发现空无一人。正纳闷间,眼前一黑,被罩上了头套。
几个大汉三下五除二地绑了他,扔上马车……
王阳明暗中记忆路线,感觉马车驶出了城,颠簸良久,方才停下。
他被推下车,松了绑,摘了头套。几个大汉只是看着他笑,示意他爬上面前的一座小山坡。王阳明依言而行,上到坡顶,登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一片沙漠的中央被围栏围了起来,里面有座新建的木屋,张灯结彩。沙漠东边是奔涌不息的赣江,在夕阳的照射下金光闪闪。
“表哥。”
王阳明转身,只见一个美女正巧笑倩兮地看着自己,煞是好看。
“你是……芸玉?”
诸芸玉笑道:“南昌有豫章十景之说,分别是滕阁秋风、西山积翠、南浦飞云、赣江晓渡、龙沙夕照、东湖夜月、苏圃春蔬、徐亭烟树、洪崖丹井和铁柱仙踪,这厚田沙漠不在其中,鲜为人知,却是江南的一大奇景,相传因沙龙在此驻足而成。好看吗?”
王阳明脸红道:“好……好看。”
诸芸玉嫣然一笑……
第二天,厚田沙漠鞭炮齐鸣,热闹非凡。环绕木屋的,是几十桌丰盛的筵席。诸养和头戴四方巾,身穿重紫苏绸圆领的大袖袍,一张胖脸笑得像朵菊花,立在围栏门口迎客,接受来宾道喜。
管家高声道:“南昌知府黎大人到—”
已经入座的宾客交头接耳,诸养和谦逊地迎接。
“江西布政使顾大人到—”
宾客们啧啧称叹,诸养和的态度更为谦和。
管家愈加大声:“宁王世子朱宸濠到—”
宾客们一阵骚动,诸养和谦恭到了极点,亲自将朱宸濠引入上座。嘈杂声中,管家扯着嗓子喊了句“应天府解元唐伯虎到”。喧闹立刻停止,女宾们疯了般朝门口拥去。
只见唐伯虎身背长剑,揽辔缓缓而来。他一抬头,看见一群如狼似虎的女人高呼自己的名字争先恐后地冲过来,吓得从马背上跌落。
诸养和端着酒杯,走到正中,咳嗽了两声,道:“小女今日出阁,仰赖各位捧场,诸某真是三生有幸啊!”
木屋里,王阳明吃力地将一件胸前绣着鹌鹑补子的九品官服往身上套。这是新郎官穿的喜服,由于很多人一辈子都当不了官,民间能穿官服也就新婚这么一遭,故男子娶亲亦称“小登科”。
王阳明穿不上喜服,急得满头大汗,王畿过来帮忙。
屋外传来员外甲溜须拍马的声音:“诸翁真是别出心裁啊。厚田沙漠壮美如斯,怎么就没人想过在这举办婚礼?反正我是等不及了,快把令坦请出来让大伙瞧瞧吧!”
众人起哄。
王阳明紧张地望着木门,手忙脚乱。
门外,诸养和笑而不语。
罗钦顺起身道:“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诸翁的这位贤婿,据说是成化辛丑科状元王德辉先生的公子。今日宾客雅集,还是快快让我等一瞻风采,开开眼界!”
“赶紧的”“快点啊”的声音此起彼伏,诸养和满意地朝管家点点头。
管家走到木门前,拿出钥匙开锁。
门推开了,却空无一人。众人正感奇怪,王阳明尴尬地出现,僵硬地笑了笑。
喜服紧绷,缝线处几乎快被撕裂。
众人热烈鼓掌,王阳明小心翼翼地往外走去,每走一步都胆战心惊。王畿站在门后,担忧地望着王阳明的背影。
另一边,只见唐伯虎一手端着酒壶,一手持剑,在一个小山坡上作沙画。众女宾围观,如痴如醉。
唐伯虎潇洒道:“侠客重功名,西北请专征。惯战弓刀捷,酬知性命轻。孟公好惊坐,郭能始横行。将相李都尉,一夜出平城。”
唐伯虎边喝酒边作画,一幅《湖山一览图》逐渐呈现在眼前。只见他仰首灌酒,动作潇洒,引得众女宾尖叫连连。
木屋前,诸养和拉着王阳明的手逐一敬酒。王阳明喝晕了,眼前的景象模糊不清,只隐隐感觉到宾客们对自己极尽逢迎,耳边不断回响着“成化辛丑科状元王德辉先生的公子”。
敬到某桌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竟是娄素珍。王阳明以为自己出现幻觉,瞪大了眼睛。
诸养和觉察到异样:“这位是……”
管家凑近小声道:“兵部郎中娄忱之女、理学大师娄谅的孙女,娄素珍。”
诸养和笑道:“原来是名门之后。幸会,幸会。”
娄素珍与王阳明四目相对,眼波流转,其他人似乎都成了空气。诸养和有些尴尬,隔壁桌的朱宸濠看在眼里。
娄素珍道:“看你的样子不胜酒力。这一桌我替你敬!”
娄素珍夺过王阳明的酒壶,一饮而尽。她斜眼看着王阳明,眼眶里噙着泪。王阳明黯然神伤,诸养和大窘。
“不愧是喜酒,味道不错。你们慢慢喝。”娄素珍离席泪奔而去。
王阳明惆怅万千,朱宸濠则目不转睛地盯着娄素珍。
员外甲手指木屋道:“快看,新娘出来了!”
众人循声望去,娄素珍也站住了。只见木屋二楼的阳台上,诸芸玉戴着盖头缓缓而出,手持一枚宝玉。
诸养和大声道:“各位!这‘抛玉’是诸家祖传的节目,新娘将手里的‘奇魄古玉’扔向人群,新郎则必须戴着金丝手套接住,暗合‘金玉良缘’之意。”
管家将金丝手套交给王阳明,众人屏息凝视。
诸芸玉将玉扔了出去,王阳明踏出一步,却听见“哧”的一声,喜服被扯开了一道口子。
一阵大风吹过,“奇魄古玉”竟冲着娄素珍而去。娄素珍下意识地接住了玉,愣在原地。
四周鸦雀无声。
众目睽睽之下,娄素珍赌气般转身就跑。
管家反应过来,大声道:“快回来!”
几个家丁追了上去,娄素珍路过唐伯虎的沙画,小心翼翼地看着脚下,尽量不去破坏。众女宾破口大骂,见家丁拥来,更是自发组成人墙,将他们拦下,死命捶打。
娄素珍飞奔到围栏门口,翻身上马。
刘养正提醒道:“世子,那不是您的马吗?”
朱宸濠不接话,只静静地看着娄素珍在夕阳下策马狂奔。众人乱作一团,王阳明回过神来,奔至门口,上马去追。
诸芸玉蒙着盖头,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也不知是何表情……
长河落日,沙漠里只剩下王阳明和娄素珍一前一后两个身影。
娄素珍回首一笑,打马加速。眼看来到赣江边,王阳明用力一蹬,飞身跳到了娄素珍的马上。娄素珍翻身下马,往江边跑去。王阳明也跳下马,追了上去。二人扭打争抢“奇魄古玉”,双双跌倒,竟搂在一起滚到了江边。
停下来后,两人看着对方,不知该说什么。娄素珍冷不防地亲了王阳明一口,然后一把将他推开。
她起身跑到水里,拿出玉,作势欲扔。王阳明大惊,追上前去。
娄素珍恫吓道:“你再上前一步,我就把你的宝贝扔到江里。”
王阳明急停,道:“有话好好说,你想怎么样?”
“问你一句话。”
“什么话?”
“敢不敢像我一样逃婚?”
王阳明不语。
“回答我!”
王阳明撕了喜服,随手一扔。
娄素珍脸红道:“你……你干什么?”
王阳明冲了上去,一把搂住她,尽情地吻起来。末了,在她耳边轻语道:“你想去哪?我陪你去。”
娄素珍欣喜道:“庐山!”
庐山花径。
王阳明和娄素珍站在白居易手书的“花径”石碑前,观赏漫山遍野的桃花。
娄素珍嗅着花香,欢快不已,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白乐天的这首诗,真是道尽了眼前的美景。”
王阳明含情脉脉地望着娄素珍灵动的背影。
夜里,东林寺外,两人来到一口井前,只见唐太宗题刻的“聪明泉”三个字下方有首诗。
王阳明念道:“一勺如琼液,将愚拟圣贤。哈哈,难道喝了这里的水,就能当圣贤?”
“别光想着当圣贤了,怎么不念后两句?”
“欲知心不变,还似饮贪泉?”
娄素珍笑道:“要想知道一个人会不会变心,就看他能不能多喝这的泉水。”
王阳明看了看娄素珍,只见她俏皮地眨了眨眼,于是一把捞起井中的木勺,喝了起来。木勺很深,王阳明喝了一半停下喘气,只见娄素珍笑吟吟地望着自己,便又铆足了劲把剩下的喝光。
他把木勺递给她,娄素珍二话不说也舀了一满勺。她喝得很急,呛得直咳嗽。王阳明笑她狼狈,娄素珍不服气,又舀了一满勺,一饮而尽。
山里阴晴不定,第二天下午忽降阵雨,王阳明与娄素珍跑到御碑亭躲雨。
娄素珍好奇地抚摸石碑,道:“这是……”
王阳明仰观石碑,道:“当年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争天下,得到庐山一个叫周颠的赤脚和尚的帮助。等朱元璋坐了天下,便立了这个御碑亭,表彰周颠的功德。”
娄素珍笑道:“朱元璋心眼那么小,还懂得知恩图报。我在关外救过你,你说,该怎么报答?”
王阳明从怀中摸出一支短箭,递给娄素珍,道:“一命还一命,早就报答过了。”
娄素珍想起自己在关外遭娄忱逼迫,情急之下从王阳明的箭壶中抽出一支箭抵住脖子自杀,被他救下的场景。
王阳明道:“走,我们去含鄱口看日落。”
含鄱口是庐山的最佳观日点,含鄱亭被云海包围,宛若仙境。娄素珍冻得搓手哈气,王阳明拉过她的手,放到自己嘴边吹气,两人相视一笑。
忽然,云朵散去。远而望之,夕阳把鄱阳湖染成了赤色,水面波光粼粼,半壁河山都成了一幅绚丽的画卷。
王阳明赞叹道:“好一幅‘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
娄素珍动情道:“鄱阳湖真美,什么时候我们去那泛舟吧!”
“好啊!”
落日给这对璧人的背影镶上了一道金边,娄素珍情不自禁地把头倚在王阳明的肩上。
那一刻,王阳明觉得非常幸福,却又隐然感到这幸福会转瞬即逝。
半夜,娄素珍睡下了,脸上兀自带着笑意。王阳明给她添了床被子,一转身,一副玉镯掉落在地,滚到门口。
王阳明捡起玉镯,念及病重的母亲对自己说“这是你爹当年送给我的,替我把它交给芸玉”,不禁惆怅万分。
他看了看娄素珍,悄然走出东林寺。
月下,枕流石边坐着一个男子,似在打坐。
王阳明路过,驻足瞧了片刻。没想到男子蓦地发出一声长啸,惊得树林里的乌鸦一阵乱叫。
男子机警道:“什么人?!”
王阳明躲避不及,只好走了过去。
“王守仁?”
王阳明定睛一看,竟是王琼,不禁道:“王大人,您怎么会在这?”
王琼起身道:“朝廷调我到池州当知府,我就多走两步,来庐山看看白鹿洞书院。”
“孙燧还好吗?”
“他还在余姚,准备乡试。”
“哦。”
王琼正色道:“我路过南昌时,听人说你逃婚,把布政司参议的女儿晾在一边。是真是假?”
王阳明低头,小声道:“嗯。”
“唉!你怎么能做出这么荒谬的事?心里有别人?”
王阳明点头。
王琼看了看周遭,低声道:“私奔?”
王阳明又点了点头。
“你呀你,你害了两个人!你的妻子就不用说了,那个女人你也不可能明媒正娶,难不成这么躲一辈子,父母都不要了?”
王阳明一惊,抬头看着王琼,喃喃道:“我、我……”
“你什么你?还不快回去?!”
回到东林寺,王阳明发现娄素珍仍在熟睡。他收拾好行李,看了看爱人的脸,凑过去轻吻了一下,泪水夺眶而出,滴在枕头上,发出“滴答”的声音。
他把那支短箭放在枕边,夺门而去……
王阳明躺在马背上,信马由缰地望着月亮发呆,不知不觉来到南昌城里的一所道观,只见门额上题写着“铁柱延真宫”五个大字。
王阳明下马入,穿过大殿,但见一个不大的水池被石栏杆围着,里面戳着根锈迹斑斑的铁柱。水池前摆着一座半人多高的香炉,旁边立有一石碑,上书“镇蛟铁柱”四个大字。
整个道观只有一间静室亮着灯,王阳明走到门口,正待敲门,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出:“一晃二十年,伯安都做了新郎官了。”
王阳明大惊,推门而入。
诸府早已炸开了锅。
诸养和拍案而起道:“大婚之日,合卺之时,新郎官居然不见了,当真是古今未有的奇谈!继续找!掘地三尺也要给我找出来!”
管家还从未见诸养和发过这么大的火,俯首道:“是,老爷!”
洞房里,喜帐高挑,锦衾绣枕,两根小碗口粗的龙凤泥金大红蜡烛已经燃掉半截,烛泪淋漓。诸芸玉戴着盖头坐在喜床边,纹丝不动。
诸妻入内,看了眼铺着鸳鸯红锦台面的花梨木圆桌,只见上面摆着的和合面都凉透了,糊成一团,不禁叹气道:“芸玉啊,你爹已经派人去找了。把盖头揭了,先吃饭。”
诸芸玉一言不发,诸妻摇头离去。
铁柱宫的静室里,王阳明与无极道长相视而坐。
王阳明感叹道:“没想到时隔多年,竟在这里与道长重逢。”
无极道:“伯安气色不好,莫非身体有恙?”
“道长神通广大,能否算出我阳寿几何?”
无极掐指一算,平静道:“不到六十。”
王阳明沉默半晌,叹息道:“人生忽然而已,太短太短,什么事都干不成,倒不如学道家的养生术,做个不死神仙。”
“不死?呵呵,路再长,也有走完的时候。”
“敢问道长贵庚?”
“惭愧,九十有六。”
“啧啧啧,何愧之有?这岁数都够短命鬼活两回了。”
“生死修短,岂能强求?再说,人这一世,苦多乐少,活得太久未必不是一种惩罚。”
王阳明长吁道:“是啊,人世虚无,虽有点滴美好之事,终不免化作焦土。昔日碧山苍翠,如今荒岭鬼哭。多少繁华都成过眼云烟,多少爱恨掩埋于断井残垣。盛极而衰,荣枯轮转,此乃天道。”
“伯安有心事?怎么生出这么多感慨?”
“我……我想追随道长云游四海。”
无极大笑道:“你虽一时消沉,终究一副官相。”
“官相?官场有什么意思?名利一夕间也许会消逝,权力不可能任你主宰,还是当名士好。名士无冠,王者尊之。”
“世事无常,穷通莫测。你现在这么想,将来怎样还不好说。不过,这养生秘法嘛,贫道倒是可以教你一套导引术。”
王阳明眼前一亮,道:“多谢道长!”
无极用左手虎口抱住右手四指,右手虎口抱住左手拇指,两只手在虎口处正好形成一个太极图。又翻过手来让王阳明看,只见两手拇指正放在手掌心的劳宫穴上。
王阳明依样画瓢。
无极道:“你听好了。手抱太极,脚分阴阳。闭口藏舌,二目垂帘。意守祖窍,气沉丹田。”
王阳明随无极打起坐来……
不知过了多久,王阳明周身酸痛,有些倦怠,不由得睁开了眼。
无极闭目沉吟:“着于心,不着于形;固于本,不固于体;身无为,而意有为。如江岸苇,似炉中香。”
王阳明放松肢体,收束精神,继续打坐……
东曦既驾,绳金塔沐浴在清晨的第一缕光中,南昌城在悠远的钟声里苏醒过来。
铁柱宫的静室香烟缭绕,王阳明仍在打坐,无极却已不见了踪影。
王畿推门而入,大惊道:“哎呀小少爷,你怎么在这呀!赶紧走吧,再不回去要出大事了!”
王阳明睁眼,恍惚道:“江岸之苇随风而曳,不动其根;炉中之香似有若无,不着其痕—王畿?”
王阳明起身,却因坐得太久,两腿酸麻,栽倒在地……
回到诸府,只见诸养和的胖脸气得鼓鼓的,挤眉瞪眼地坐在前厅。王阳明快步上前,下跪道:“爹。”
诸养和强忍怒火道:“你上哪去了?”
“我、我……”
管家凑近耳语,诸养和色变道:“什么?铁柱宫?”
他看了眼众人,担心问多了都是话柄,传出去脸上无光,只好把气撒到下人头上,道:“一帮吃干饭的东西,连个大活人都看不住!”
说完,转身离去。
管家对王阳明道:“姑爷,去看看大小姐吧。”
王阳明回过神来,起身往洞房走去。
来到门口,他迟疑片刻,推门而入。
只见诸芸玉戴着盖头,硬邦邦地坐在床边。全身上下只有左手露在外面,春笋般细长的手指紧紧地握成一个粉拳。
王阳明心里发怵,瞥见桌上放着一根紫檀木的秤杆。这是用来挑盖头的,取“称心如意”之意。王阳明拿它挑开了盖头。
但见诸芸玉双目闭合,脸色惨白,右手死死地握着一把剪子,顶住下巴。
王阳明大惊道:“芸玉!”
诸芸玉缓缓睁眼,有气无力道:“表哥……”
王阳明一把夺过剪子,道:“你这是做什么?”
“我怕坚持不住晕过去,丢人现眼,倒不如一死以全名节。”
王阳明五味杂陈道:“芸玉……”
窗外,诸养和正小心翼翼地偷听。诸妻走了过来,往里瞧了瞧,低声道:“我看守仁这回彻底被咱闺女给降服了。”
诸养和皱眉道:“但愿如此吧。让他们赶紧回乡省亲。”
三日后的南昌码头,王畿把行李扛上客船,王阳明与诸芸玉辞别诸养和夫妇。
诸妻抹泪,诸养和挥手催女儿上船。
诸芸玉依依不舍地离去……
客舱宽敞,分为里间和外间。
诸芸玉在里间的床上熟睡,王阳明趴在桌上,面前摆着一本摊开的书。夜里,他悠悠转醒,四下里看了看,唤道:“王畿!”
王畿的声音从外间传入:“小少爷,您醒了?”
“到哪儿了?”
“快到广信了。”
王阳明起身,来到外间。
王畿神色慌张,低声道:“大事不妙。”
王阳明道:“怎么了?”
“刚才我从甲板回来,看见有人在门外偷窥。我暗中跟踪那厮,结果发现这船上有贼人。”
“几个人?”
“五个。看样子都藏着凶器。”
“在哪?”
“船尾。”
“走,去瞧瞧。”
“啊?”
船尾的甲板上坐着一堆旅客,王畿给王阳明使了个眼色,只见四个贼人缩成一团,贼眉鼠眼。
王阳明佯装观赏风景,背着手走到船舷边。
王畿跟了上去。
王阳明故意道:“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江西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皇上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四个贼人警觉。
王畿反应过来,道:“小少爷,出来走走也好!久居京城,几时见过这等美景?再说了,江西一巡,何等风光!”
“这倒不假,抚台大人与我称兄道弟,还特意派人快马赶到广信,预作安排。呵呵,想必那广信知府已在码头恭候多时了。”
“说不定还带着兵丁呢!您要是有个什么闪失,他的仕途也便到头了。”
贼人面面相觑,贼人甲小声道:“看样子不好惹,还是瞧瞧老五那边吧。”
众贼人点头,相继离去。
王阳明与王畿对视一眼,若无其事地跟了上去。
另一间船舱,贼人老五在窗外察看,四个贼人走近。
贼人甲问道:“怎么样?”
老五点头。
贼人甲下令道:“动手!”
五个贼人各自摸出竹管,戳进窗纸,凑近去吹。
王阳明大喝道:“大胆贼人!”
贼人甲惊得掉了竹管。老五回头,二话不说,抽刀便砍。
贼人甲制止道:“老五,他是……”
王阳明空手夺了老五的刀,架在他脖子上。
贼人甲豁出去道:“不管了!弟兄们,上!”
王阳明以一敌五,把贼人揍得鬼哭狼嚎,贼人甲还被踢到了河里。
众贼人狼狈而逃,一人推门而出,竟是唐伯虎。
唐伯虎惊讶道:“这是……”
王畿道:“还不见过救命恩人?要不是我家小少爷,你早就被贼人迷晕了!”
唐伯虎回忆道:“你……你不是那日结婚的王阳明吗?”
王阳明笑道:“你好,唐解元。”
唐伯虎将二人请入,王阳明这才发现朱宸濠也在。
朱宸濠亲自倒茶,见王畿站得远远的,做了个邀请的手势,道:“过来坐呀。”
王畿摆手道:“没事,你们聊,我站着就好。”
朱宸濠道:“过来吧!拘谨什么?”
王畿看了眼王阳明,见他冲自己点了点头,方才过去坐下。
朱宸濠道:“多谢王兄!我还真带着不少金银细软,险些让贼人暗算。”
“世子不必客气。你们这是要去哪?”
“就在广信下,去芸阁。”
“芸阁?”
唐伯虎插言道:“世子要拜访娄大师。王兄若没有紧要的事,不如与我们同去?”
王阳明眼前一亮,道:“娄谅娄一斋?”
唐伯虎点头道:“正是。”
王阳明喜形于色道:“方便吗?”
朱宸濠道:“方便!王兄肯去,再好不过。”
王畿嘀咕道:“小少爷,你又乱跑……”
王阳明笑道:“王畿,你当年卖假药的时候不是凭着一个老君像就敢断言对方的病能不能治吗?”
王畿脸红道:“过去的事,还提它做什么?”
王阳明道:“这娄谅能预测福祸,你不想一探究竟?”
王畿一脸怀疑道:“真的假的?”
王阳明道:“比你真多了。早年他去考进士,走到一半便折返回乡,家人都很生气,他却说‘我这次应试,非但中不了,还会遭遇奇祸。所以最好不要去’。”
王畿追问道:“那后来呢?”
王阳明道:“后来考场失火,考生被烧死者不计其数。”
王畿咋舌道:“既然这么神,那就听你的。不过,以后能不能别说我卖假药?很多病不吃药也能好,我那是给病人家属一个善意的安慰。”
朱宸濠与唐伯虎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