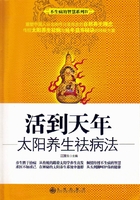离开吴学仁家、于占吉没回家,而是拐个弯儿去了帽子家。
“咚咚咚,咚咚咚。”于占吉连敲两遍才把帽子家敲出来,“你那耳朵有毛病吗?”
“一个耳朵能顶你那两个灵!”帽子家说,“我是忙着拉呱儿没听见。”
“和谁拉呱儿?”于占吉一时弄不清,天这么晚了,是谁还在这里。
“还能和谁,就是让你愁得整夜睡不着觉的那一个。”帽子家说,“今后晌总算让我把吉光说通了。”
“改姓的事他也认头了?”于占吉小声问。
“不认头那能叫说通了吗?”帽子家朝吴学仁家的方向指了指,“要不是好端端的吴林娶了傻大菊,要不是吉光亲眼看见傻大菊下轿、拜天地的傻样儿,我估计不一定能说通他。光他爹,吴学仁帮了你家的大忙了。”
于占吉想说,我也帮了吴学仁的大忙了。但他急着进屋,已顾不得说这些了。
“吉光啊,你总算想过来了。”于占吉破例走到儿子跟前,摸了摸他的头。
吉光勉强叫了一声爹,但没好意思抬头。他觉得“嫁”出去不光委屈了自己,更对不住爹。
“大娘,爹,”吉光猛然间又冒出个新想法,“我在咱村找媳妇……不,我‘嫁’到咱村里行吗?”
“行啊,刚才你咋没说?”帽子家眯起双眼看着吉光,“早有目标吗?”
“行啊,行啊。”于占吉一听这话,也以为吉光是早有目标,“姓吴的,还是姓罗的?”
“我想嫁个姓于的。”吉光天真地说,“嫁个姓于的我还能姓于。”
“傻孩子,你这叫捂着耳朵偷铃当啊!有好闺女的于姓户,没有一个敢‘娶’你的。为啥?就是因为你改来改去还姓于,脱不掉地主子弟这张皮呀!”于占吉泄气地说,“我还以为你在咱村的吴、罗两姓里早有目标呢!”
“吴、罗两姓里就算是有想招我为女婿的,也招不了我去。”吉光说,“我无能我就滚出于家屋子,改姓就到外村去改的,决不在本村丢人现眼。”
有啥丢人现眼的?这话刚到嘴边就被咽了下去。于占吉埋怨自己道,你咋不考虑考虑孩子的承受能力呢?俗话说“小子无能,改名换姓”,吉光真是无能也就罢了,家里穷得娶不起也就认了,可这两条与这个家庭一点关系没有,好好的一个孩子活活被你坑了,还好意思说“有啥丢人显眼的”,你个老不要脸的东西!
“光他爹,你咋不作声啊?”帽子家说,“依我看,吉光的话也在理儿。街里街坊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今日还是于吉光,明日就成了吴吉光、罗吉光,不光吉光接受不了,就连街坊们也觉得别扭。唉,改后面的字容易,改前头这个字难啊!”
“我……我不作声是等着你作声。”于占吉遮掩起自己的苦恼,露出一脸的苦笑,“孩子的事孩子说了算,孩子找个啥号的全凭你推荐。”
帽子家说:“那好,三、五天后听我的信儿。”
五天后,帽子家给吉光物色了三户人家,任他挑任他选。吉光挑选了干家屋子干亭柱的闺女小绵。
干家屋子离于家屋子只有二里地。干亭柱是三代祖传的正骨先生,他爷爷当年被村民们称为正骨仙医,黄河三角州一带至今流传着他家过年用不着包饺子的故事——
有一天夜里,亭柱他爷爷被一阵轻轻地、敲屋门的声音所惊醒。说是人敲吧,院门早已关上;说不是人吧,敲门声又很有节奏感。仔细一听,响声来自门的下半部分,哪有这么矮的人?亭柱他爷爷有点儿害怕,可他越害怕就越想看个究竟。
慢慢把门开开,一只黄鼬抱着它的孩子走了进来。黄鼬胆怯地看了亭柱他爷爷一眼,然后两只前爪一伸,把孩子递给了他。
亭柱他爷爷把小黄鼬放在炕上,小黄鼬吱吱地叫着,试图站起来。可它的后肢就是不听使唤。他给它做了检查,发现它的一只前腿脱臼,一只后腿骨折。前腿好治,他只拽了几下、推了几下,关节就复位了;后腿难办,折断的骨头都错到一边去了,必须经过牵拉、复位后固定。亭柱他爷爷摸人的胳膊腿儿摸惯了,乍猛的摸起黄鼬那胳膊腿儿来,不是一般地不适应,而是很不适应。摸人那胳膊时一只手攥不过来,摸人那大腿时两只手攥不过来,摸黄鼬那胳膊腿儿时,根本用不着攥,只需用俩指头捏着就行了,稍一不注意劲儿就用大了。在推、拽、按、捺的过程中,小黄鼬不时发出一声声尖叫。尖叫声使黄鼬妈妈变得烦躁不安,它把前腿搭到炕沿上,甩着长长的尾巴,用狐疑的目光望着亭柱他爷爷。
亭柱他爷爷不管它是听懂还是听不懂,只顾对着黄鼬妈妈说:“给人接胳膊捋腿时,人也是疼得嗷嗷叫,恁那孩子细皮嫩肉儿的,前、后腿比人那指头还细,稍一用劲儿就用过了头,不好掇弄啊!”
黄鼬妈妈好象听懂了他说的话,耳朵一耷拉,前腿迅速离开炕沿,蹲在地上静静地等待。
经过一番细心地包扎,小黄鼬的后腿固定好了。亭柱他爷爷用五指当梳子,从头到尾给它梳理了好几遍,舒服得小黄鼬发出类似呻吟的声音,身子一个劲地往他跟前靠。
按照常理,大人抱着孩子来串门儿,户主就应该给孩子找点好吃的东西;黄鼬妈妈抱着小黄鼬初次登门,亭柱他爷爷觉得也应该给它找点儿好的吃,它也是个孩子呀!忽想起夜里打鼠的夹子曾响过,跑进里屋里一看,果然打着一只。他提着老鼠尾巴在小黄鼬面前晃了晃,馋得它伸出前爪儿、连抓带扑,看来它脱臼的那条前腿已完好如初。
也许怕打扰亭柱他爷爷的时间太长,小黄鼬刚叼起老鼠,黄鼬妈妈就抱起了它。临走前黄鼬妈妈没有更好的办法表示感谢,只是深情地望着他,一个劲地摇尾巴。
一溜十八屋子一带的村民,都是年三十晚上包饺子、年五更下。给小黄鼬看病的这一年的年五更,见亭柱他奶奶烧开了锅,亭柱他爷爷就去里间屋里端饺子,刚点起灯就惊得重新跑回外间、拉住老伴儿的手说,你看,你看,你快进去看。亭柱他奶奶一看就跪下了,朝着她摆放饺子的盖垫,磕头如捣蒜。原来在她包的那盖垫饺子上,又胡乱摞上了一大堆饺子,堆成了“饺子山”,满得眼看就要从盖垫边儿上往下滚。这些饺子是从哪里来的?亭柱他爷爷抬头一看,里间屋窗户上糊的那层纸,都被撕得烂烂乎乎了。这些外来的饺子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有肉馅的、有素馅的,有忘了放盐的,有咸得不就干粮就没法吃的。亭柱他爷爷每天早晨下一锅儿,一直吃到正月十五。
第二年的年五更又是这样。到了第三年上,亭柱他奶奶干脆就不包饺子了,年三十后晌放到里间屋里两个空盖垫,年五更烧开了锅、着下饺子就行了。
吃“百家饺子”连续吃了七年,第八年的年五更又进里间屋端饺子时,看到的却是两个空盖垫,亭柱他爷爷的眼圈儿一下子就红了……
把正骨手艺传给亭柱他爹后不几年,亭柱他爷爷就“走”了。他走了日本鬼子就来了。亭柱他爹弃医从戎,在黄河三角洲一带的八路军清河军区,当一名普通战士。有一次连长派他和一名神枪手押送俘虏,连长说这几天连里人手不够用,押送二十名俘虏到大队部的任务,只能交给你们两个人去完成了。神枪手说路上出了问题咋办?平时押送这么多俘虏,可是由五六个人去完成啊!我打枪打得再准,他们要是四处乱逃的话也打不过来呀!连长说我也不是不担心,实在是腾不出更多的人手。亭柱他爹说,人手不够我自家去算了。神枪手说,你那本事比天还大吗?亭柱他爹说,人各有各的本事,我打枪不如你,干别的事儿不一定不如你。
“你一个人要是能完成这项任务。我给你记三等功。”连长以为他是闹着玩儿。
“完不成任务提着脑袋瓜子来见你。”亭柱他爹说,“这一路都是解放区,遇到敌军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唯一应防备的就是俘虏们逃跑,而我最不怕的就是他们逃跑。”
“有啥绝招儿你得当面说出来,让我评估评估。”连长既担心跑了俘虏,又担心自己因这事犯错误。
“说给你听不如做给你看。”亭柱他爹领着连长和神枪手朝俘虏们走去。他来到一个大个子俘虏跟前,一手按住他的右肩,一手攥他的右手腕儿,并从上到下瞅了瞅他这条胳膊。
“嗨,嗨!”亭柱他爹攥住俘虏手腕儿的那只手用力往上一推,又用力往下一拽,就把他的右胳膊“卸”了下来。也就是说,肱骨和肩胛骨脱位了。
当亭柱他爹准备卸他的左胳膊时,大个子俘虏说话了;“八路哥,你卸胳膊的目的不就是怕我们逃跑吗?卸下一条我们就跑不了了,跑和走一样快了;卸下两条的话,不光给你增添多卸二十条的麻烦,一路上还会给您增添很多麻烦。”
“给我添啥麻烦?”亭柱他爹一时没明白他话中的意思。
“你算算,”大个子俘虏说,“卸下一条胳膊我们小解时还能解腰带,你只需给我们扎腰带就行了;卸下两条胳膊,解腰、小解、扎腰,就都得麻烦您了。”
亭柱他爹觉得有理,就听从了他的意见。
半路上,亭柱他爹给一个俘虏扎腰时,恰巧旁边有一片树林,大个子俘虏乘他不备,拔腿就往树林里跑。亭柱他爹朝天开了一枪,用以警示其他俘虏,然后甩开两条胳膊去追赶甩开一条胳膊的大个子,没费多大气力就追上了。原想一脚踢翻他,在树林里砸他一顿解解恨,又怕那些俘虏们趁机逃跑,于是就用枪托子顶着他的脊梁,把他押出树林。归队后,随即把他的另一条胳膊也卸了下来。多给自己添点儿麻烦是小事,跑了俘虏是大事。
正当亭柱他爹准备把俘虏们的另一条胳膊都卸下来时,一个小个子俘虏对他说:“大个子是个傻大个儿,他逃跑是不知天高地厚,是不想给自己留后路,刚才您撵他时我就估计,您回来后可能要卸我们的另一条胳膊,果然让我猜中了。八路哥,弟兄们让我当代表,跟您说几句。”
“有话快说。”亭柱他爹一只眼盯着小个子,下意识地用另一只眼睃了一下大个子。
“用不着再给我们卸另一条胳膊了。”小个子说,“从卸下一条胳膊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跟你跟定了,撵也撵不走了。”
“为啥?”亭柱他爹催他说出理由来。
“离开了您,谁还能为我们推上这条胳膊呀?”小个子抬他的右胳膊抬不起来,只得伸出了左手的大拇指,“象您这样高超的医道,我们别说见过,连听都没听说过!”
亭柱他爹相信了小个子的话。
到达目的地时,大个子俘虏的褂子、裤子差不多全湿了——褂子是被汗溻湿的,裤子是被尿尿湿的。
干亭柱的医道不如他爷爷高,也不如他爹高,但他所接触的某些病号级别高。爷爷的辉煌是给小黄鼬接胳膊捋腿儿,爹的辉煌是押送俘虏,也就是说,他俩一生只给草仙、草民们看过病,而他的病号中却不乏科局级干部,他曾给乡长正过脚踝,他曾给女县长按揉过手腕儿。
平民百姓谁跟县长握过手?就算和县长走个面对面,他不伸手你也干眼馋没办法。
县委、县府的干部们谁敢胡乱揉搓女县长的手腕儿?能跟她握握手就不错了。
干亭柱也没想到能揉搓揉搓姓胡的这个女县长的手腕儿,说起来这机会应算是临河公社的杜书记给的。有一年公社超额完成了公粮征收任务,为确保下一年继续超额完成任务,胡县长在麦收时节亲临临河视察。光在公社视察显得太官僚主义、太脱离群众,习惯的做法是再挑选几个大队视察视察。
杜书记领着胡县长去了干家屋子。这次所谓的视察,就是小领导领着大领导到基层走一走、看一看,活动活动手脚干一干。
胡县长见路边有个社员在刨一棵树,夺过锨来就想帮着他干。刨树可不象翻地那样轻松,翻地时翻一锨是一锨,刨树时有些根在暗处看不见,一锨刨到树根上就白刨了。胡县长刨了七、八锨,有五、六锨刨到了树根上,反冲力撞击得她那身子一歪一歪的,杜书记怕他扭伤关节、或一腚蹾在地上不雅观,硬是把锨从她手中夺了过来。
顺路再往前走,就是生产队的麦场。胡县长见一老汉正在扬场,伸手把簸箕要了过来。胡县长年轻时当过几年农民,场里、地里的活都会舞弄两下子,她把簸箕往后一伸,管着上锨的社员眼疾手快,满满一锨掺杂着麦糠的麦粒,被“颠”进了簸箕里。胡县长左腿向前迈半步,右腿往后一伸,胳膊往斜上方一扬一甩再往后一带,簸箕里裹挟着麦糠的麦粒“刷”地一声腾空而起,在他的斜上方形成了一条长长的抛物线,风吹糠、麦两分离,这一连串动作完成得干净又利落,赢得了在场社员们的一片掌声。受到鼓励的胡县长越扬越有兴趣,越扬越熟练,越扬抛物线越高,这哪里是在扬场,简直是在表演。一簸箕,两簸箕……十二簸箕,忽然,胡县长扔下簸箕,用左手攥往了右手的手腕子。杜书记跑了过来,大队书记、生产队长跑了过来。哪个当官的跑过来也白搭,只有把干亭柱叫来才管用——胡县长晃着手腕儿了。
还没等干亭柱走到跟前,胡县长就朝他伸出了右手,也不知是主动和他握手,还是让他捋手腕儿。
干亭柱弄不清胡县长的真实意图,也不知她是晃着了哪只手的手腕子,只好一手握住胡县长的手,另一只手攥住胡县长这只手的手腕子。问她进村后都干了些啥活儿,胡县长就把刨树和扬场的过程原原本本说给他。这可不是县长向社员汇报工作,这是医生对病号进行的必要问寻。
根据胡县长的讲述,干亭柱分析:刨树和扬场都需手腕子用力,刨树对手腕子有一种往里戳的劲儿,扬场时手腕子往后一甩又往前一撩……干亭柱边分析边揉搓县长的手腕子。通过揉搓、通过摸弄他断定:胡县长的手腕子是筋跳槽儿。
胡县长一听,拍着扬场老汉的肩膀对干亭柱说:“这个老哥天天扬场筋都没跳槽儿,我扬了几下子怎么就跳槽儿了呢?”
“打铁的手上长茧子,挑担的肩上长茧子,拿钢笔的中指上半截的里侧长茧子,用哪里用得勤哪里就经磨呀!”干亭柱说,“单是刨树或扬场也许跳不了槽儿,两桩靠手腕子用力的活连在一起,又加上你不经常干,又加上心情激动干得猛,所以就跳槽儿了。”
“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止住疼、象先前那样活动自如?”胡县长不注重发病的原因,只关心结果。
“不是我姓干的吹牛,”干亭柱借机紧紧攥住胡县长的手腕子说,“哪里跌倒哪里爬,我就在你晃着手腕子的这地方、治好你的手腕子。”
在场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在胡县长的手腕儿和干亭柱的两只手上。
干亭柱攥住胡县长的手腕子也推也拉、也揉也搓,边推拉边揉搓、边看她的表情。不一会儿,胡县长的汗从额头流到了腮上,干亭柱的汗从腮上流到了脖子上;不一会儿,跳槽儿的筋归了槽儿,按照老百姓的习惯说法叫做“捋”上了。
“谢谢干医生。”胡县长紧紧握住了干亭柱的手。
干亭柱激动得把左手也搭了上去,胡县长又把左手搭在了他的左手上,四只手抱成了一个“指头疙瘩”。
“干医生”三个字出自县长之口,这是多么抬举干亭柱的一个称呼啊!
乡下人都把正骨先生叫做捋胳膊捋腿儿的。外村人来请干亭柱找不着门儿时,见人就问:你们村那个捋胳膊捋腿儿的住在哪里?只有少数城里人来求他时,才称呼他为干先生。称呼他为干医生的,到目前为止只有胡县长一人。
在之后的日子里,干亭柱的服务圈儿越来越大,慕名登门的越来越多,偶尔还有吉普车停在院外的时候,真给他壮门面啊!
假如把给县长捋手腕儿、看做是干亭柱的“过五关斩六将”,那么给小寡妇捋腰就应算是他的“夜走麦城”。认为把村民们对他的误会称做“夜走麦城”有点牵强的话,那就称它为“夜走小麦城”吧。
这小寡妇是干亭柱的一个街坊小婶子。她在挑着一担水快到家门前时,只顾和路边人说话,不慎踩在一块反扣着的西瓜皮上,桶飞水撒人下趴,摔倒后就站不起来了——她的腰被严重扭伤。
干亭柱和路边人把她扶进屋里、放到炕上后,路边人走了,他却不能走,他得为她捋腰。
小婶子岁比他小、个儿比他矮,但腰比他的腰粗了一圈儿。为便于操作,他让她趴在炕上,把她的褂子往上掀了掀,裤子往下褪了褪,雪白而有些微微颤动的腰部,便亮在了他的目光下。摸一把摸不透,摁一下嗷嗷叫,不用力捋不行,用力过猛还实在是有些不好意思。唉,捋胳膊捋腿儿易,捋腰难、捋异姓的腰更难。可又一想,干哪一行也不可能一帆风顺,玩船的会遇上顶头风,推小车的会遇到上坡路,比起逆风和上坡来,捋个粗腰又算得了啥?玩船、推小车的面朝水、土背朝天;捋胳膊捋腰的风刮不着雨淋不着,想歇歇就歇歇,想喝喝就喝喝,全都是自家说了算,有啥难的?
不比不知道,一比知足得不得了,干亭柱对破解眼前这一难题充满了信心。他挽挽袖子、搓搓手,贴近炕沿靠近腰,双手五指伸开,两手掌贴近胯骨上缘,两拇指分按在脊椎骨两侧,试探性地往上一推,“哧溜”一下,十指已溜到了肋骨跟前——小婶子吃的油水太多,腰不光粗、还打滑。
干亭柱把毛巾泡进热水里,打上胰子使劲揉,然后用热毛巾使劲搓自己的手、搓小婶子儿的腰。手、腰洗净凉干后,十指拤腰又一次往上一推,磨擦系数顿时增大,效果果然不错。
“小婶子儿,放松,放松。”干亭柱说,“接下来一切都得听我的,要有不怕疼的准备。”
干亭柱从小嘴就巧,见了同辈的哥嫂、不叫哥嫂不开口,见了上辈的叔、婶儿,不叫叔婶儿不说话。
“嗯,嗯,”干亭柱双手拤腰使劲推、用力按,在推的过程中按,在按到恰到好处时推。
“哎呀,哎呀——”小婶子疼得直叫唤。
“小婶子儿,嗯、嗯——”捋腰属重体力活,干亭柱的额头冒出了汗。
“哎哟,哎哟——”小婶子的额头也冒出了汗。
“小婶儿,嗯、嗯、嗯!”干亭柱用尽全身的力气猛地一按又一推,终于听到了来自腰椎骨节间令他熟悉的响动声。
“哎呀,哎呀,哎呀呀——”要不是有两只大手压在腰上,小婶子儿准会疼得满炕上打滚儿。
“哎呀小婶子儿啊,可累煞我了!”干亭柱在喊累的同时,仍没忘了关心小婶子,“舒坦了吧?”
“嗯,舒坦了。”从小婶子儿的声调中,就能听出她是在微笑着说话。
“腰下再垫上个枕头。”干亭柱边说边帮她翻过身来,“这个架势挺舒坦吧?”
“嗯,挺舒坦。”小婶子边说边舒服地呻吟着。
一前来串门的老光棍儿,就在这时进了院子,他听到屋内的声音和对话后,知趣地走开了。
干亭柱给小寡妇捋腰的笑话,丰富了人们睡前饭后的谈资,缓解了田间地头的疲劳,在于家屋子一带久传不衰。
干亭柱不论给谁捋胳膊捋腿儿,一律不收钱。不收钱人们也不白让他捋,夏秋季他家里不缺瓜桃梨果,冬春季不缺红糖挂面,他老伴儿到经销点上去买油盐酱醋,从来都是用鸡蛋换。逢年过节请他的不断,不光过了酒瘾,还省下了饭。
各家有各家的难处,人家眼热他家庭条件好,他眼热人家有结实孩子(小子)。随着女儿小绵日渐长大,干亭柱打好了招养老女婿的谱儿。想把人称“暄物”的闺女,当成结实孩子使唤。
消息一传出,干家屋子的适龄男青年跃跃欲试。干家屋子是父子爷们儿村,除了饲养员赵大叔和外村嫁进来的媳妇,都姓干。在本村招婿不能说招不到好的,但干亭柱不想在本村招。原因就是招来个姓干的女婿,改姓和不改姓一个样,同意改和不同意改看不出来,澡堂子里尿尿没处查的。说不定女婿看中的是你的家庭条件,白赚个媳妇还捎带着受一份财产。就算女婿确乎是一个好女婿,决不会骗你,亲朋好友也会认定你是受了骗——招来个没改姓的女婿,你却认为他改了姓,那是自欺欺自。
打消了在本村招婿的念头后,干亭柱就把目标对准了周围的村子。或者说打消了招同姓女婿的念头后,又把目标对准了异姓。可一句“小子无能,改名换姓”的古训,把所有好儿男都挡在了这道门坎儿之外。
正当干亭柱为招婿的事愁得茶饭不思时,平地一声惊雷,送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五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子弟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对贫下中农来说也算不上什么好事儿,但对急于招婿的贫下中农干亭柱来说,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从五类分子子弟中挑女婿,已成了一家三口的共识。
求谁来当这个媒人呢?不打算在本村招女婿、最好还是不在本村找媒人,以免让媒人无缘无故地得罪人。外村的媒人他物色了好几个,挑来挑去还是选中了于家屋子的帽子家。
求人家给儿子说媳妇也许不怎么憷头,求人家给闺女招女婿实在是难以开口。难开口也得开口,自家的事自家不说人家咋知道?自家的事自家不去求人,难道等着人家来求你吗?
“回去等我的信吧!”听干亭柱说明来意后,帽子家就把干小绵的名字记在了她的本子上。
帽子家的本子上记了很多闺女的名字,她给吉光推荐了三个,吉光从中挑选了干小绵。
干家屋子和于家屋子、就象是一个稍微断开了一点的大村,吉光和小绵十二、三岁上经常在一起玩儿,十五、六岁上见得就少了。女大十八变,长大后的小绵和吉光、相互从未认真看上几眼,所以双方都愿意“小见小见”。
帽子家把“小见面儿”的地点选在了临河大集上。她让小绵提前赶到水煎包子摊儿的左边,假装买包子,然后领着吉光走到包子摊儿的右边,拍拍他的肩膀说:“吉光,你不买包子吗?”
——这是“拍”给小绵看的。
“哟,是小绵啊!你打算买包子呀?”帽子家走过去攥往了小绵的手。
——这是“攥”给吉光看的。
四目隔摊儿相望,在相望的同时,两人的目光还不住地往别处斜,假装谁也没看见谁。
“小见”后双方没意见,接着就准备“大见”。于占吉对吉光说:“这门新亲家条件比咱高,礼节上咱得处处大方着点儿,别让人家看不起咱。当下‘见面钱’一般都是五块,咱掏十块,你看怎么样?”
“不怎么样。”吉光说,“依我看一分也不花。”
“该省的省,不该省的咱不能瞑起个眼来瞎省。”于占吉说,“大见面儿男家头儿哪有不花钱的?”
“不是我瞎省,而是你瞎花。”吉光说,“‘大见面儿’时男家头儿花钱那是因为男家头儿娶。咱这个男家头儿是嫁,是假男家头儿,干亭柱才是实际意义上的男家头儿。按说他应该装上钱、提上礼到咱家里来‘大见面儿’才对,把见面儿地点定在他家已经是抬敬他了,不让他掏荷包已经是便宜他了。到见面儿的那一天,我空手攥空拳、三根筋挑着个脑袋去,他家同意就成,不同意就散。”
“前几年我操办的那几副‘招婿媒’,大见面儿时和一般的媒也没啥两样。”帽子家说,“见面礼是男家头儿出,见面钱也是男家头儿拿。”
“前几年那些给人家当养老婿的,大都是家里穷得娶不起的。”吉光仍坚持自己的看法,“要不是让成分逼的,咱这样的家庭、俺哥这样的人材,拿座金山也换不了去。招个好女婿就够他干亭柱的了,咱凭啥再给他送钱花?”
“也是这么个理儿。”帽子家说,“到那天咱就空着手去。”
果然让吉光算了个正着,面对“赤手空拳”的他,干亭柱笑脸相迎,先酒而后饭,饭后为女婿掏腰包,不是时下流行五块,也不是比五块高一档的十块,而是十块加十块。更让人感动的是,临走还给了帽子家两包糖块儿,给于占吉爷俩每人两盒“红红”牌的烟卷儿。看来干亭柱是实实在在地把男家头儿当成女家头儿了。
过了没几天,干亭柱就托帽子家捎信,说愿意让亲家哥定个日子,过去认认亲家那门儿。
“我这门儿啥认头?破屋烂房的。”于占吉明明刚盖了两口新屋,咋就说破屋烂房呢?这可不是哭穷,这是他对自己房子的谦称。
“他大娘,回亲家哥个信儿,明日我在家等着他。”于占吉说,“看样子是不办‘手续’不放心,那就让他早来早放心,省得夜里睡不着觉。”
还真就让于占吉猜中了,干亭柱坐下闲谈了没几句就扯到了正题上:“占吉哥,咱兄弟俩好归好,让吉光改姓干,还是红纸黑字写下来比较妥当。空口无凭,有据为证嘛。”
“大见面儿那天本想写个字据带上,可又一想,‘小见’是定两人相中相不中,‘大见’是定两家成不成。还没定下成不成就带着字据过去,我觉得早了点儿。”于占吉见干亭柱的右手有往荷包跟前靠近的迹象,忙对吉霞说,“快把笔墨拿过来。”
“用不着笔墨,我这里就有写好的。”干亭柱赶忙把手伸进了荷包。
于占吉从干亭柱手里接过一式两份的字据,“过儿单”三个字让他的脊梁沟儿“嗖”的一下,从头顶一直凉到了脚后跟儿,心里扑腾扑腾地跳个不停。扑腾也白搭,也得硬着头皮往下念:
今有于家屋子的于占吉,自愿让儿子于吉光改姓留名为干吉光,过与干家屋子的干亭柱为养老女婿,永不反悔。立字为据。
右下方“经手人”三个字后面,一上一下画有两条粗粗的横线,象两条没有腿儿的小凳子。“干亭柱”三个字早已写好,并很礼貌地让自己“坐”在下面的凳子上。于占吉想推辞也没法推辞了,小笔一挥坐在了“上座”上。
“占吉哥,你这字写得真秀气,三个字还是一笔写下来的。”干亭柱看着两份字据上的两个“于占吉”,爱不释手。不知真的是为着“于占吉”三个字不释手,还是为吉光姓“干”已成定局不释手。
不释手也不能让你全拿回去,字据理应一家一份。字好不如儿好,我教你写字你能把儿还给我吗?于占吉心里这样想着,嘴上说出来的却是:“我的名字一笔写下来易,你的名字一笔写下来难。”
干亭柱说;“我占的这三个字,后面那两个笔画多,不好连笔写。”
“你没说到点子上,你的名字一笔写下来一点也不难,只是你这个姓不能与名连笔写,因为连笔是用‘弯儿’连,”于占吉解释说,“‘干’字的竖画向右一弯和‘亭’字相连时,‘干’就有点儿象‘王’,向左一弯再往上一挑和‘亭’字相连时,‘干’就有点儿象‘于’,所以不是你不会连写,而是你的姓不允许和你的名连起来写。”
“哎哟俺那占吉哥呀,你可真会说话!”干亭柱边夸奖于占吉,边草草叠起一份字据,匆忙装进了荷包里。好象装晚了就怕于占吉撕了、抢了去似的。
“认门儿”的任务这就叫完成了吗?看了干亭柱这近乎滑稽的动作,于占吉想笑,但笑不出来。
“占吉哥,有这字据在,我看咱就不再‘换号’了。”干亭柱用商量的口气说,“反正咱俩都无上辈儿,‘换号’也是写咱俩的名字。”
于占吉说:“这字据比‘换号’来得还实在。”
酒开瓶,菜上桌。于占吉发现干亭柱的右手,又有点往荷包跟前靠近的迹象,难道荷包里还有故事吗?
“占吉哥,吉光呢?”坐在椅子上的干亭柱,半抬腚、半抻脖儿地往外看。
于占吉一下子明白了,原来“认门儿”的任务才完成了一半。他跑到天井里转着圈地喊吉光,其实他知道,吉光就在西北屋里躺着。
吉光刚进来,于占吉就说:“酒我烫热了,先给你爹满上。”
吉光听了一愣:应该先给干亭柱满才对,爹咋就让我先给他满呢?
当吉光端起酒壶往爹跟前靠近时,于占吉轻轻推了他一下说:“不是让你先给你爹满吗?”
吉光这才明白,刚才爹所说的“爹”,指的是干亭柱。
于占吉这才明白,吉光端着酒壶往他跟前凑,不是吉光的错,是自己在话语中没把两个爹明显地区分开。
在吉光满酒时,干亭柱并紧右手的中指和食指,一直伸在酒盅的旁边,虽然这两个指头离酒盅足有二指远,但在当地却把这种姿势叫做“招盅子”。满完酒把手指撤回去时叫做“撒手”——这是酒场儿上的礼节,以表示对满酒人的尊重。
于占吉说:“自家孩子满酒,还用得着招盅子干啥?撒手就行。”
干亭柱既不答话,也不撒手,只是嘻嘻地笑。
见吉光满好了酒,于占吉便说:“快给你爹端起来。”
吉光双手把酒递到干亭柱面前。
“咋不叫爹呢?”于占吉催促道,“这不正是叫爹的时候吗?”
“爹。”吉光没朝着干亭柱叫,而是朝着俩爹所面对的小饭桌儿正中叫的。
“哎——”干亭柱甜甜地应了一声,接过盅子一饮而尽,幸福的泪花随即在眼角生成,但没有落下来。
放下盅子掏荷包,于占吉估计也就十块二十块的,没想到掏出来的竟是一张百元大票。
又是泪花、又是大票,这让于占吉又是嫉妒又是高兴。嫉妒的是,自己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孩子,让干亭柱给“哄”了过去;高兴的是,孩子有干亭柱这么个新爹关爱着,自己也就放心了。
两亲家办完“交接手续”、吉光敬完酒,于占吉以为快晌午了,扶着门框往外一探头,太阳赖在东南方的上空,一点也没见动弹。天咋还这么早呢?静心一想才明白过来:签过儿单的时间是自己感觉着长,实际很短很短,不就是写了六个字吗?连吉光敬酒,一共也不过一顿饭的工夫。又加上干亭柱急着认门儿来得早,天能不早吗?天再早也得让他吃了饭再走。借这个机会了解了解他干亭柱的脾气儿,日后也好为俺那儿当当参谋。
两亲家边喝边拉,从于家屋子拉到干家屋子,从这家拉到那家,从两家的日子拉到两家的孩子,从孩子又扯到名字。干亭柱好奇地问:“占吉哥,你占个‘吉’字,为啥孩子们也占个‘吉’字?”
于占吉说:“我占‘吉’,为啥就不让孩子们占‘吉’呢?”
“不,不是这个意思。”干亭柱忙解释道,“我是说在一般情况下,父与子忌讳占同一个字。”
“这个问法就对了。刚才你那样问,我必须那样答。”于占吉说,“象大多数人的名字一样,我的名字也是我爹给起的。这名字既好听、又好写。直到孩子们到了该起大名的时候,我才发现这名字有问题:我把‘吉’字占了,给孩子们起啥名字都不‘占吉’了,我陷入了无法摆脱的苦恼之中。办法总比困难多,在吉光入学的前一天,我把四个孩子的名字全都起出来了。具体起法是;把我名字后面的‘吉’字,放到孩子们名字的中间,既能让俺爷们儿都占‘吉’,又避免了‘同辈儿’。这样起出来的名字,其‘吉’的程度只能比我高不会比我低,因为我只占了个‘吉’字,他们还可以在‘吉’字后头再加一个吉利字,于是便有了给你带去‘吉利’和‘光明’的吉光。”
“哎呀呀俺那占吉哥呀,”干亭柱双手合十、对着于占吉一个劲儿地点头,“我算是打嘴头儿到心眼儿,全都服你了。”
于占吉只是淡淡地一笑,没作声。他想,你把我儿子糊弄了去,还倒过来说服气我,是笑话我输给你了吧?嘴头儿行、心眼儿多有啥用?
“送送我的。”干亭柱指着自己骑来的那辆自行车对吉光说。
人是送下了,自行车却让吉光骑回来了。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得了辆八成新的自行车,并没提起吉光的情绪,回来后又钻进西北屋里躺下了。大白天价总不能光躺着啊!于占吉让吉亮把他叫了过来:“我咋看着你有点儿不高兴啊?”
话刚出口就后悔了——今日他能高兴吗?于占吉一时没有了下言,于是便明知故问:“你相没相中小绵?”
吉光说:“相中了。”
“相中她这个家庭了吗?”
“相中了。”
“相中你丈人、丈母娘了吗?”
“也相中了。”
“那你不就全相中了?”
“不,”吉光大声说,“我没相中他这个姓。”
“既是相中了家庭,相中了自家那个人,就不要在乎他这个姓了。”于占吉说,“其实这两个姓的区别也不是很大,姓干的和姓于的比,不就少了一个钩儿吗?”
“我不愿意少这个钩儿,我不愿意改姓。”吉光的声音和刚才差不多高,因是跺着脚说的,让人产生出一种比刚才高很多的错觉。
“吉光啊,姓只不过是个记号。”于占吉劝解他说,“姓啥不都一样?”
“说得倒轻巧,都一样的话你去姓干的!”吉光一摔门子不见了人影。
“你看你看,你看你这孩子咋这么不会说话呀!”于占吉对着半掩半开的屋门说,“谁家那孩子敢这样道他爹?真让我惯得没大没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