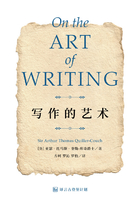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饱受百年战乱之苦的中国人,不论士农工商,还是海外侨胞,无不人心思安,都以极其饱满的热情,投身到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中去。人们将自己的工作热情与成果,自觉地和新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和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事印度语言文学研究的学者当然也不例外。1950年代,中国和印度同为“五项原则”的发起国,相同的历史和命运将两国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在“中印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声中,中国师生对学习、研究印度语言文化抱着一种别样的心情。这种别样心情和那个时代“大干快上”的精神相结合,为新中国的印度学研究,在语言和文学翻译上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印地语的教学与研究,是从新中国成立后走上正轨的。到1958年,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印地语教研室,“在党的三面红旗指引下,在兄弟单位的大力协作下,大搞群众运动,编出了这部辞典”。(《印地语—汉语辞典》1972年重印说明)
由语言到文学有一个发展过程。1950—1970年,印度文学的翻译,以梵语文学翻译为主,一些重要的现代文学作品则从英语译本被转译成汉语。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金鼎汉以“索纳”为笔名翻译的普列姆昌德的中篇小说《妮摩拉》,这是中国学者从印地语翻译印度文学作品的开始。由此,翻译泰戈尔和普列姆昌德的作品,逐渐由英译汉转为从孟拉语、印地语直接译为汉语,开启了一个从印度民族语言汉译文学作品的新时代,出现了“泰戈尔热”、“普列姆昌德热”。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对印度文学的翻译、研究阵容中,以季羡林、徐梵澄、金克木三驾马车的声势最为显赫。他们的研究成果互相支持,互相发明,在中国印度学界呈品字结构,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一道奇丽景观。
第一节 季羡林从语言到文学研究
季羡林(1911—2009年),中国当代大学者。范曾对季羡林有宏观而精准的评价,认为“季羡林是一位博雅的仁者,其气深矣,其养邃矣,于是他成了20世纪最杰出的几位人文学者之一”。他说:“我们不妨将季羡林先生的学术著作视为那磅礴的大山,其中必有学术所不可或缺的苛酷而严正的考据和印证,其对原始佛教语言的追溯探讨,对玄奘《大唐西域记》的校注、对《列子》成书年代的推断、对吐火罗语文字涵义的破译,甚至季羡林先生的翻译文学《罗摩衍那》和《沙恭达罗》,都需付出季先生穷年累月的辛劳。那林林总总的著述,令人望而兴叹,直如我们登山之时,尽管觉得山势峻美,但也觉得高不可攀。”[1]综观季羡林的学术人生,从语言走向文学,是他的极为重要的里程。而从语言走向文学的转变,恰恰是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完成的。这一转变对季羡林本人和印度学研究,甚至对中国整个当代文化学术,都有重要意义。如果没有这种转变,中国只有作为印度古代语言学家的季羡林,而不会有作为印度梵语文学翻译家、研究专家的季羡林,更不会有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几位人文学者之一”的季羡林。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读完四年西洋文学系,又在母校济南高中任教一年,考取了清华大学和德国的交换留学生。1935年10月31日,他从柏林来到哥廷根,一住就是十年。这样,就决定了季羡林的梵文人生。他说,如果当年他去了别的地方,“我不但认识不了母克(Sieg)教授和瓦尔德施米特(Waldschmidt)教授,就连梵文和巴利文也不会去学。这样一个季羡林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那只有天知道了”。偶然决定必然。由于偶然机会,季羡林来到哥廷根大学,走上了研究印度梵文、巴利文和印度文学的必然道路。
1946年,季羡林回国被胡适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和东方语言系主任。当时,抗战刚结束,国共内战又起,季羡林所学梵文、巴利文无法施展。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天下大局已定,季羡林的印度学研究才真正步入正轨。季羡林的博士论文题为《〈大事〉颂中限定动词的变化》(Die Konjugation desfiniten Verlourns in dan Gāthas des Mahavasis),是一个研究早期佛教语言的题目。后来,围绕印度佛教语言,季羡林的研究出现了三次高潮。他自己说:“当年除了博士论文外,我还写了两篇比较重要的论文,一篇是讲不定过去时的,一篇讲-am>o,u。都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此时还写了一篇关于解读吐火罗文的文章。”[2]季羡林说:“这算是我研究佛教梵语的第一次高潮。”[3]
1956年季羡林发表《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58年他发表《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4年他又发表两篇文章《中世纪印度雅利安语二题》和《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季羡林很看重这四篇文章,说:“可以算是第二次高潮吧!”[4]并且说:“我相信,在今后图书资料条件日益改善的情况下,必将有一个第三次高潮出现,而且是一个高于前两次的最高的高潮。”[5]1970年代,中国新疆出土了吐火罗文A(焉耆语)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集中精力,把全部残卷译成英文……即使我再谦虚,我也只能说,在当前国际吐火罗研究最前沿上,中国已经有了位置。”[6]季羡林的研究成果在西方的刊物上发表,并以《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中英文合本的形式,收在《季羡林文集》第11卷中。[7]季羡林在耄耋之年完成的这些成果,“说其是奇迹,是破天荒之作,是中外翻译史上的幸事,一点也不过分”。[8]这不正是比前两次更高的第三次高潮吗?
季羡林自己并没有说第三次高潮的到来。但是,从他说话的语气中,完全可以看出他对第三次高潮的到来充满信心,预言是一个高于前两次的“最高的高潮”。在季羡林的所有著述中,如此信心满满的语言,是极其少见的。这说明,在1980年代初,接触到了吐火罗文A(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的季羡林,已经对第三个高潮的出现,充满着预期。季羡林在《〈季羡林文集·第十一卷〉自序》中写道:“了解我们这一行行情的人都知道,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的学者中,谁要是从新疆或其他有关地点或机构,拿到一张半张的出土残卷,都会视同珙璧,大写其文章……我何独不然?”[9]季羡林知道任务艰难,他“硬着头皮”接受了下来。用十几年的时间,进行译释研究,用中英文在国内外刊物发展,在学术圈内轰动一时。
季羡林对中国学术的贡献,无论怎样评价,他对佛教语言研究的贡献,总是第一位的。
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对季羡林来说是从佛教语言到文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吐火罗语是我国新疆的一种语言,又以文献出土地称焉耆语,从语言学上讲它属于印欧语系。季羡林译释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是一个文学作品,但是在译释工作中最见功夫的,是季羡林的语言功底。当然,在1950年代,季羡林翻译研究印度文学已经成绩斐然。这说明,佛教语言研究和印度文学的翻译研究,在季羡林这里是长期并行不悖的。只是在某一时期内有所侧重而已。但是,如果从宏观上看,季羡林的研究重心是由语言朝着文学方向逐步发展的。
对印度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是季羡林的又一大贡献。郁龙余在《中国印度文学交流史》中这样说:“中国印度之间的文学交流,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东汉以后的中国文学,实际上是中国先秦、秦汉文学和印度古代文学(以佛教传播为主要渠道)相融合的产物。由于宗教的排他性,印度文学的主流(吠陀教、印度教)作品,并没有传播到中国来,即使有,也只是夹杂在汉译佛经中的吉光片羽。这种局面,到近代被慢慢打破。但是,早期的印度文学的翻译,大多数由英语、法语等译本转译而来。真正从梵文原典将印度文学的主流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并进行学术研究的,季羡林是第一大家。”[10]
季羡林的译作主要分两大部分,梵文译作和其他语种的译作。梵文译作收集在《季羡林全集》第20卷和第22至29卷中,其他语种的译作(包括德文译作、英文译作和由英文转译的作品)收集在第21卷中。第22至29卷是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开译时间是1973年,及译成则过了十年时间。季羡林在《〈罗摩衍那〉译后记》中说:“时间经过了十年,我听过三千多次晨鸡的鸣声,把眼睛熬红过无数次,经过了多次心情的波动,终于把书译完了。”[11]译印度古代史诗之难,可见一斑。
1950年代至1970年代,季羡林的梵文译作主要是《沙恭达罗》、《五卷书》、《优哩婆湿》,还包括《十王子传》选译,《佛本生故事选译》和《念诵甘露》。
第二节 徐梵澄静谧而非凡的人生
徐梵澄(1909—2000年),原名琥,谱名诗荃,字季海,湖南长沙人。他幼年得名师启蒙,“旧学甚笃”。年轻时游于鲁迅门下,后留学德国,主攻哲学与艺术史。回国后,有规模地翻译了尼采的著作。1945年底参加中印交流,先后执教于泰戈尔国际大学和室利·阿罗频多学院30余年。1978年,70岁高龄皓首还乡。他通晓多种语言,尤其擅长梵文和德文,对中印西三大文明学术都有深入研究,“数十年来治精神哲学”,“锲而不舍”。[12]
2005年,16卷《徐梵澄文集》出版,共收录了600多万字,四个方面的学术作品:一为尼采主要著作的翻译;二为印度古代典籍如《奥义书》和《薄伽梵歌》的系统翻译和近世圣哲阿罗频多思想的系统译介;三为以英文著、译述向世界介绍中国古代思想和学术;四为以精神哲学的进路诠释中国古代思想。
在中印文化学术交流上,徐梵澄的贡献主要有两个,“一是传播中国学术菁华,二是汉译印度文学哲学经典”。[13]他自己的文字,即集中反映其思想、观点的主要在各译著的序跋里,而写于1971年的《玄理参同》在形式上也已不是单纯的译介。
纵观徐梵澄数十年的翻译生涯,费时最多,用力最勤,影响最大的译作,当为《五十奥义书》。
徐梵澄翻译奥义书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他深深了解奥义书在印度乃至世界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印度诸宗各派,无论“有”宗、“无”宗,胜论、数论、瑜伽、因明或者顺世、佛教、耆那皆自此一渊源衍出,起盛衰没,物极则变。但吠檀多学迄今两千余年未亡,晚近自印度独立,其知识人士,莫不以吠檀多学者自居。研究印度思想、哲学、宗教,“撷此一线索而纠结已解,则上下通流,上窥四《吠陀》,诸《婆罗门书》及《森林书》,下瞰六派哲学及今之印度教,鲜有不贯穿者矣”。[14]他追溯奥义书的流传,早在16世纪,已被译为波斯文,后陆续被译为法文、拉丁文、英文、德文等各个版本,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也深受其影响,曾在《世界为意志与想象》一书的序言中向奥义书“三致意焉”。[15]
其次,他要破除中印间的文化隔阂与误解,增强彼此间的交流,开拓国人视野。长久以来,“吾国佛教徒知印度有佛教而无其他”,而“彼印度人士,则以为吾国舍自彼所得之佛教而外,亦无其他。民族间之误解,亦莫大乎是”。[16]实际,印度历史上教派林立,各种思想层出不穷,而今佛教早已湮灭,印度教独大。奥义书被“五印奉为宝典,吾国久已宜知。文化价值难量,象寄菁英稍见,其可以隶之《杂藏》,博我书林”。[17]
复次,他译《奥义书》,受阿罗频多的影响,当是应有之义。[18]他首译《由谁书》和《伊莎书》,并附室利·阿罗频多对此二书的疏释,某些地方他沿着阿氏的疏释补以自己的注解。每书前加引言,或论其大旨,考辨源流;或寻词义版本,析辞章体制;或言明翻译原则,补足相关背景。尽量给读者还原更丰盈、更明朗通畅的“吠檀多”。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奥义书义理宏富,属于内学。吠陀的思想总的来说是外向的,充满自然意识,在奥义书中才开始返观内照,对人的内心世界进行探寻。印度人远祖信鬼神好祀事。《梨俱吠陀》为祝颂天神之诗,《娑摩吠陀》是颂神歌曲集,《夜柔吠陀》阐释礼仪法规,《阿闼婆吠陀》是巫术禁忌咒语之类。《梵书》是婆罗门阶层解释“四吠陀”颂诗的文献,也多是形式主义的祭祀手册。《森林书》的作者厌离世俗祭祀方式,遁入山林,静观默想,探讨祭祀的神秘意义,更注重内在的精神祭祀。奥义书最早集中探讨世界的终极原因和人的本质,“虽然排在梵书之后,但它们的主题思想并不是梵书的继续或者总结,而是展现对宇宙人生的另一种思路”。[19]此一转变使奥义书在印度宗教与哲学发展中产生了极重大的意义:成为“后世诸宗各派之祖”,“信宇宙人生之理有在于是”。[20]在其思想基础上产生了吠檀多派,是古印度六派哲学中影响最大的一派。
在印度文化史上,《薄伽梵歌》是文学经典,是哲学经典,亦是印度教的根本宝典。它在印度现代思想中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印度教之有《薄伽梵歌》,犹伊斯兰教之有《可兰经》,基督教之有《新旧约圣经》也。”[21]继奥义书时期后,印度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哲学派别和宗教团体,它们的基本观点都或多或少导源于奥义书。基本为两类:一是继承维护婆罗门教传统的,主要有六家[22],即所谓正统的六派哲学;一是批判和反对婆罗门教传统的,称为非正统哲学,佛教哲学便属于后者。六派哲学中的后弥曼差论正是吠檀多学派,它先后产生了两部重要的吠檀多哲学著作:《薄伽梵歌》和《梵经》。因此,奥义书、《薄伽梵歌》和《梵经》被奉为印度教的三大圣典,也是吠檀多哲学的三支柱。
《薄伽梵歌》是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第六篇《毗湿奴篇》的一个插话。背景在战场上,王子阿周那和他的御车兼导师克里希那(为大神毗湿奴在人间的化身)之间展开了关于宗教哲学的问答。[23]很多研究者都认为这一故事只是作者借题发挥,抒发思想的艺术形式。[24]徐梵澄早在1950年代即持此见:“撰者之意,盖假一历史事迹,以抒其精神信念与宗教热忱。”[25]《薄伽梵歌》对世界及其本源的看法紧紧承接奥义书中的传统,包括“梵我同一”、“轮回业报”、外持苦行、内修瑜伽以得解脱等理论,同时又吸收了其他各派的观点。
徐梵澄翻译《薄伽梵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那之前,已有学者比较过其与《圣经》、《可兰经》的相同处。[26]剥去宗教的外衣,它们同与精神哲学相关联。在他看来:
“世间,一人也;古今,一理也,至道又奚有二?江汉朝宗于海,人类进化必有所诣,九流百家必有所归,奚其归?曰:归至道!如何诣?曰内觉。”[27]
文化学术与人类社会一样,有其生命的变化轨迹,且两者的盛衰起伏互为因果。“求世界大同,必先有学术之会通;学术之会通,在于义理之互证。在义理上既得契合,在思想上乃可和谐。”[28]而“学术无论新、旧,唯求其是”。[29]所以尽管存在地域、时代、语文、体系之殊异,仍有会通的可能。如何会通,首重证悟,即“内觉”。现世,“学术昌明,分科繁细,重外轻内,枝叶深芜,而人生大端,或昧略矣”。[30]精神真理是身心性命之学,“由内中修为醒悟而得”,大足以淑世而成化,小之足以善生而尽年,所以一直为徐梵澄所重视、关注、研究,数十年不辍。
室利·阿罗频多是现代印度精神哲学的最大代表。作为思想大家,阿氏涉猎的领域广泛,著述丰赡,在哲学、文化、瑜伽、文学理论、诗歌创作等方面都有不俗的成果。其百年诞辰纪念时,已出版作品集三十巨册。徐梵澄主要翻译他在哲学和瑜伽方面的作品,他高度赞誉阿氏“综合自韦檀陀(即今译吠檀多)以下之精神哲学而集其大成”,“超出了韦檀多学的范围,度越前古”。[31]阿氏以“精神进化论”和“整体瑜伽论”闻名于世。他一方面承袭了传统哲学的基本原理——吠檀多一元论,认为“梵”是世界的本体,“万物起源于梵,存在于梵,并还原于梵”。同时“梵”外现众相,构成世界。世界又有物质和精神两层,分为若干等级,从低到高大致为:物质、生命、心思、超心思,梵为最高等级。[32]梵为超验的圣位,前三者均为经验的凡位,而超心思则是承上启下、引下向上的中间范畴。“梵”(纯精神)先从最高位逐层下降,产生生命、物质,所以万物都隐藏梵性。后天人的精神进化过程是“梵”摆脱物质和低等思智上升到绝对精神(梵界)的过程。通过“超心思”达到精神进化的人是为超人,超人用其无限的智慧和力量照亮启发无知的人,如此实现社会及全人类的精神化。这一过程要依赖“整体瑜伽”的修行。
阿罗频多综合了传统瑜伽的菁华部分,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整体瑜伽。“视整个人生为瑜伽”,其目标不为“出离世界与人生而入‘涅槃’或‘天’国,乃在于转变生命和存在”。[33]其方法“在旧的智识,敬爱,行业三大瑜伽中,特重‘行业’,要工作,无论高低,由工作即‘行业’而见道,空心静坐不为功”。[34]把理论(智识)和实践(行业)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强调在内心直觉上下功夫,通过“超心思”的证悟把万物的精神本质还原出来,亲证“梵”的存在。同时,阿氏不排斥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吸收其为自己的理论作注解。他高度关注现代印度社会生活,尽可能使其理论应用于解答当代的世界政治问题。总之,他丰富发展了传统吠檀多哲学,使之呈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形态。徐梵澄评价阿罗频多:“可说一手将整个印度民族提高了,使全世界认识此民族尚有此学术思想,尚有此人。”[35]
反之,阿罗频多的思想对于徐梵澄的影响是显而易见和相当深刻的。他称阿氏是当代印度的精神哲学大师。而徐梵澄最锲而不舍的,正是“数十年来所治之精神哲学”。[36]他很早就显露出倾心于“内学”研究的倾向,喜欢佛学,读《大藏经》;留学德国,浸染于哲学圣地,翻译尼采,逻辑、理智、情感、意志、信仰这些精神范畴可能在他脑中反复萦绕甚至搏斗过;客居印度——世界又一哲学源地,在轻视外在物质、崇尚内在精神的印度文化哲学中继续探寻;遇到阿罗频多,他的研究视线清晰起来,与过往的各种积累和自己的心之所系相叠合,产生了一个确定不移的名字——精神哲学。反观他毕生译作、著述,皆未离开这一主题。汉译印度作品方面,以哲学经典居多。从奥义书到《薄伽梵歌》以至阿罗频多的著作,都是印度的“内学”大典,脉络清晰可辨,思想一脉相承。用英文向世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也未尝离开此领域,这在下文中会有详细介绍。那么,让徐梵澄所集中心力的“精神哲学”到底关涉些什么?
精神哲学(Philosophy of Mind)一词在现代常见,曾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西方哲学的核心课题。涉及形而上、认识论和道德领域,分为若干部分,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总体上对精神的哲学认识,二是对精神哲学各特殊部分的研究。前者包括精神的本性、精神同他物的关系以及精神的活动机制等,后者涉及精神活动的各种具体概念,如思维、记忆、目的、意志、高兴、痛苦、梦境等。如果说在与阿罗频多相遇之前,他的翻译和学术方向尚且模糊的话,那么译介阿氏作品时,他已经非常清晰地在序跋中多次用到“精神哲学”一词。他在成书于1973年的《玄理参同》之序言里说:
通常说精神哲学,总是与物质科学对举;但从纯粹精神哲学的立场说,不是精神与物质为二元;而是精神将物质包举,以成其一元之多元。主旨是探讨宇宙和人生的真理,搜求至一切知识和学术的根源,其主体甚至超出思智以上,它立于各个文明系统之顶级。其盛、衰、起、伏,实与各国家、民族之盛、衰、起、伏息息相关。
此处不论其观点的合理性与否。只看与阿罗频多学说的契合之处:一,认为世界的本体为精神,这与吠檀多一元论无二;二,主张精神哲学的旨归是宇宙人生,为此岸的现实生活,正是阿氏所提倡的;三,试图通过精神哲学的作用影响更大的团体——民族和国家。
1994年出版的《陆王学述》的后序以及第三节再次对精神哲学的相关问题做了专门阐述。他认为精神哲学其领域很广,“本自无边,其出发乃自心源,而心源无尽”。[37]精神哲学顾名思义是研究精神的哲学,那么何谓精神?他说,精神一词涵义深广,很难用一二语下定义,就质素而言,它是指对人的生命力的研究,包括生理体、思维心、情感心和性灵。
这儿有两个问题需要厘清:一是精神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二是精神哲学与纯粹思辨哲学的关系。对于第一个问题,他肯定许多的精神真理涵藏于宗教中,比如对宇宙人生最高真理的探寻;但精神哲学本身与宗教有天渊之别,它没有宗教之仪法、迷信甚至虚伪、妄诞的层层包裹,所以宗教的玄虚不适用于它。第二个问题,精神哲学较纯粹思辨哲学的范围更大,思智只是属于精神之一部分。故而,纯粹思辨哲学的方法也不全适用于精神哲学。那么,这一修为或者说研究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完成呢?
思智属逻辑层面,方法如归纳、推理、演绎等,可用语言表达;而精神出乎思智以外有待开发的东西很多,有时语言文字都力所不逮。正像奥义书中深邃的精神无法用逻辑思维的利器尽数丈量一样,精神“真理原是由内中修为省悟而得”,“首重证悟”[38],“学者犹当恢宏其心以证会之,然后明其真”。[39]精神真理具有普遍性,凡人自知或不自知皆多多少少地生活其中,禀赋有此灵、此心、此性,此情、此体、此气,中西古今不异。[40]对精神真理的实践,思维不如观照,观照不如体验。通过不断反观修正自己的内心,与亘古如斯的真理相遇,达到如一的境界。他曾比较获得知识的几种途径,认为“同一知”最上最佳,“同情之”居次,“推理之”又次,“识感知”最不可靠,但又绝不可弃。[41]虽然证悟往往为思智、语文所不及,仍当讲明,有可表现,不能遽弃之。总之,精神哲学应当内外交修,内重证悟,外倚思智、语言文字。
徐梵澄主张精神哲学的旨归是现实生活,小则个人从中得到精神助益,完成身心修为的转化。大到改善社会,推进文明进步。他希望从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哲学与宗教原理中汲取养分重建中国的精神哲学。在古希腊罗马,印度、中国三大文明系统中,印度一系的宗教色彩最浓,有丰富的精神哲学资源可供借鉴。他不遗余力地翻译各种印度文化经典当属意于此。西方从各种维度研究精神哲学亦有几百年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无与此相关的范畴呢?
除了翻译印度哲学经典外,他还从梵文翻译出了一部印度古代的文学经典——《行云使者》(Meghadūta)(也有的译作《云使》,以下简称《云使》)。
《云使》作者迦梨陀娑(Kālidāsa),“是印度中古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诗人和剧作家”。[42]他生卒年不详,身世无信史可考,但才华卓越,作品众多。其代表作长篇抒情诗《云使》和戏剧《沙恭达罗》为古今公认的梵语文学的高峰。
《云使》在印度文学史上地位不凡,是第一部抒情长诗,也代表了“印度古代长篇抒情诗的最高艺术成就”。[43]《云使》之后印度出现了“信使诗热”,模仿之作不断,成一代诗风。该诗被翻译到欧洲后,曾得到浪漫主义诗人的欣赏。《云使》讲述的是被贬谪的药叉在山中思念妻子,托一片行云将自己的一腔思恋带给妻子的故事,突出夫妻之间真挚的爱情。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而徐梵澄本人也极擅长诗歌创作,鲁迅曾评价他“诗甚佳”。他自己也留有旧体诗七百余篇,结集为《蓬屋诗存》。他有诗人敏锐的感知力和审美判断,认为《云使》“词义清新,文字简洁”,“音节浏漓顿挫,附义丰多”。[44]同时,他也是个论诗的行家里手,1996年连续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蓬屋说诗》,所论别出心裁,独具真知灼见。《云使》序言中他比较中印诗歌传统,看到“诗,华梵诚有闲矣”。中国古诗自来重“言志”,即使抒情也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仪”,“乐而不淫,哀而不衰”,有所怨怼则需“婉而多讽”,“寄托遥深”。虽然到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纯粹直白的抒发一己之情在中国诗歌史乃至整个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始终都不占主导地位。而《云使》“无所寄托,舍抒情而外,他无胜义”。作为诗人的徐梵澄当然知道“性情真际”之于诗歌的重要性,他论诗的最关切处也是“性情”,但他对“低回三叹于天神之敬祈祷,夜叉非类荒忘欲乐”的描写仍不敢苟同。所以翻译时去粗存精,删削不少。
《云使》的翻译,用的是徐梵澄擅长的古体诗,“七言五言”、“巧构连连”。[45]他明通诗理,了解诗的“言外之意,义内之象,旋律之美,回味之长,风神之秀,多无可译述”。至于“神来之笔,灵感之言”更非语言传统悬隔的华语梵文所能尽数传达,故而“尽取原著灭裂之,投入熔炉,重加锻铸”。这不是直译,也不是意译,而是“创译”。创译既需要译者对于原著精神的深入玩味,又要深厚的表达功力。“创译,只有少数大家可以成功,寻常舌人象胥不可妄为。否则,必然沦为曲译,误译。”[46]
纵观徐梵澄的一生,他“未尝离学术界一步”。[47]作为文化的传播者、沟通者,他通过双向翻译、介绍各种哲学文化经典,开拓国人对于印度文化的视野,同时把中国传统文化菁华传播出去。以精神哲学为研究核心,自觉比较不同文化体系下,特别是中国、印度文化中的精神哲学内容,试图发现其共通点,以为借鉴,希望找到影响人类进步的精神因素。他有广阔的世界文化的视野,思想中始终隐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晚年回归儒学,他曾说:“中国文化真好。儒家真好。”[48]
“总之,这个对很多人来说也许还陌生的徐梵澄,大体就是这样的人物。当代学界的所有现成框架都不足或无法用以规范他。你可以在他头上安上这个家那个家,然而,这对他都不重要。”[49]
第三节 金克木及《梵语文学史》
金克木(1912—2000年)是中国著名的梵语文学家、诗人、翻译家,他学贯中西,知兼古今,著述等身。说他是梵语文学家,因为他多年来致力于梵语文学和印度文化的研究,撰写了《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等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著。说他是翻译家,因为他通晓数种外语,译有《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印度古诗选》、《伐致呵利三百咏》、《我的童年》、《云使》等著作。说他是诗人、杂家,因为他在报刊发表了大量随笔,古今中外、诗词小说、历史风俗、读书论道,无所不谈,文章言简意赅、活泼有趣、沉静而厚重。他一生散文诗集丰硕,除早年的诗集《蝙蝠集》、散文集《天竺旧事》、小说集《难忘的影子》之外,还有《书城独白》、《长短集芦》、《金克木小品》、《燕啄春泥》、《末班车》、《槛外人语》、《蜗角古今谈》、《梵佛探》等。据《中华读书报》刊文记载,“金克木先生生前一直关心和支持本报的工作,从1994年本报试刊时起,就开始为本报撰写专栏文章,是在本报发表文章最多的著名学者”。[50]余杰曾表达了他对先生的喜爱之情:“老先生们的文章,我只喜欢金克木一个人的,喜欢里面的智慧和幽默,生机和顽皮,金先生该是老顽童一流的人物,故老来仍能作好文章。”[51]
金克木一生,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是:“儿童的人间:做梦,做诗。少壮的人间:苦斗,沉思。”然而,在学者们的心中,他留给后学的却是激情、敏锐,和超凡的学术智慧成果。凡是和金克木有过接触的人,无不对他的博学、健谈、敏锐留下深刻的印象。多数学者称他为专家、“智者”[52],可他却自谦是“杂家”[53],他说:“我不是专家,也许可称杂家,是摆地摊子的,零卖一点杂货。我什么都想学,什么也没学好,谈不上专。”[54]
一、金克木与印度文学的译介
中国对印度文学的翻译已有近百年的历史,金克木是翻译和推介印度文学的先锋,在翻译印度诗歌方面做出巨大贡献。他不仅为后学提供了学习印度文学文化原典的中文资料,而且为后来翻译印度文学的译者打开了梵语翻译的窍门。金克木翻译和研究印度文学的品类包括诗歌、诗论两个方面,译著和专著有《伐致呵利三百咏》、《云使》、《通俗天文学》、《甘地论》、《我的童年》、《印度古诗选》、《莎维德丽》、《梵语文学史》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名气的诗人,金克木对文学语言,特别是诗歌语言韵味的把握,在印度文学翻译中充分表现出来,并发挥得淋漓尽致。下面简说金克木对印度文学翻译评价的贡献。
(一)翻译的经典性
1956年,金克木先生译出印度古代抒情诗诗人迦梨陀娑的作品《云使》,该书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单行本,后来收进《印度古诗选》。“译文所根据的是摩利那特本,同时共参看了六种铅印版本。现在只译出公认为原作的一百一十五节。”[55]关于《云使》的翻译,金先生在题为《印度的伟大诗人迦梨陀娑》的译本序言中说:“他(迦梨陀娑)的译本非常难译;恐怕没有一部语言的翻译能够传达吟咏原作时的情调。例如《云使》通篇用了一种‘缓进’调,一节六十八音,就是以两个三十四音构成一联,其中十七音相当于现在诗的一行,由此表现出夏季雨云怀着电光雷声缓缓前进的情调;这种梵语所特有表现力是不能移植到现代语言中来的。”[56]迄今为止,《云使》的汉译本有三个,分别出自金克木先生和徐梵澄先生的译本,还有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罗鸿译的全新版本。罗鸿在译本前言赞扬金先生的译本:“采用了摩利那特的梵文注释本为底本。这个译本清新自然,非常忠实于原文,只对诗中的专有名词作了一些简化的处理。”[57]王向远援引《云使》第82、89节诗歌译文评价金克木的翻译水平:“现在看来,在中国的印度文学翻译中,金克木译《云使》是少见的颇为成功的例子。金克木本人就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的诗人,诗人译诗,最为合适。从译文中可以看出,金克木具有非常敏锐的语言审美感受与表现能力,他用标准的现代汉语,很好地、近乎完美地表现了他所说的原诗的‘缓进调’,既保留了原诗的印度风味,也体现出现代汉语诗意特征,读起来酣畅、圆润、流丽。”[58]他认为金克木的译文之所以能长风行云,诗趣盎然,是因为将“译文的风格与原文的风格、译文的形式与原文的形式,达成了一种高度的和谐,从而进入了‘化境’”。[59]1998年,台湾的广阳译学出版社出版了赖显邦根据英译本翻译的《云使》。译者在《译后序》中说:“中国大陆金克木先生曾译过此书,其译文比英译本保有更多诗趣,也比英文本更符合梵文的句法顺序。”[60]黄宝生也评价说:“金先生是译诗高手……我曾对照梵文读过《云使》译本,对金先生的翻译艺术由衷钦佩。只是中国的翻译理论家们不谙梵语,无法真切体认。我总惋惜金先生翻译的梵语诗歌不够多。梵语诗库中的一些珍品,惟有金先生这样的译笔才能胜任,也不至于辜负印度古代诗人的智慧和才华。”[61]以上赞誉可见金克木先生《云使》译本的经典性。
(二)诗意的翻译法
1982年,金克木翻译出版了一部在印度流传很久、很广的梵语短诗集《伐致呵利三百咏》(人民文学出版社)。金克木的译本是根据印度学者高善必的“精校本”定本翻译的,所译出的是高善必认为的确切无疑的最古的二百首诗。早在1947年,金克木就译出了《三百咏》中的69首,发表于《文学杂志》1947年第6期。金克木的译诗原则是尽可能地恢复原诗句的格调,“依照原文的词句甚至其先后序列,力求不加增减,但在汉语的选词造句和文体上则又求像古代人的诗,不只是用现代汉语述意”。[62]可见,金克木先生是诗人和学者的结合,这种译诗能力不是人人能及的。
(三)选译本能力强
1984年,金克木先生的《印度古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面世。这本译诗集所选的印度古诗范围约在一千年以前,当时通行于印度的文化语言称为梵语,另有些“俗语”,例如佛教文献中用到的巴利语。书中的诗是从吠陀语、梵语(或称古典梵语)、巴利语的文学作品中选出来的。金克木对所选的古诗也有自己的标准,“并不是在印度古诗中选出最好的精华,而是选其几个重要方面的一些例子。由此‘一斑’还不足以见‘全豹’”,但是印度古诗的面貌特征也可由此见其大概。这些也不能说是代表,只能说是样品,更准确些说,只是诗史的抽样”。[63]
《印度古诗选》所译出的古诗虽然数量很少,但编选的诗歌范围包括了印度诗歌重要的几个方面,比如印度最古文献《吠陀》的诗篇20首,蜚声世界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著名插话《莎维德丽》,巴利语佛教经典之一《法句经》中15节文学性较强的诗歌,《伐致诃利三百咏》中21首可见文人作的体式的诗歌,模仿《五卷书》的《嘉言集》中的23节格言诗,还有《妙语集》中的14首具有代表性的晚期连佛教徒也欣赏的抒情诗。以上诗篇中,其中《吠陀本集》在此之前我国一直未有翻译,金克木先生的翻译对我国研究印度神话、宗教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1987年,他和几位学生赵国华、席必庄、郭良鋆合作,翻译出版了《摩诃婆罗多插话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翻译了《摩诃婆罗多》的“初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摩诃婆罗多插话选》的翻译依据的本子是所谓“精校本”。“本世纪有一位印度学者苏克坦迦,集合印度和外国的一些学者,根据现存的各种写本,校勘出了这个本子。”[64]这本选集所选插话共15篇,虽然不能包罗《摩诃婆罗多》中所有优秀的插话,但它给后来翻译全篇史诗的译者提供了翻译的方法和示范,正如他自己所说:“希望这15篇插话可以帮助读者增加一点对邻邦印度最流行的古代文学的知识,也扩大一点文学的视野。”1993年,《摩诃婆罗多》第1卷出版,这卷前四章为金克木亲自翻译,2005年,该书六卷全译本在黄宝生主持下出版,尽管“金克木虽没有参与翻译,但此前他所做的工作,成为《摩诃婆罗多》成功翻译的有利条件”。[65]
综上可见,金克木关于印度学方面著作译文的翻译不仅水平高,而且达到“神似”与“形似”相结合的状态,这都缘于他优秀的国学功底和对印度文学的熟悉程度。
二、金克木的其他梵学造诣
1941年金克木经缅甸到印度,任一家中文报纸编辑,同时学习印地语和梵语,后到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佛学,跟随印度著名学者乔赏弥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从此走上梵学研究之路。他的学生郭良鋆在回忆中谈道:“金克木先生四十年代游学印度五年,按印度传统的口耳传授方式,拜名师乔赏弥学习梵文、巴利文。”[66]“有因必有果,金公由于少年到壮年奠定了广泛而扎实的好学基础,所以日后必然获得了学术上的卓越成就和丰硕成果。”[67]
金克木研究梵学的成果集中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及1980年代出版,论文集和专著有《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等,其中1999年出版的《梵竺庐集》尤为盛名。《梵竺庐集》分三卷,甲卷《梵语文学史》,乙卷《天竺诗文》,丙卷《梵佛探》。2002年又出版《印度文化余论——〈梵竺庐集〉补编》以集合金克木先生另10篇有关印度文化的文章。
在印度语言、哲学和佛教研究方面,金克木研究颇丰。他先后发表过《论“有分识”》、《试论梵语中的“有—存在”》等一批论文。这些文章,后来大多收入他出版的《印度文化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旧学新知集》(三联书店,1991年)、《比较文化论集》(三联书店,1984年)几种书中。1981年在《语言学论丛》上发表的《梵语语法〈波你尼经〉》尤为突出。这是中国第一次详细介绍古代印度最著名的梵文文法家波你尼的《八章书》的文章。
在金克木的散文中,有不少和梵学研究有密切关系的著作,如《天竺旧事》、《陈寅恪遗札后记》、《〈心经〉现代一解》等等。《天竺旧事》是金克木回忆性的艺术散文集。全书由十五篇散文构成,记述了当年他在印度的所见所闻,从不同角度将一个绚烂多姿的印度呈现了出来。金克木的文笔清秀,寓意深刻,颇具韵味。“一本《天竺旧事》把人们带回到20世纪40年代的印度,不但给人以美的享受,使人增长见识,而且给人们留下了印度文化方面的宝贵资料。”[68]
除此之外,金克木先生在中外文化交流史、文学史、佛学、美学、比较文学、翻译、诗歌等方面也颇有建树,如《艺术科学丛谈》、《比较文化论集》、《中印人民友谊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等。翻译作品还有《通俗天文学》、《甘地论》、《高卢日尔曼风俗记》、《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等。2011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以金克木生前三十余部已出版的专著(包括译作)或自编文集(绝大部分为旧作,重编的几部文集除外)为主体的《金克木集》,其中关于印度文学翻译、印度文学评论和印度诗学理论的作品分别收录于第2卷、第3卷和第7卷中,该文集的出版为我们全方位地了解远见卓识的金克木先生的印度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同时还是中国印度学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
三、金克木的《梵语文学史》
金克木研究印度文学的成果主要集中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及1980年代出版,其中金克木的《梵语文学史》是梵语文学研究的巅峰之作,也是一部影响众多学者和读者的教科书。它就像是码头上的灯塔,永远指引着年轻一辈航行前进。
(一)《梵语文学史》是中国梵语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本书是学习印度文学的必读课本,最初是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度语言文学专业使用的教材。1963年金克木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次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8年再版,1999年收入《梵竺庐集》甲卷,2011年收入《金克木集》。本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编“《吠陀本集》时代”(原始社会解体和阶级社会形成时期的文学),介绍了《吠陀本集》;第二编“史诗时代”(奴隶社会的文学),介绍了《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等作品;第三编“古代文学时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文学),介绍了迦梨陀娑、檀丁、波那、苏般度等作者的作品。内容包括梵语(包括吠陀语)文学作品,时代从上古跨越到12世纪。
《梵语文学史》既是教材,又是研究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由梵语专家撰写的梵语文学史。那个阶段中国正式出版的国别文学史不多,研究印度文学史的著作也寥寥无几,可以说金克木先生所写《梵语文学史》“在研究外国文学史的学者中是比较少见的”[69],而且该书“很长一段时间是这一领域里唯一的一种文学史著作”。[70]在此著作出版前,中国对印度文学研究的著作仅有两本,一本是许地山的《印度文学》,一本是柳无忌的《印度文学》。然而,相较这两本,《梵语文学史》无论是在资料上、篇幅上和研究深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是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印度文学史著作。郁龙余分析说:“许著当属首创,带有较多概述性质,还不是一本印度文学史专著。金著则完全不同,是一本28万余言的大著,不但有自己的观点,而且自成体系。”[71]黄宝生、郭建荣也著文评价道:“这部《梵语文学史》是中国梵语文学研究的奠基作。与国外的同类著作相比,它有自己的显著特色和长处。它努力运用唯物史观,将梵语文学的发展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中。对作家和作品的介绍和分析,采取‘历史和美学’相结合的文学批评方法。但是,因印度古代历史本身的研究难度就很大,故采取这种写作方法决非轻而易举。金先生为开辟梵语文学史的写作新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联想到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国学者撰写的外国文学史著作屈指可数,更显出这部《梵语文学史》的难能可贵。”[72]
(二)《梵语文学史》中关于梵语文学史时期划分问题的解决
学界对梵语文学史的时期划分问题一直都存在分歧,这与古代印度的历史分期存在争议有关。金克木指出,“最大的困难是历史方面问题:一是古代印度的历史分期和社会发展情况,一是作家作品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文学史按社会发展阶段分期还是按朝代分期,这在写中国文学史时似乎还有不同意见,而在写梵语文学史时两者都很难办到。原因是对古代印度历史情况的研究还不足以解决写文学史中的问题。古代印度历史按社会发展阶段分期的问题,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是不注意的,宣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印度历史的人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我所知,大概直到近年来,尽管这样论述古代印度社会的人不少,但是互相争论的各种说法仍然没有趋向一致,而且差别还是不小。究竟印度的奴隶社会起于何时,又在何时发展到封建社会,这个过渡时期有多久,有什么样的特点和过程,各地先后差别如何,这类问题,几乎‘言人人殊’;论证较全面和说服力较强的很少,而凭单文孤证或对史料意为去取和解释的却不是没有。当然史料的缺少和复杂是一个客观原因,而其他原因也不能排除。我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问题争论了多年,近年来才略有一致趋向,而尚无一致结论。由此可以想到古代印度社会历史分期问题也不会很快解决”。[73]
尽管如此,金克木仍然在继承许地山和柳无忌的划分法的基础上,将梵语文学史划分成“《吠陀本集》时代”、“史诗时代”、“古典文学时代”共三个阶段,颇为成功地解决了写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张剑文章《槛外有情——金克木和他的〈梵竺庐集〉》对这种划分方式有一个中肯的评价:“《梵语文学史》是中国第一部对印度个别语言的文学史研究专著,为印度文学史的整体研究架上了一座桥梁。古代印度学问以口传为主,派别繁多,字体复杂,且带有世代积累性特点,文本及其作者的断代工作很难理出一个清晰线索,金先生打破了传统文学史研究的‘时代—作家—作品—评价’的模式,而是按照作品的内容和类型将古代印度文学划为《吠陀本集》、史诗、古典文学三个时代来论述。既避免了将文学史写成繁琐的文献考证史,又使文学史研究直接切入到了文学本身。”[74]
(三)《梵语文学史》采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史研究方法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以其理论的科学性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国许多文学史都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批判继承为原则,用阶级观点、以人民性和历史进步性为主导而写成的。《梵语文学史》是在这种学术氛围中产生的,无疑也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关于这种指导方法,学术界有批判的成分,但相比之下,对该著作的评论还是认定为它表现了时代“特点”,表现了优于其他同类著作的特点。评论家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阐释《梵语文学史》所体现的以马列文学理论思想,特别是“现实主义”理论作为评价的标准。
首先,全书各章节的标题[75]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金克木在梵语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划分上与许地山和柳无忌的《印度文学》相似而不同,他的划分法与当时的学术环境有关,与列宁、斯大林的社会阶段划分理论挂钩。他将《吠陀本集》时代称为“原始社会解体和阶级社会形成时期的文学”,将“史诗时代”称为“奴隶社会的文学”,将“古典文学时代”称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文学”。各章节标题也如此,比如第二编第一章的标题是“奴隶制王国中新文学的形成”,三小节的标题分别是“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发展”、“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反映阶级斗争的庞大文献”。除此之外,在每编的第一章里,都综述各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对文学发展和演变的影响。[76]王向远指出,金克木不同于其他学者的地方在于“努力地体现马列主义的观念和方法”,但“明显地暴露出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生硬痕迹”,“带有它写作与出版的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77]
除了标题,行文中也运用了马列主义理论来指导写作。金克木的《梵语文学史》“以马列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论作为评价作家作品的主要依据,在论述和评价两大史诗、《五卷书》、迦梨陀娑的戏剧等主要作家作品的时候,作品与现实生活关系是作者的主要的视角,反映出19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气候的影响。实际上,印度文学(当然包括上述作品)的主导倾向是超越现实生活的、形而上的、冥想性的、神话式的、非现实主义的”。[78]尽管作者(金克木)清楚印度文学的超现实特点,但“没有将这种特点充分地展开来论述,而往往将它们归结为‘唯心主义’并加以贬抑”。考虑到作者出于写一本中国人写的印度文学史这一目标,“《梵语文学史》的‘时代性’,又是与它的中国的学术特色密切相连的,因而我们似乎还不能简单地视为‘缺点’,而应更恰当地视其为‘特点’”。[79]何乃英举《梨俱吠陀本集》中因陀罗的形象问题为例,认为金克木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人们历来认为因陀罗只是自然现象的化身,与社会生活没有什么联系。金克木文中提到印度传统历来把他算作雷雨之神,西方学者更多以为他只是雷雨的人格化。但这不能解说许多关于他的神话故事。如果把它看做是人间的英雄与天上的自然威力的结合,这样社会的典型人物就是他的形象和故事的主体,自然现象的描写则是对他的威力与功勋的艺术加工。
其实,关于文学史使用马列主义的观念,金克木先生是非常清楚的。金克木说:“这本书一望而知是依照当时的教科书规格和指导思想编写的。然而我没有放弃自己原先的原则,一是评介的作品我必须看过和读过,没看到的则从简;二是处处想到是中国人为中国人写,尽力不照抄外国人熟悉而中国人不熟悉的说法。”[80]郁龙余举四点分析金克木考虑如何写好一本中国人的《梵语文学史》的思路,认为理解这四点是理解全书的关键:“第一,‘以文学为主,非文学部分从略’;第二,‘写成一本看出来是我国人自己写的书’;第三,‘使本书能为一般读者看得下去’;第四,简略他人‘有所未妥之处’,‘大胆说一点自己的浅尝臆说’。”[81]可见,尽管带有当时鲜明的时代特色,但在使用此方法之余,他还运用了适合中国人阅读的、研究印度文学的方法,力求给读者呈现印度文学的原貌,让读者能更深入地了解印度文学,彰显了一位中国学者应有的立场。
(四)《梵语文学史》注重原典和中印比较意识
《梵语文学史》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文学的原典性,二是注重中印比较意识。
金克木在研究编写印度文学史、研究印度古籍时一直秉持原典,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治学。“该书的主要贡献有两点:一是建立比较科学的、完整的梵语文学史体系,二是对于梵语作家作品的深入评析。”[82]他认为:“印度古籍和中国古籍类似,历来解说纷纭,断章可以取义,‘六经’可以注我,容易作‘各取所需’式的引用和解说。近代和现代的西方人和印度本国人的一些说法各有各的来源和背景,不能一概认为信史和结论。对古文献的研究又随着人类的科学和思想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不会停滞于一点。我依据这一点认识就注意言必有据,据必核对原来情况;重分析而戒笼统;同时又注意到边界的‘模糊’,注意各种文献‘信息’的复杂性,避免简单化,不轻下论断;要求分析而不割裂,概括而不含糊。当然,这些只算是我心中悬着的目标,自己未必都能做到,不过力求不盲从而已。”[83]他在《印度文化论丛》自序里也说:“我尽量探寻原始资料,核对本来面目。我对印度古代文献当初一开始涉猎,就感觉到原来自以为知道的多不可靠,而许多常见到的表述又往往同实际情况不尽符合。”[84]从众多与印度古代文学相关的著作和论文所引用数据来看,《梵语文学史》从原典出发,着重分析和诠释重点作家作品,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迄今并未有其他相关著作可以超越。目前,中国学者在论述印度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内容和观念大都援引于这部经典的文学史著作。而许多从未介绍的作家作品就更不用说了,比如对《瑜伽婆私吒》的研究,只有金克木先生在其《梵语文学史》中作过简要的介绍。王向远对金克木先生从原典出发写文学史的做法表示敬佩:“这是中国第一部专门的梵语文学史,第一部由通晓梵语的人以第一手材料写成的梵语文学史,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印度文学史。它的资料的丰富翔实、内容全面系统、论述严谨,分析透彻,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梵语文学史体系,确立了梵语文学史的基本内容,从阅读原作入手对作家作品,特别是重点作家作品都做了透彻的阐释和独立的评价,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85]
为了让读者更深入了解印度文学,金克木除了在翻译原典材料上下功夫外,在论述评价印度文学时常以中国文学为参照。如介绍吠陀语时,金先生拿我国的汉语体系来比较;介绍印度个人祭祀时,拿我国古代的礼来比较。介绍《伐致诃利三百咏》中诗人表白自己节操的诗句后,为了让读者能理解诗人叹息社会对自己的冷落之情,金克木引述陶渊明《咏贫土》的诗句,让中国读者感同身受,极富启迪意义。正如学者王向远所认为的那样:“许多地方都可以发现作者有意将印度文学与中国文学做比较,虽然通常是三言两语,却富有启发性。”[86]
《梵语文学史》的许多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无论是资料翻译的准确性、论述的严密性,还是资料的丰富性、观点的新颖性,填补空白性,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此书不仅有史料意义,而且还具有开拓性意义,既通俗易懂,又高雅不俗,是印度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
注释
[1]范曾:《范曾自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249页。
[2]季羡林:《病榻杂记》,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页。
[3]季羡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4]季羡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5]季羡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6]季羡林:《病榻杂记》,新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页。
[7]季羡林:《季羡林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8]郁龙余:《梵典与华章》,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8页。
[9]季羡林:《季羡林全集》第11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10]郁龙余、刘朝华:《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38页。
[11]季羡林:《季羡林全集》第29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第634页。
[12]徐梵澄:《跋旧作版画》,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徐梵澄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
[13]郁龙余、刘朝华:《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68页。
[14]徐梵澄:《〈五十奥义书〉序及各书引言》,载《徐梵澄文集》第4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15]徐梵澄:《〈五十奥义书〉序及各书引言》,载《徐梵澄文集》第4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16]徐梵澄:《〈五十奥义书〉序及各书引言》,载《徐梵澄文集》第4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17]徐梵澄:《〈五十奥义书〉序及各书引言》,载《徐梵澄文集》第4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18]郁龙余、刘朝华:《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89页。
[19]《奥义书》,黄宝生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导言”,第4页。
[20]徐梵澄:《〈五十奥义书〉序及各书引言》,载《徐梵澄文集》第4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21]徐梵澄:《〈五十奥义书〉序及各书引言》,载《徐梵澄文集》第4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
[22]分别为:数论、瑜伽论、正理论、胜论、前弥曼差论和后弥曼差论。
[23]般度族人和俱卢族人两军对垒,即将恶战。般度族统帅阿周那在战车上望向敌军阵营,见对方有好些自己的族人甚至老师,想到这些人将在战争中被自己杀死,斗志动摇,武器从手中掉落。阿周那表示宁愿游方乞食,也不愿参与杀戮。内心极为冲突,无法选择判断。克里希那向他开导,对话构成《薄伽梵歌》的主要内容。
[24]如立道《〈薄伽梵歌〉及其宗教思想探析》,张保胜《〈薄伽梵歌〉初探》。
[25]徐梵澄:《〈薄伽梵歌〉南印度版译者序》,载《徐梵澄文集》第4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26]日耳曼学者罗林泽于1896年翻译此歌,乃条出百余处,谓思想甚至其文字有与新约福音书相同者……近代甘地之记室得赛,于其译本中广引可兰经等以相发明,第13页。
[27]徐梵澄:《〈薄伽梵歌〉南印度版译者序》,《徐梵澄文集》第4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28]徐梵澄:《〈玄理参同〉序》,载《徐梵澄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
[29]徐梵澄:《〈玄理参同〉序》,载《徐梵澄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
[30]〔印度〕室利·阿罗频多:《薄伽梵歌论》,徐梵澄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77页。
[31]徐梵澄:《〈玄理参同〉序》,载《徐梵澄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
[32]阿罗频多的理论体系中,世界共有八个范畴,依次为:Pureexistence、Consciousnessforce、Bliss、Supermind、Mind、Psychic、Life、Matter。
[33]徐梵澄:《〈瑜伽的基础〉题记》,载《徐梵澄文集》第4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34]徐梵澄:《〈周天集〉译者序》,载《徐梵澄文集》第4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
[35]徐梵澄:《〈周天集〉译者序》,载《徐梵澄文集》第4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页。
[36]徐梵澄:《跋旧作版画》,载《徐梵澄文集》第4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37]徐梵澄:《〈陆王学术〉后序》,载《徐梵澄文集》第4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
[38]徐梵澄:《〈薄伽梵歌〉南印度版译者序》,载《徐梵澄文集》第4卷,上海三联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店2006年版,第169页。
[39]徐梵澄:《〈薄伽梵歌〉南印度版译者序》,载《徐梵澄文集》第4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40]徐梵澄:《〈玄理参同〉序》,载《徐梵澄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41]徐梵澄:《希腊古典重温》,载《徐梵澄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42]郁龙余、孟昭毅:《东方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
[43]郁龙余、孟昭毅:《东方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
[44]徐梵澄:《〈行云使者〉跋》,载《徐梵澄文集》第4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45]陆扬:《跋徐梵澄文集》, php?threadid=22732。
[46]郁龙余、刘朝华:《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84页。
[47]孙波:《徐梵澄传》,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10页。
[48]徐梵澄:《徐梵澄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49]参见孙波、杨煦生:《此何人哉——关于徐梵澄的对话》,载《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7期,第88页。
[50]王小琪:《金克木先生告别读者哭着来笑着走》,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16日。
[51]余杰:《余杰精品集》,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
[52]纪念金克木先生的文章中有许多对金克木冠以“智者”之头衔,如牟小东:《当代智者金克木》,载《群言》,2000年第10期;王献永:《智者的魅力——敬悼金克木先生》,载《江淮论坛》, 2000年第5期;陈芳:《湖畔智者大师风范——缅怀印度文化学者金克木》,载《民主与科学》, 2000年第5期等。
[53]金克木:《金克木集》第5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04页。
[54]金克木:《金克木集》第5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04页。
[55]《印度古诗选》,金克木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
[56]金克木:《印度的伟大诗人迦梨陀娑》,载〔印度〕迦利陀娑:《云使》,金克木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9页。
[57]〔印度〕迦梨陀娑:《云使》,罗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58]王向远:《近百年来我国对印度古典文学的翻译与研究》,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59]王向远:《近百年来我国对印度古典文学的翻译与研究》,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60]金克木:《梵竺庐集(乙)天竺诗文》,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
[61]黄宝生:《金克木先生的梵学成就——读(梵竺庐集)》,载《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62]金克木:《尝一滴海水可知大海的咸味——〈印度古诗选〉前言》,载《江淮论坛》,1984年第1期。
[63]金克木:《尝一滴海水可知大海的咸味——〈印度古诗选〉前言》,载《江淮论坛》,1984年第1期。
[64]金克木:《〈摩诃婆罗多插话选〉序》,载《南亚研究》,1984年第2期。
[65]王向远、冯新华、李群等:《佛心梵影:中国作家与印度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2页。
[66]郭良鋆:《师恩深如海——纪念金克木先生逝世一周年》,载《南亚研究》,2001年第1期,第74页。
[67]牟小东:《当代智者金克木》,载《群言》,2010年第10期,第30页。
[68]谢宁:《哲人风范——怀念一代智哲金克木先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9月13日,第9版。
[69]刘安武:《印度印地语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序言”(季羡林),第1页。
[70]王邦维:《北京大学的印度学研究:八十的回顾》,载《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103页。
[71]郁龙余、刘朝华:《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315页。
[72]黄宝生:《金克木先生的梵学成就——读〈梵竺庐集〉》,载《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第147页。
[73]金克木:《梵语文学史》,载《金克木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24页。
[74]张剑:《槛外有情——金克木和他的〈梵竺庐集〉》,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11月29日。
[75]这里说的标题出自196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梵语文学史》(第1版),此著作后来收入《梵竺庐集》(甲)和《金克木集》第2卷时已经把标题改为“第一编:《吠陀本集》时代”、“第二编:史诗时代”,“第三编:古典文学时代”。
[76]王向远:《七十年来我国的印度文学史研究论评》,载《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第146页。
[77]王向远:《七十年来我国的印度文学史研究论评》,载《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第146页。
[78]王向远:《七十年来我国的印度文学史研究论评》,载《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第147页。
[79]王向远:《七十年来我国的印度文学史研究论评》,载《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第147页。
[80]金克木:《金克木集》第6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75页。
[81]郁龙余、刘朝华:《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316页。
[82]何乃英:《东方文学研究在中国》,载王邦维主编:《比较视野中的东方文学》,北岳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83]金克木:《印度文化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84]金克木:《金克木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5页。
[85]参见王向远:《七十年来我国的印度文学史研究论评》,载《外国文学评论》,2001第3期,第146页。
[86]王向远:《佛心梵影——中国作家与印度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