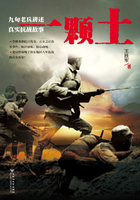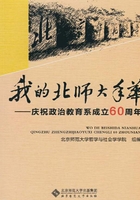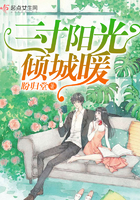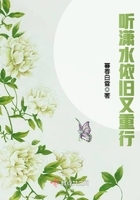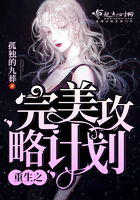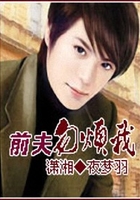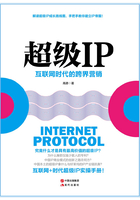十、在我到达加拿大的第一年里,所有的梦都是和我在中国的生活有关的,加国无梦
打工或是读书的日子,有时也会感觉到有些累了、倦了,但我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心中还有未来,眼前还有希望,也就不觉得苦,不觉得累,只是那份孤独,那份寂寞,那份思乡的惆怅,久久地陪伴着我,难以释怀,难以忍受。
说来也怪,在我来到加拿大以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我从来就没有做过任何关于我在加拿大的生活以及任何与加拿大的场景有关的梦,我很奇怪,加国无梦?
一个人在海外,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尽管对于眼前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与希望,但是浓浓的思乡之情却总是沉沉地压在心里,挡不住,挥不去。几乎在每个夜里,我都会在梦中见到家里的亲人,见到往日的朋友,更多的时候是一次次在梦中,感觉到自己仿佛仍然身在国内,在纠结地思考着,要不要出国,该不该出国?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梦醒之后,睁开双眼,茫然环顾四周,好一会儿才清醒地意识到,我已经置身国外,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朋友相伴,只有自己,还有漫漫的长夜带给我的孤独。
有一次在跟妻子通电话时,妻子告诉我,我走后女儿好像突然长大了,听话了,懂事了,钢琴也进步了,说着把电话移到钢琴旁,女儿知道爸爸在电话的那头听着,就越加弹得卖力,于是,一曲《水边的阿狄丽娜》便行云流水般的漂洋过海,回荡在我的耳畔,虽然我的嘴上平静地说“弹得好,弹得好”,但是眼泪却早已止不住悄悄地流了下来。
即使在一年以后,妻子、孩子已经来到了我的身边,我们也买了房子,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小家,可是我对家乡的思念却依然如故。有一天,情浓之际,我挥笔写了一首歌词——回家。
回家
走在异国的大道上
迎面飘来草木花香
伴着
柔的清风
暖的阳光
可心情却总是有些不一样
人说这里是个好地方
生活似乎也宁静安详
还有
景色很美
人也善良
可心情却总是有些不一样
白天
一次次告诉自己
好男儿就该志在四方
夜里
却一回回难以抗拒
似梦似醒重回故乡
啊,故乡
对你的思念
原来竟是那么的无法阻挡
离家的脚步越远
对家的思念就越长
即使偶尔在异乡绽开笑颜
也难掩嘴角弯起的一丝惆怅
故乡,你已深深地,深深地
铭刻在我的心上
回家
一刻也不停留
收拾行囊,现在就出发
我不要等什么事业有成衣锦还乡
也不再怕两手空空无颜见爹娘
回家
一刻也不停留
收拾行囊,现在就出发
只为漂泊的脚步不再迷失方向
只为流浪的心从此不再流浪
回家
一刻也不停留
收拾行囊,现在就出发
十一年过去了,现在,加拿大也是我的家了。
记得在蒙特利尔的中文报纸上看到过一篇文章,一个女孩在写到故乡和蒙特利尔的关系时,把故乡比作父母,把蒙特利尔比作爱人,她爱蒙特利尔,也爱自己的故乡。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也许她会和她的爱人永远在一起,但是在遥远的东方,在那个叫做“中国”的地方,有一个我们海外游子心中永远的家!
老冯语录:
离家的脚步越远,对家的思念越长,移居海外,才发觉对家的思念竟然是那么的无法阻挡。
十一、第一次回国,感觉有些异样,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家乡变了?抑或是我变了
八个月的“COFI”课程结束了,家人的团聚移民申请也顺利通过,我决定回去一趟,亲自把妻子、孩子接过来。把行李重新整理好,装上箱,寄放在朋友家,买张机票,我回到了已离别了十个月的祖国。
临回国前,常有从国内回来的人抱怨国内的脏、乱、差,并诉说着他们种种的不适应。怎么会呢?我想,至少我不会有这种感觉。刚刚离开家乡不到一年,闭上眼睛,老家附近的每条街道、每个商铺的样子都历历在目。做梦都想着彩电塔夜市儿一条街的小吃,一想到那里的烤羊肉串儿,放在小火炉上烤的蛤蜊,我的口水就像小溪一样汩汩流淌。怎么能不适应呢?可能是他们太久没有回去的缘故吧,我绝对不能。
还没等到家,祖国的变化就已经感同身受了,最大的感觉就是人们仿佛一下子都富裕起来了。
在北京机场等候转机的时候,我看到一位年轻时尚的母亲在教训她的看起来只有五六岁大的儿子,因为什么原因我没听清,只是听见那个母亲大声地说:“我都带你去了十个国家了,十个国家,非洲都去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大家都寻声望去,同样的话,她又说了一遍,还在十个国家处加重了一下语气,强调一下。小孩子好像并没领情,依然撅着嘴在踢脚下的椅子,很显然他并没有明白十个国家和他的行为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在我看来,孩子惹妈妈生气了,不外乎要什么东西没给买之类的小事,使个小性子,跟十个国家扯不上关系,十个国家在孩子心里远没有十块糖,十个玩具来得直观和直接。她那么大声,并且把“十个国家”说得很重,总像是在告诉别人,你看我闲着没事儿,已经带孩子去了十个国家了。
在另一边的机场的坐椅上,是一群东北老乡,好像也是刚刚旅游归来,为了打发候机的无聊,玩起了扑克牌,玩得起劲时兴高采烈,大喊大叫,情到浓处,甚至嘴里“妈妈、奶奶”以及“生殖器”都不经意也溜了出来,听得我既感到了乡音的亲切,又有了些久违了的陌生。
紧挨着我坐着的一老一少两位女士,也在大声地说着话。我听得出她们是刚刚从新马泰旅游归来,高兴之余还在不停地谈论着旅途感想,继而又聊到各自单位的经济效益多么好,最后话题落到各自老公多么能挣钱,各自的家里是什么样的车,天天“呲”(吃)鱼,“呲右”(吃肉)等,越发使得我感到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国内人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可说实话,我对这种有关个人隐私的直言不讳也有些不习惯、不适应了。日子是自己过的,不能分享,尤其是和陌生人,我和她们只是近在咫尺,而她们的“喊话”绝对可以传到十米以外,以至于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年轻女孩一直在不耐烦地看着她们,最后还是带着一脸的愤怒走了。而我由于旅途劳累,懒得动弹,便由始至终地被动地“偷听”她们的谈话。
回到家里,除了感到温暖、亲切,同样也感受到了变化。
父亲刚刚从七十多平方米的旧房搬到了近九十平方米的新房,家居陈设也旧貌换新颜。妹妹新家的面积更是直逼两百平方米,以当时的情形来看,可以说是吓了我一跳,再看看酒柜里摆放的形状各异的各国名酒,使我感觉到我精挑细选、物美价廉、加拿大特产的冰酒有点儿拿不出手。
最初的几天,只是待在家里,陪陪家人,享受亲情,也顺便倒倒时差。闷了,也试着出去走走。有一天,我骑上自行车想在家的附近转转,透透气,可过了不一会儿就捂着鼻子跑了回来。大街上,尘土飞扬,空气中,弥漫着被太阳烤热了的柏油马路上浓浓的沥青味儿;汽车的嘀嘀声和商家高音喇叭里传来的音乐声、叫卖声,此起彼伏,收废品的叫喊伴随着他手中刺耳的打击声,不分时间地灌入我的耳中。抬眼望去,马路上,汽车、自行车、行人密密麻麻地交织在一起,加上豪华饭店门前摇曳的色彩缤纷的广告使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我有些心跳加快,血压上升。
我发现我好像有点不习惯这种“热闹”了,心中不免有些沮丧。
这不是我想要的感觉!
但是我的这种不习惯的短暂的“矫情”,很快地就被推杯换盏、歌舞升平的亲友团聚击得粉碎。
这毕竟是我生活了近四十年的地方,我生于斯,长于斯,苦于斯,乐于斯。几乎所有的亲人、朋友,昔日的同学、同事以及我前半生的记忆都依然鲜活地留在这里,所以我很快地又融入其中,甚至有些乐不思蜀。后来的几次回国也证明了这种不适应、不习惯的感觉只有几天,也只是在第一次回国时比较明显,第二次、第三次、第N次便不再那么难以接受了,而且国内的环境也在不断改善,人的精神面貌也是越来越好,更重要的,这里仍然是,并且永远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家园。
来到加拿大,我们曾经有过苦,但更多的还是甜,朋友相聚之时也总是谈起昔日的“艰苦岁月”,谈起我们刚来的时候如何如何的难,谈起那时候是怎么怎么的不容易。对于我们当中绝大多数的朋友来说,这种不容易只是最初的一两年,来加拿大的时间也只有十年,我们的故事也就只能追溯到十年前。而每次回到国内,在和国内的亲朋好友把酒相聚时,我们无意中说起的事情都很久远。诸如上大学的时候班上谁追过谁,上中学的时候谁的学习总是不好,上小学的时候谁总是打架淘气等,在家里,当老人端上来一道菜时也总会跟我说:“这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每当这个时候,
我的思绪便一下子回到了很远很远的从前。
我想,这应该就是人们所说的——根!
老冯语录:
对于我们这些半路离家的游子来说,家不仅仅是一个概念,那里有许多亲朋好友,以及依然鲜活的记忆。
十二、时隔一年,全家登陆,租房,办手续,所有的事情重新来过,但我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2001年11月2日夜里,我们全家人到达蒙特利尔。
看惯了高楼大厦的女儿,探着头望着窗外,看着一片片黑乎乎低矮的房子,发出了“这也不比沈阳好哇”的感叹。
房子是提前两个多月,回国前草草定好的,不是十分理想,只有一室、一厅、一厨、一卫。并且我也是和家人一起回来,从朋友那儿现拿的钥匙,无法提前收拾或是添置些什么家具,所以,家徒四壁,空空如也。陌生的地方,空空的房子,与连续两个月来在国内亲友设宴送行的热烈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仿佛从天堂一下子掉到了地狱。妻子有些沮丧,倒是女儿很懂事儿地装出一副没事的样子说:挺好啊,我喜欢这儿!
住在附近的朋友给我们准备了热乎乎的汤面,吃完之后又塞给我们好几个装垃圾用的大大的黑色塑料袋,回到家里,铺在地上,上面再铺上褥子,收拾停当,已经是下半夜了,我们全家人挤在一块儿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出去买些柴米油盐之类的东西,以及一些日用品,新生活就算是开始了。
新租的房子虽说同样有炉头冰箱以及壁橱,但家具却是一样儿也没有,别的还好,全家人站着吃饭的问题急需得到解决。虽说我已在此生活了近一年的时间,但除了打工,就是学法语,加上是一个人,没有车,吃饱了就得,对这里的情况了解得还是不多,我们就在新家附近的连锁的二手商场花两百多元买了一个柜子、一张餐桌加上四把椅子,同样的价钱几乎可以买到新的了。
同样的错误我犯了两回。
租的房子,面积不大,总觉得是暂时的,能对付就对付,但是床还是要买个新的。当时,对于又好又便宜的几家大型连锁家具店还不知道,就在离家最近的商场转了转。床的样式都不怎么样,价格却都挺贵,最便宜的床架子加上垫子,也要五百加元左右,妻子掐指一算,“这也太贵了,合人民币要三千多块,不行,明天再看看其他的商店”。说来也怪,那时候在国内花三千多元买张床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怎么到这儿就觉得贵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突然发现,在一家门前的大树旁,靠着一套看起来很新的床架以及床垫子,外面还套上了塑料罩子怕被雨淋了,我知道这是那户人家丢弃的。这里,每个星期有一天是丢垃圾的日子,每到这一天,家家门前放着垃圾桶,以及人们不要的旧家具等。老外就这习惯,喜新厌旧,买到手的东西没用多久就不喜欢了,就换新的,旧的就当垃圾随手扔掉。有的人家知道其扔掉的状况良好的“垃圾”还很新、很好,可能有人会用得着,就把它倚靠在什么地方摆好,而不是扔在地上,以方便人家来拿,更有的人家扔了好东西,怕人家不知道是不是扔的,不敢捡,就在上面写上“赠送”两个字,告诉你随便拿。
真是想什么就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