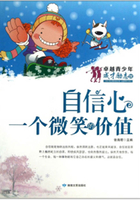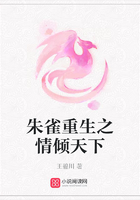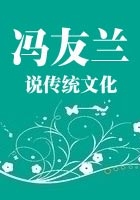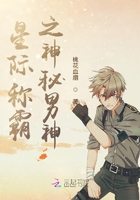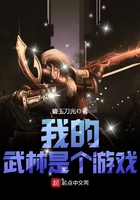古典诗词专家、大书法家吴丈蜀先生在世时,有一次我有幸陪他老人家去鄂南采风。在路边歇息时,说起了黄鹤楼上的字画,我说:好好的一座名楼,只可惜字画挂得太多,给人以堆砌之感。吴老说:岂止是堆砌,简直是“污我眼目”。这四个字给我印象太深了,后来每当看到恶俗不堪的字画,我也喜欢借用这四个字来调侃一下。
外地客人到武汉,总会慕名去登黄鹤楼。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被誉为“江南三大名楼”。我在武昌居住二十多年了,每次陪客人去看黄鹤楼时,一般都是买好票,让客人自己去登临,我宁愿在楼下盘桓等待。只因为我心中藏着吴老说过的那四个字。可是慢慢地,我发现,蛇山之上,黄鹤楼下,另有几处艺术景观,却也值得一看,而许多客人,往往对它们忽略不见,错失美景了。
说起黄鹤楼,许多人都会随口吟起诗人崔颢那首千古绝唱:“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因为此诗也曾被称为“崔诗楼”。知道一点文学典故的,当然还会想到诗仙李白当年看了崔诗之后的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黄鹤楼东侧,离主楼不足百米处,迎面可见一座色泽古朴的石照壁形式的黑色浮雕:《崔颢题诗图》,描绘的就是这座名楼和这首名诗结缘的故事。画面上的诗人崔颢,峨冠博带,衣裾飘飘,宛如仙人临世。他的目光追寻着高远,仿佛胸中正有千般诗情萦绕升腾。他手中的如椽巨笔,正饱蘸浓墨,满腔激情似乎就要喷涌而出。暮色苍茫,大江奔流;故园迢遥,前路旷远,此情此景,也许正牵惹起诗人无边的乡愁。于是,诗人若有神助,口吐莲花,吟诵成诗,几令云天俯首,江山动容……
这幅巨型浮雕,把这首千古绝唱诞生的那一瞬间,生动地呈现在了游人面前,为巍巍名楼平添一处不朽的文化景观。照壁上的崔诗,系当代大书法家沈鹏先生所书。浮雕所用的石材,选自四川越西的异常坚硬的黑沙石。浮雕设计者是四川著名雕塑艺术家、当年轰动全国的《收租院》的主创者之一赵树桐先生。赵氏擅长历史文化人物题材的创作,其代表作有四川眉山的《诗人苏东坡》,重庆的《张露萍烈士》,四川奉节的《白帝城刘备托孤》等。
在黄鹤楼公园南区的白龙池畔,另有一幅大型花岗岩高浮雕塑,名为《鹤归图》。这幅近五米高、四十米长的浮雕上,共有九十九只黄鹤,有着“久久”即不朽的寓意。这些黄鹤分成了鹤栖、鹤戏、鹤舞、鹤翔、鹤鸣五组。每一只都显得栩栩如生,仿佛从天外归来,从苍茫的烟雨中飞来,欢聚在这千古名楼之下。
昔人已乘黄鹤去,今人重唤黄鹤归。艺术家分别采用了高浮、浅雕、透雕等艺术手法,配以松、竹、梅、灵芝、流水、岩石、祥云等自然景物,使九十九只姿态各异的仙鹤尽情释放着各自的生命灵韵,整个作品有如一幅壮丽的流动的长卷,又似一首节奏分明、故事跌宕的童话叙事诗。看着这些华羽纷披的吉祥大鹤,我想到的是:天地有正气,人间有大美,天下苍生和万物的和谐与吉祥,才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祈愿和追求。
为了对这幅雕塑有更多一点了解,我特意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原来,这幅作品是我国目前为数不多的几幅超大型室外花岗岩浮雕之一。它凭借蛇山白龙池畔的山势而筑,由三百四十多块枣红色花岗岩石材镶嵌拼接而成。这幅作品从酝酿草稿,到最后落地竣工,历时四个寒暑。所用的石头,采自距离武汉两千多公里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境内,海拔近五千米的海阿山中。整个作品耗去的石料,前前后后运载了足足四火车皮。而为了对付这些硬度堪称世界花岗石之最的石头,雕刻家们光耗用的合金钢钢钎,就重达三吨之多。
参与这幅大型作品的设计和创作的艺术家,除了前面说到的赵树桐先生,还有四川的另一位雕塑家任义伯先生。任氏的主要雕塑作品有《收租院》、《毛主席纪念堂南大门群雕》等。
除了《崔颢题诗图》和《鹤归图》,黄鹤楼下的景物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矗立在蛇山之巅的一座青色花岗石雕塑:《精忠报国图》。猎猎战旗,滚滚长车,青鬃烈马,故国山河。伫立在这凝重的如同古城墙般的浮雕之前,仿佛还能感到岳家军誓死踏破贺兰山缺,用壮志洗却靖康之耻的热血豪情。后人曾评论岳飞的《满江红》说:“千载后读之,凛凛有生气焉。”《精忠报国图》这幅雕塑作品,也能给人以“凛凛有生气”的艺术美感。
还思故园今夜月,几人相忆在江楼?美丽的名胜留下了美丽的故事,天上人间,代代相传,使人即便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黄鹤楼,不正是因为有了这美好的传说故事,益添了几许文化的灵光和诗意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