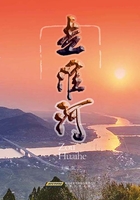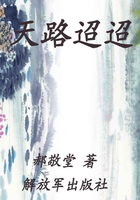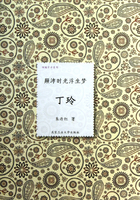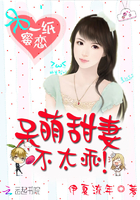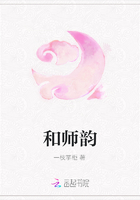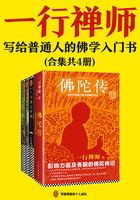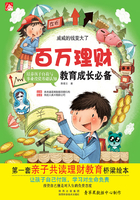意大利著名作家和学者卡尔维诺,一生兼有作家、文学批评家、编辑出版人等多重身份,许多作家同行觉得他把那么多精力与才华用在文学批评和编辑出版上,以致影响了他个人的创作,未免有些可惜。卡尔维诺自己却很坦然,他说:“因为做的是出版工作,我花在别人的书上的时间比自己的书多得多,我并不介意。任何消耗在有益于以文明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的事务上的精力,都是适得其所的。”这是一种十分大度的、让人肃然起敬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的美德。
书法家、作家刘永泽先生,身兼湖北省文艺界多种领导职务,在我看来,这些年来,他的主要精力与心思,无疑也是“消耗在有益于以文明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的事务上”。换句话说,他在书法、文学创作等方面的才华与成就,被他自己所从事的对全省文学艺术界的领导、协调、组织和服务的工作掩盖、遮蔽了,以至于朋友们在和他交往时,有时会忘记了他的书家和作家的身份。然而,大道低回,静水流深,永泽先生自己倒并不在意。他说,能够做一个职业书家、专业作家当然很好,可是全省文艺界也十分需要一些甘居幕后的“服务人员”,需要一些乐于躬下身来,为作家和艺术家们搭建平台、铺设“红地毯”的人。他觉得他就是这样一个“服务人员”。
其实,刘永泽进入文艺界的时间很早,与文艺界的缘分也源远流长。青年时代,当他还是“铁道兵”的时候,就是一位经常在军报上刊发诗歌和散文的军旅诗人了。后来进入全国残联工作,曾经策划和组织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若干大型的演艺活动。其中他最为得意的两项“杰作”,一是策划和组织了大型歌舞节目《我的梦》,先后出访过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希腊、埃及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我的梦》在首届好莱坞国际电影电视节上获得了最佳舞台艺术片奖;聋哑人舞蹈《千手观音》更是家喻户晓,获得了二〇〇五年央视春晚歌舞类一等奖和特别大奖。
我记得,十几年前,当《千手观音》的女主角邰丽华还在湖北美术学院念书时,有一次我为湖北电视台的一档节目去采访她,她用手语给我“朗诵”过《我的梦》里的一首感人的“手语诗”。朗诵完毕,在她写给我的一些她所感激的老师和领导的名字里,就有“刘永泽”三个字。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刘永泽先生。还有一次,是徐迟先生还在世时,他命我给他去买几张好一点的宣纸,我觉得奇怪,因为他几乎从不用毛笔写字,买宣纸干什么?后来才弄明白了,原来他是应刘永泽先生的约请,要为湖北省残联的一次大型公益活动写一幅字,写的是《哥德巴赫猜想》里的“何等动人的一页又一页”那一段辞采斐然的文字。那是徐迟先生稀有的一次在大宣纸上写字,当然,他用的仍然是粗大的记号笔,而非毛笔。
永泽先生在负责省残联工作期间,以及到省文联主持工作之后,亲自策划组织和担任总指挥的文艺活动可真不少呢。文艺界朋友们记忆犹新的就有全国性的“长江文学笔会”、“神农架文学笔会”,“楚天翰墨情”、“云横九派浮黄鹤”、“荆楚狂歌——周韶华新作展”、“唐一禾艺术展”、“情系大别山”等大型书画艺术活动,以及“大地之爱”、“金秋地平线”等大型的综艺晚会。
作为作家,永泽先生曾担任过徐迟生平传记艺术片《把太阳拿过来》的总撰稿,还参与创作了《不凝固的雕塑》、《玫瑰项链》、《我在生活》等电视剧作品。真力弥满,万象在旁。我想,永泽是把自己对于文学的爱与知、对于艺术和艺术家的尊重与敬仰,都默默地融合进了他日常的策划、组织和协调工作之中了。也只有这样,文艺工作才能真正做得好、做到位。作为省文联的领导者之一,他内心里怀有一些十分美好的愿望和理想,例如,他非常希望能通过自己和同事们、同行们的努力,真正推动“荆楚画派”、“荆楚书风”能得到更好的彰显与传播;他也非常盼望着有一天,通过自己和同事们的努力,让全省的艺术家,无论什么流派和风格,都能摈弃狭隘的门户之见,携手并肩,共同踏上一道象征着团结、繁荣和荣誉的“红地毯”;他还希望,能用一些切实可行的活动,完善全省文化市场的运行机制,提升全省书画展览和书画市场的学术含量与艺术水准,等等。
在和他的寥寥几次交谈中,我能体会到并且认同他的一些朴素的观点。那就是:文艺活动确实需要“策划”和“包装”;文艺家们也需要更多的展示平台;人民群众需要优秀和高尚的文艺生活;文艺市场也需要高雅和优质的作品来提升和引领。总得有人来做这些事情。总得有人来做一些铺路、架桥、搭建平台、疏通渠道、完善市场和创新机制的事情。这些事情可能非常琐碎和不为人知,甚至做起来可能相当艰辛和困难,但是,只要在做着,只要做好了,全省的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们都能深受其惠,文联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就能有所提高。
这些年来,永泽先生作为省文联领导和书法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不遗余力地在为“荆楚书道”的发扬光大创造条件、寻找机遇。每当说起“荆楚书道”这个话题,他就兴奋无比,话语滔滔。他说:“荆楚书道,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他坚信,书道即书法创作的文化之道、艺术之道和学养之道,“书道乃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域或一个创作群体从历史积淀、文化特色、发展走势到艺术素养、创作倾向、作品风格、成果风貌以及书论研究水准的总体定义和系统概括。”
他在一篇谈论书艺的文章中曾举例论说荆楚翰墨、书道曾经的辉煌。“鄂州的怡亭摩崖,镌刻着晋人陶侃、唐人元结和李阳冰、宋人苏轼等历代大师的笔墨遗韵。苏东坡挟楚地灵气,创造出写意书法的风范。黄山谷奇崛峻傲,米芾八面出锋,张裕钊劲拔雄奇,杨守敬形韵并生,这都是荆楚书道所根植的文化生态环境。而唐醉石、邓少峰、吴丈蜀、黄亮、王遐举、曹立庵、杨白稥等近现代书法名家,则使荆楚书道得以薪火相传。”他认为,荆楚书道传统,是与钟灵毓秀的湖北山水有着割舍不断、挥之不去的情结的。“千湖的灵性孕育了楚人浪漫、狂放以至怪诞的性情,而两江的通达,又造就楚人兼容并蓄、敢为人先的气质。奇正相成而又气骨兼具,文脉悠久而又辈出新意,积淀厚重而又不断进取,是荆楚书道最显著的个性和特色。”
作为一位著名的书法家,永泽有自己的书艺追求和书法理想。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临帖,先后习过王羲之、米芾、王铎等人的作品,对于中国传统书道有自己的领悟与感受。他对楷、行、草、碑等各类书体皆下过苦功,其书法作品多次在国内参加展览,并且在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举办过个人书法作品展。他注重通过书艺表达心智,通过领悟书道而完成自我的精神修为。他认为,书法艺术,虽然人各有体,但是最终总会反映着修养的差别与人格的高下。他强调,所有艺术最后的竞争,必定是创作者个人精神境界与人格高下的竞争。
钱锺书先生《谈艺录》开篇有言“诗分唐宋”:“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又谓,“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刘永泽的书法里有以丰神情韵擅长的“少年才气”,然则更多的是以筋骨思理见胜的沉雄与萧散之风。如行草对联《云山星斗》、《云晴风逆》和草书斗方《舞魂》等几件作品,笔势蕴藉内敛,却又风骨凛然;结体迤逦,而运笔秀健,若风卷云舒,流丽而浑厚。
他对自己曾经投入过无数心血的聋哑人舞蹈《千手观音》情有独钟。我曾向他请教过,如何理解这个舞蹈,他说,千手观音之舞乃是灵魂之舞,抒发的是对人类和平、和谐世界和吉祥人间的祈愿与呼唤。我注意到《舞魂》这幅斗方里,他在“舞魂”这两个大字之下,又有一些文字补充道:“艺术真谛在于情。千手观音祈福人间,表达了对真善美的追求,舞动的灵魂。”这段文字也可用来解释他对书艺的追求。他的书道与书魂,又何尝不是对真善美的追求与拥抱。他在另一幅行草斗方《兰幽》里所书写的一段文字,也可用来作为补充:“兰幽美于情韵,品雅源于德馨,山峻显于湖秀,业盛得于智睿。”
在我看来,永泽的书法里处处充盈和流动着一种旷达而睿智的“逸气”。这是他的作品内在的“气韵”。这种气韵或者也可归结为一种“书卷气”,是一种内在的综合修养与气质,是一种成熟自如的风度。它们与书写者内在的学术底蕴和精神境界密不可分。正是有了这种气韵,才能意到迹随,若行若藏,乃至笔挟风涛、力透纸背。
“云晴鸥更舞,风逆雁无行。”我想,大处着眼,小处落墨,就是永泽先生文润墨畅、翰逸神飞的艺术状态的写真了。
永泽先生还有一个比较“特殊”一点的身份,也值得一说,那就是,他还是在武汉书画界颇有影响的一个艺术同人组织“武汉书画村”的一位积极的支持者和诸多活动的参与者。这也是他从内心深处想为武汉的艺术家们搭建更多的展示荆楚画派、荆楚书风的平台而表现出的具体行动之一。他把这个“书画村”称之为“都市里的村庄”。也因此,他和这个艺术村庄里的许多艺术家都成了经常互相切磋书道艺事的朋友。
永泽先生曾经以十分赞赏的口吻向我介绍这个“艺术村庄”:到这里来,大家可以暂时安静下来,享受一下淳朴、恬静和清新的艺术气息。在这里大家可以喝喝茶,互相观摩一下各自带来的书画新作;可以坐而论道,也可以挥毫作书;甚至还可以听听古琴弹奏,听听韦庐讲讲汉像砖和碑帖。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功利因素,大家纯粹为交流艺事、享受一下纯净的艺术而来。
这使我想到了乔治·桑在她的自传里写过的一段话:“如果世界上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能够完全摆脱浮华的时尚,能够使用少许的物质,甚至几乎是两手空空,单凭自己的梦想便为自己创造出一种生活,那么,这些人就是艺术家,这是因为他们的身上具有一种天赋,他们可以让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东西也充满盎然的诗意,可以用自己一贯的情趣和天生的诗情,为自我建造起一座朴素的草棚。”我想,聚集在“书画村”里的这些书法家、画家和作家们,大致就是这么一些人。“真力弥满,万象在旁。”永泽先生无疑是这个艺术村庄里的“灵魂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