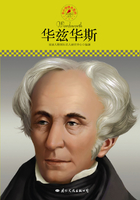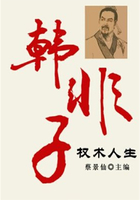第二天下午,一个身穿长衫,颇有风度的男子,在熙熙攘攘的南京路上由东向西走着。他蓄着一头乌发,厚厚地抹上金刚钻发蜡,颇像斯文的知识分子。大约在他后边十多米的地方,一个身穿黑长衫,脚着黑布鞋,戴一副墨镜,理着分头的青年尾随着他。这人尖锐的目光,透过深蓝色的墨镜,紧紧盯住前边那个颇有风度的男子。汽车、电车、黄包车、人流搅和在一起的南京路走过了,来到静安寺路,这位有风度的男子讨了辆黄包车,对车夫说:
“兆丰公园南门口。”
后边盯梢的青年也叫过一辆黄包车,吩咐车夫:
“跟着前面那辆车。”
车子过了静安寺,转到愚园路,而后在兆丰园的大铁门口停住。从黑的铁门栅栏中望去,园内花木郁郁葱葱,特别是进口处不远的一池秋水,碧绿清澈,在午后的骄阳映照下粼光闪闪。
园内游人稀少。
公园门口不远地方有棵高大的榆树,在秋阳下顶天立地站着,树下有卖香烟、五香豆的小摊子。那有风度的男子站在榆树底下,默默地抽着香烟,眼睛尽向东边的愚园路上看。
“先生,请问您是等沈女士的吧?”盯梢的青年已摘掉墨镜,很有礼貌地鞠躬,问。
“你?”
“喔,我是沈女士派来的。她说见面地点临时改在法国公园,让我来接您。”
说完,他左手一扬,在空中打了一个响指,忽然,一辆黑色汽车不知从哪里开过来,在大树边“嘎”的一声刹住。车内跳下一个彪形大汉,打开车门。那青年将这男子一推,说了声“请吧”,便把他弄进车里。
车子朝西北方向,着了魔地飞驰而去。
第二天,上海北郊大场地方的乱草中,丢着一具衣衫剥得精光的男尸。这便是沈素娥的表哥。
处理掉这个男人以后,杜月笙又叫人把开车送素娥去龙华寺的司机的双眼刺瞎,然后终身养着。
沈素娥坐在自己的卧房里寸步难行。她想找瑞兰,可这丫头说是出去叫老周,此后一直没见人影,老周更是没露过面儿;她试着拨了好几个电话,终于确认自己房里的电话已经拨不出去了。至于自己出去,沈素娥想也不敢想,她可以肯定杜月笙正等着她不顾一切地冲出去。现在,沈素娥还是不想双方抓破脸,那样她倒不在乎,可表哥肯定会完了。沈素娥甚至还抱着这样侥幸的幻想:只要自己克制住不做出失态的事情,杜月笙虽然影影绰绰知道了一点她和表哥的事情,但抓不住切实的把柄,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
大钟打响了整整七下,沈素娥被突然的钟声一惊,下意识地往墙上看了一眼,巨大的表盘上竟然映出了表哥痛苦的脸色,她像被蛇咬了一口似地猛地从椅子上弹起来,心里狂跳不已。再仔细看看,仍然是那张表盘。沈素娥轻轻舒了一口气,暗骂自己疑神疑鬼的太不吉利。站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坐回到椅子上。
一直紧紧关闭的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顾嘉棠毕恭毕敬地往门口一站。
“夫人,先生请您下楼用晚餐。”
沈素娥猜不准杜月笙的用意,但是不得不下去。虽然她心里始终挥不去对表哥的担心,根本没有心思去吃饭,但是也不得不应付一下。而且,不知为什么,沈素娥总觉得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从沈素娥的卧室到杜公馆豪华考究的餐厅,要走过一条不短的廊道。顾嘉棠在前面走着,沈素娥隐约听到路过的一间房门里面传出女人的呻吟和哭泣,可能是因为哭喊的时间太久了,那声音已经嘶哑变调得让人难以置信,在空荡荡的长廊里幽惨凄厉得怕人,时断时续地在沈素娥身边飘来飘去,让她不寒而栗。她想知道那是什么声音,可是顾嘉棠不告诉她。
顾嘉棠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速度,像是什么也没听见似地照直往前走。沈素娥向后看了看,她觉得声音是从贮物间里发出来的,可又不敢确定。这声音让她听得很不舒服,她看了一眼顾嘉棠,不由得脚下加快了速度,逃一样地通过了走廊。
一进餐厅,沈素娥就觉得头皮一阵发麻。
今天的餐厅里没有一点晚餐应有的气氛,宽大的加长餐桌上没有任何东西,只平整地铺着雪白的桌布,顶灯的光从天花板上直射下来,让桌布白花花地反射回来,仿佛是一间大大的手术室,张着空空的大嘴等待着下一个病人。
杜月笙一动不动地端坐在长桌的那一头,屋里的一片白光让沈素娥一下子看不清杜月笙脸上的表情。沈素娥迅速地扫视了一下餐厅,发现偌大的房间里只有杜月笙、顾嘉棠和她三个人,这让她感到阵阵逼人的寒气,联想到刚刚在走廊里听到的痛苦得有些奇异的惨叫,沈素娥的小腿一阵阵发抖,要不是赶紧扶住了桌子,说不定会一头栽倒在地上。
顾嘉棠一把扶住摇摇晃晃的沈素娥,把她搀到杜月笙的旁边,坐了下来。
杜月笙向顾嘉棠挥挥手,顾嘉棠点头出去了。
屋里只剩下沈素娥和杜月笙。杜月笙又取出一只雪茄来,在烟盒上磕了几磕却一直没有点着。沈素娥摸出手绢不停地擦拭着额头渗出的虚汗。
“素娥,现在这屋里就我们两个人了,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沈素娥一言不发,她的脑子确实是在飞速旋转,却什么也想不出来。在这种时候,还是没有任何表示为好。
静默了三分钟左右,杜月笙把那支雪茄又放了回去,烟盒的盖子被他用力一压,“啪”的一响,死气沉沉的房间里这声音显得特别刺耳。沈素娥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机会了,她心里不由一动,旋即又黯淡下来:作为杜月笙的妻子,已经发生的事情无疑都是不可挽回的。她比谁都了解这一点。每一个让杜月笙感到窘迫一时的人,都付出了自己一生的代价,除非,是那种永远也不可能让杜月笙抓住把柄的人——而她,显然不是这种人。从嫁给杜月笙那一刻起,她就注定了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而再也不是自己。甚至,还不如杜月笙身体的一部分,沈素娥只是一个随时候用的妻子,闲下来,也完全可以放在杂物间,仿佛根本没有这么一个人一样。
现在,沈素娥终于让杜月笙知道了自己还有一个不从属于任何人的人,可是,这代价未免太大了。
“来人!”杜月笙咬了咬牙,向门外喊了一声。
从外面走进来四个壮汉,一起抬着一张被单,四个人一人抓着一角,被单里的东西挺重,还在动。四个壮汉把被单一撒手,里面一团白乎乎的东西跌落在地板上。
“瑞兰——”沈素娥失声叫了出来,刚要从座椅上站起来,却让杜月笙一把摁住了。
瘫在地板上的瑞兰已经没有人样,一丝不挂地暴露在这么多男人的面前,却没有一丝一毫羞怯和躲闪。她瞪着空无一物的眼睛,直直地仰望着天花板上的顶灯,已经认不出人来了。
沈素娥往瑞兰身上一看,心里更凉了半截,白皙的身躯布满了一道道青紫、鲜红的抓痕。沈素娥像一头受了伤的母鹿一样,突然回头瞪着杜月笙:“你,你把她……怎么样了!”
杜月笙满意地看着沈素娥,这样的反应让他有一种复仇的满足。“这个奴才不守家规,为了儆诫旁人,我把她赏给底下的弟兄们了。”
四个壮汉脸上露出控制不住的狞笑。
“好了!”杜月笙一挥手,“太太看够了,你们把这堆烂肉给我抬下去,随便找个堂子卖了,得的钱就留给你们喝酒了。去吧!”四个人重新提起被单的四角,拖死狗一样把瑞兰拖出去了。
沈素娥浑身不住地抖动,两眼几乎要喷出火来。等几个人消失在门口,她突然对着皮笑肉不笑的杜月笙嚷了起来:“是我!都是我!事情是我做的,有什么事情你冲着我来!她还是个孩子,是我嫁给你,你凭什么对她这样!你如果有气,你杀了我好了!”
“啪!”的一声,杜月笙一巴掌打在沈素娥脸上,沈素娥向后一仰,差点从椅子上栽下去。“贱货!你还有脸说!你做的烂事,以为我不知道!杀了你……没那么便宜。无论如何,你还是我的大老婆,我杜月笙宽宏大量,不会和你计较的。我要让你活着,看着,让你明白什么叫规矩。当了我杜月笙的老婆,应该守什么样的规矩!当初我说过,我要让你一辈子过好日子,这点我说到做到!你睁大眼睛看着,你不仁,我不能不义,说到天外去,你也是我杜月笙的人。我不让你死,你就死不了……我要让你好好活着……”
沈素娥颓然扑倒在桌面上,动也不动一下。
杜月笙吩咐顾嘉棠给沈素娥上菜,顾嘉棠捧着一只紫砂汽锅走了进来,把汽锅端端正正地摆在沈素娥的跟前,他恭恭敬敬地请师母尝一下那锅里大补的东西。
沈素娥趴在桌上一动不动。她知道,自己已经彻底完了,这辈子也别想再有出头的日子。杜月笙会让她生不如死地度过后半生。现在,沈素娥什么都无所谓,只希望表哥快点逃,听她的劝告快点逃走,逃到杜月笙鞭长莫及的地方,她全部的心愿也就算是实现了。她不想听杜月笙的,也不用听,因为听与不听都是一个样。
杜月笙让顾嘉棠再劝,可沈素娥仍然没有反应。
杜月笙一把抓住沈素娥后脑勺的头发,死命把她的头往上提,沈素娥叫了一声,脸离着那只汽锅只有半寸多远。“嘉棠,把菜给你师母揭开!”顾嘉棠应了一声,一团热气直扑沈素娥的脸上。
沈素娥的头发被杜月笙扯得生疼,不得不睁开眼睛,透过厚厚的水汽,沈素娥看到汽锅里煮着两只人手。
沈素娥大叫一声,伏在桌上吐了起来。
杜月笙又一次揪着她的头发把她的头拎到汽锅的上面,又狠狠地向着那两只煮熟了的人手按下去。她什么都清楚了,因为在汽锅里同时煮着的,还有自己的那挂“丢了”的珍珠项链。
“你看看,你好好看一看。这两只手多美呀,嗯?我本来不想这样,可是这两只手太过分了,它们摸过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我只好把它们留下来了,这难道不正是你想要的吗?现在,它们是你的了……你记着!是你把他的手剁下来的,是你!你哭吧,你哭的时候还多呢。”
顾嘉棠在旁边连大气都不敢出。
“嘉棠,你师母不喜欢这道菜,拿出去喂狗吃!”
沈素娥挣扎了一下,想要说什么,突然眼一翻,歪倒在一边,杜月笙踢了她一脚,沈素娥像一包棉花似地瘫倒在地上,昏过去了。
顾嘉棠端着汽锅正要往外走,杜月笙叫住了他。“嘉棠,这次让你受了不少累,不过我知道你从来是个在人前不善表功的人,所以我才特别地器重你,你师母是偶感风寒,又突然让恶梦惊了一下,就那么一直晕晕乎乎的。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顾嘉棠连忙躬身称是,转身退出去了。
当夜,沈素娥被杜月笙送到了搬家前的老宅,由几个丫环婆子照顾着过起了长达10年的禁闭生活,断绝了和外界的联系,杜月笙对这个突然从上海的社交圈子里退出去的元配夫人,最大的关心是每月按时送来的500元生活费和一盒鸦片烟膏。
这一幽禁就是十年。直到她儿子维藩结婚时,在她的苦苦哀求下,才允许以婆婆的身份出席婚礼。那时,她白发苍苍,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其实,只不过四十有三。此系后话,按下不表。
不动声色而又干脆利落地摘掉了头上的绿帽子以后,杜月笙把二房陈帼英和三房孙佩豪招到大餐厅,问:
“你们知道不知道太太搬出公馆的原因?”
两人摇摇头。
“这骚货同别的男人鬼混,我要关她十年禁闭!”
陈帼英、孙佩豪两人面面相觑,吓得不敢做声。尤其孙佩豪,两腿嗦嗦发抖。
杜月笙故意停住了话头,他要看看自己这几句话的威力。当他看到两个女人在他面前心惊肉跳的样子,心里得到极大的满足,他觉得自己的话已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才从长衫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郑重其事地交给帼英:
“帼英,今后家里的事你要多操心。这是银箱的钥匙。”
陈帼英接过了钥匙后,杜月笙的脸上现了一种似笑非笑、似怒非怒的表情,点上一根纸烟,他抓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我要卢筱嘉先生听电话。”
“我就是啊。”电话里传出了对方的声音。
“啊,卢公子忙啊,我是杜月笙呀!……哪里,哪里,这两天正好赶上外地来了客人,褥接待一下,你关照的事情,我己和老大说过了,这挂项链在这里,你听听,抛起来声音挺悦耳的。”
“这么心爱贵重的宝物,贵太太肯借吗。”对方的口气有些惊讶!
“那是你卢公子面子大,哪有不借之理?我看,是我派人送去,还是你与木兰小姐一道来取?”
“我们马上去府上拜访。”
“好,我杜某恭候大驾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