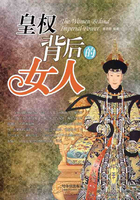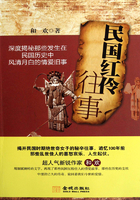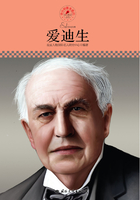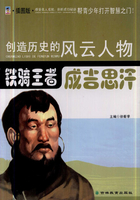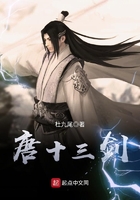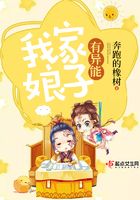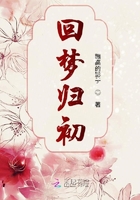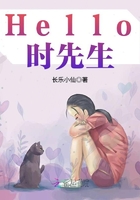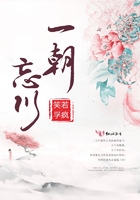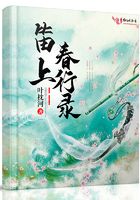1946年秋,蒋政权为填补浩大的军费所造成的空前财政赤字,宣布向小商贩们增加税收。本小利薄的摊贩们不堪承受,纷纷抗交税款,酿成风波。
同年11月,上海数千名摊贩与当局发生冲突,造成“摊贩事件”。对当局肆意搜刮素怀不满的杜月笙对此抱默许的态度。
警察局长宣铁吾见摊贩难以摆平,怀疑是杜月笙在后面撑腰,遂向蒋介石告了杜月笙一状,并以辞职相要挟。
杜月笙被南京方面警告了一通。
无端受气,怎能忍受?杜月笙带着妻妾愤然离沪而去,声称赴港“养病”。行前,他把在杜美路上的公馆,以45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领事馆,表示了他对蒋介石等当局者的愤慨和“眷恋”的决绝。
杜月笙住在香港,听书看戏,倒也逍遥,但蒋介石却坐不住了。国内战场上军费浩大,损失惨重。蒋介石觉得,杜月笙这样的人,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己的统治基础,应当“善待”,不然,不就是有更多的人反对自己了吗?从这一点出发,蒋介石便亲自出面调停,连派钱新之等几批说客,赴港“劝说”杜月笙早日回到上海。
杜月笙迟迟没有回沪,蒋介石又亲自下令给杜月笙的儿子杜维恒前往香港“接驾”。
杜月笙是个死要面子的人,蒋介石三番五次如此这般地请他,他不由得有些飘飘然,认为自己总算还是有些分量的。
1947的3月23日,在香港居留了50多天的杜月笙宣称“病愈”,启程返沪。
几天后,杜月笙一家都回到上海,当晚,杜月笙又乘夜车赶到南京,向蒋介石当面解释了自己的“病情”,并对总统的关怀表示感谢。此举并非画蛇添足,多年来,杜月笙对蒋介石已了解得十分清楚,这个“多疑”的家伙叫他回上海后,若别人放几股坏水,他可能会麻烦的。所以拜访过总统后,他才安然回上海,当起了悠哉闲哉的“一品百姓”。
自杜月笙返沪之后,便开始改变了以前随意挥霍,一手来一手去的作风,“右手来的钱放进口袋中,左手来的钱也放人口袋中”,同时又让其手下紧缩各项开支,家里雇佣的人员也减少了一些。这样增收节流,杜府的财政渐趋平衡。
时间进入到1947年8月,杜月笙又成功地在上海大出了一次风头,这就是他的60大寿的寿庆,当然,这比起1931年的杜祠落成典礼,无论是规模还是气势,都要小得多了。但对于战后的杜月笙来说,算是最轰轰烈烈的大事了。
原来,杜月笙打算像杜祠落成典礼时一样也举行全国性的堂会,来庆贺一番的。但他的一些谋士提出:“单纯庆寿,意义似乎不大。”
杜月笙一听,说:“有道理。”
此时,恰巧两广、四川、苏北等地又发生水灾,杜月笙灵机一动,何不像去年举行上海小姐选举一样,来个祝寿赈灾呢?
他把这个意图一说,得到了手下人的一致赞同。
经过详细讨论,最后大伙决定:把举行堂会演出的收入用来赈灾,而寿礼收入则用来办一个月笙图书馆和编印《上海市通志》。
几个替他捧场的文人,准备在编印通志时,把他过去在上海的一切活动都写进去。杜月笙一向是希望“人死留名,豹死留皮”的,所以,对这件事极感兴趣。
8月1日,恒社成立了“庆祝杜月笙先生60寿诞筹备委员会”,开始编写“杜月笙先生大事记”,并决定这部分经费由社员们分摊。另外,还决定分送寿屏全堂、商请电影厂摄制杜月笙传记的影片。
杜月笙知道这些后,说:“现在国内到处有灾荒,大家还是不要铺张的好。”
说是这么说,但有些事情,铺张得还是很厉害的。
头天晚上,顾嘉棠,万墨林等发起为杜先生暖寿,在北原西路佳庐路的家中,办了40桌最丰盛的酒席,到的有许世英、钱大钧、王正建、郑介民、钱新之、王晓籁、章士钊、唐生明、潘公展等300多人。
席间,章士钊读了他写的一篇祝寿文,这篇寿文是由于右任、孙科、居正、戴传贤、李宗仁、宋子文、孔祥熙、吴敬恒、吴铁城、何应钦等100人联名签字送给他的。在宣读时,不少人当时都感到捧得实在太过分了。
下面这段是写抗战中的杜月笙的,吹得简直有些神乎其神了:
“卢沟变起,海内震动,未达三月,乱席卷千里,浸不可制,如是者相持至于八载,倾之,强敌一蹶不振,肉袒请降,此掺之至坚,导之使然之二三者,其谁手?吾易之,吾再思三。此其人不必在朝,亦不必在军……试问执涂之人而问焉,吾敢日,战时初期,身居上海而上海重,战事中期,身居香港而香港重,战事末期,身居重庆而重庆重者,舍吾友月笙先生,将不知所为名之也。”
其余的贺客中,也有不少极尽阿谀之能事者,有的把他捧成郭子仪,更有人说他的富贵寿孝都超过了郭子仪。杜月笙只是简单地致了答谢。
席间,还由各地来道贺的曲艺名演员说了几段相声和滑稽戏助兴。
第二天,8月30日(农历七月十五日),为寿期,在泰兴路丽都花园中,大家举行了祝寿典礼。寿堂正中悬挂一个比人高的寿字,由上海市参议会全体参议员签名于上。寿幢上面是蒋介石题的“月笙先生,六旬寿辰嘉乐宜年”12个字。
杜月笙的八个儿子都穿着长袍马褂,几个老婆和儿媳女儿等都挂着精巧的寿字胸花。
当天,杜月笙没有去寿堂,他请陆京士、杨虎、徐寄顷、徐采丞、顾嘉棠和范绍增六个人代表他招待客人。
凡去贺寿的人,都可以得到精印的吴稚晖和叶恭倬亲笔书写的寿文和华福烟公司赠的寿烟一盒。汽车前面均贴上“庆祝杜公60寿辰”的小条。当天上海的宪兵、警察、特务大批出动去保护,警察局长俞叔平亲自在门前指挥进出的汽车。
第一个去祝寿的,是蒋介石的代表国府文官长吴鼎昌,接着才是宣铁吾、宋子文、王宠惠、魏道明、俞鸿钧、汤恩伯、郑介民、吴国帧等院长、部长、总司令及金融、工商等界的所谓巨头和社会名流,穿长袍、西服与全副戎装的都有。这天去的汽车有1000多辆,宾客有八九千人,中央电影制片厂还把这一热闹场面摄成了新闻片,在上海等地放映。
除前来祝寿的外,分布在南京、杭州、北平、天津、武汉、重庆、沈阳、青岛、西安、兰州、宝鸡、成都、昆明、桂林、南宁、福州、南昌、苏州、无锡、南通、屯溪、金华、绍兴、台湾、香港以及缅甸、菲律宾等处的恒社社员也纷纷发来贺电。
事后,恒社还将此次各方人士给杜月笙的祝词、屏联、诗文等汇编成《杜月笙先生六十合集》两册,公开出版。
这次表面上说是为了提倡节约,都吃素面,实际上是分等级招待的,一般的贺客只能吃到一碗素面,而有地位的都被请到里面去享受上等筵席。
蒋介石为了照顾影响,也为了表明自己对这个老朋友的好感,除去亲笔题字与派吴鼎昌代表祝寿外,又叫自己儿子蒋纬国领着儿媳到他家里去拜寿,向他行子侄礼。对此,杜月笙感到脸上颇有光彩。
祝寿赈灾的京剧义演,原定从9月3日到7日为期五天,因很多有钱人认为这种南北名角的联合演出太不容易,又要求延长了五天。票价分五等,最高的50万元,最低的20万元。黑市则高达100万元。当时,米价是30多万一石。
10天义演得到了20多亿元。寿礼也收到30多亿元。这些钱都是随收随存于中汇银行,名义上他是一钱不要,但等到把这笔钱捐出去时,米价已涨到50多万一石。
那些因法币贬值所得到的巨额利润,全进了杜月笙的腰包。只是苦了那些演员白帮他一场,而他却名利双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