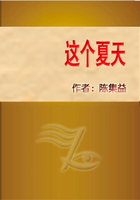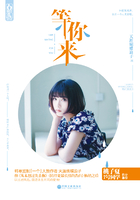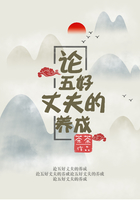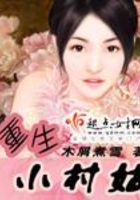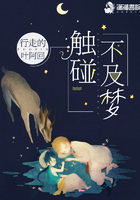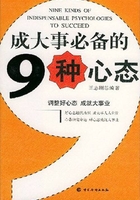通读这几十年关于苏童小说的评论,给我印象最深的依然是王干的那篇《苏童意象》,今天看来,这可能是拿不到任何学位的论文,甚至连论文也算不上。但我敢说,它在苏童批评史上的地位是无人撼动的。王干率先在文章中指出关于苏童小说的红色意象,从最早的红月亮、枫杨树系列中反复出现的红罂粟,到晚近出现的红粉意象。他从“红”和“童”字出发,甚至找出“ong”的韵母总是出现在最关键最让苏童难以忘却的人名和地名里。这篇貌似人物印象的文章,却令人信服地分析了构成苏童小说的三大类意象群,创作经历如何由“我”到“他”、由繁到简的蜕变过程等等,就是今天读来依然有着阐释的诱惑。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丰饶的时期,是一个哺育新思想的温床,思想解放是文学寻求创新探索的催化剂,形形色色的“新”包含学习上的如饥似渴但难免也有生吞活剥的弊端。但那时文风和会风的活泼生动今天已经荡然无存了。文章的不拘一格,会议的七嘴八舌,热烈争论,你一句我一句,大嗓门。以及发言不断被别人打断的情境,大概是今天的学术会议不提倡也不允许的。我不敢断定王干的文章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经过几十年学院的规训治理,此类批评文章的产生已是不太可能了。
王干的文章可贵之处还在指出意象在于苏童小说的地位和作用:“由于意象最初是从诗歌创作领域转借过来的,一些小说实验者基本上仍以诗化的方式进行小说操作,苏童小说仍然过多地化用诗歌营造意象的方式,苏童一些短篇小说却可以当作优美的散文诗进行欣赏。”“而贯串这一连串意象之珠的线绳则是苏童小说那个虚拟的‘我’的情绪自由流动。”[7]王干的文章写于1992年,这年前后,是苏童研究文章的高发期。苏童以其“故事”走红,但研究者的重心则是其小说的意象。直到去年《黄雀记》的发表,岳雯在其两度书写的评论中都感叹,读《黄雀记》都像读诗一样,“在他的回味中,风、云、光、影皆为之而来,每个细节都绽放出诗一样的光彩”[8]。
意象无疑是苏童小说批评史上的关键,自王干率先在《上海文学》发表题为《在意象的河流里沉浮》(1988年)后,光用意象作题的文章就有六、七篇之多。而把意象提高到主义的是葛红兵教授的《苏童的意象主义写作》,葛文认为:“一部《妻妾成群》就是一个意象集,它整个就是由意象组接起来的。由此,意象不仅帮助苏童在小说中塑造了凄清幽怨的叙述氛围,而且它还构成了小说叙述的深层动力。这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绝无仅有的,这种以意象性为基本特征的小说语式完全是苏童独创的,它对中国现当代小说来说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贡献。”[9]这可真是富有创见且锋芒毕露的评说。葛红兵断然否定历史镜像的价值和进化论的意蕴。断言苏童小说反时间的兴趣所在“是那个深深地潜藏在时间的湖底,任凭时间的洪流如何奔驰不复,它却始终保持不变的东西”。葛文发表于2003年,10年后,这一论断在王宏图的文章中再次重提,足见其独特的影响力。
我的疑惑在于小说和诗之间有何区别,小说的叙事语言在本质上如何不同于诗的语言。几年前,我在一篇题为《当叙事遭遇诗》的文章中,试图提出和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意象和意象群基本是一个诗学的概念,它的使用范围包括读者从一首诗中领悟到“精神画面”到构成一首诗的全部组成部分。意象是文字组成的画面,所谓视觉反映也就是“意象”。关于这一点,苏童自己的说法似乎更有说服力。“说到底,可能就是我对图像的迷恋,将其融入了我的小说当中。”“我迷恋电影,却并没有对我的创作起作用,倒是我迷恋的图像对我起作用了……破译图像是我的爱好,这样的爱好势必带到小说当中去,在我的小说中是一定存在的。”[10]我以为,苏童讲的就是意象如何走进他的小说。
三十年前,当代文学中的先锋、实验、探索响应现代主义的美学革命,追随新小说浪潮,我们都一度热烈地投身于对小说线性叙事的破坏性的运作。小说的诗化不仅是一种提法,事实上更是一种小说叙述倾向;把小说写得像诗一样仅仅只是一种现象的形象说法,而如何把诗带入小说,尤其是带入中长篇小说叙事却是一种嫁接、移植和杂交,其难度是可以想象的,其中的变数和异化却是值得研究的。
人生也许很虚幻,但至少它组成了一个故事,故事必然带有基本的结构。这个故事也许讲得乱糟糟,但背后总有一个叙事者,不论他或她多么愚蠢。小说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和故事有着不解之缘。阿多诺曾感叹现代主义挖空了对客观的叙事的戒律的墙脚,但故事还是要讲下去,“所谓讲故事,就是说出点特别的东西来,可是这种特别的东西恰恰被统治一切的世界,被标准化和平均化所掩盖了”[11]。阿多诺显然是感到非故事化给叙述者带来的困境,而不是像有些评论所轻松说说的“诗性未必拒绝故事”。
意象作为阐释或雄辩的敌人,虚假感性的敌人和客观描写的敌人,力图给观念穿上可见的外衣。唐湜这位被钱理群称之为上个世纪40年代最出色的评论家,在其评论中引用汪曾祺早年给自己信中的话,“……我缺少司汤达尔的叙事本领,缺少曹禺那样的紧张的戏剧性。……我有结构,但这不是普通的结构。虽然我相当苦心而永远是失败,达不到我的理想,甚至冲散我的先意识状态(我杜撰一个名词)的理想。我要形式,不是文字或故事的形式,或者说与人的心理恰巧相合的形式(吴尔芙、詹姆士,远一点的如契诃夫,我相信他们努力的是这个)。也许我读了些中国诗,特别是唐诗,特别是绝句,不知不觉中学了‘得鱼忘筌,得意忘言’方法,我要事事自己表现,表现它里头的意义,它的全体。事的表现得我去想法让它表现,我先去叩叩它,叩一口钟,让它发出声音。我觉得这才是客观”[12]。汪曾祺甚至想把自己编的小说集名为《风声》,以表达“风声入牛羊”的意境。我相信,汪曾祺信中的这些话真实表达其小说创作中的美学追求,这也是他的小说叙事少有中长篇的缘故,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小说在沉寂了四十几年后重新焕发其耀眼光芒的缘故。顺便提一下,唐湜是九月派诗人,而上面所提及的葛红兵的文章也自称得益于另一位九月派诗人郑敏写于1993年的文章。此类巧合可能会产生另类的联想。
一方面被称之为讲故事的高手,另一方面在肯定苏童小说艺术成就时讲的又是“他孜孜以求的是与中国传统文学‘诗画同源’精神相通的‘空间型写作’”。这一对立现象无疑是我们理解苏童小说艺术的关键。真正的小说家总是力图使我们切身体验到他的创作矛盾。因此,他使用较为巧妙而复杂的手段,恰在他将世界拆开时,他又将它重新组装起来。人们欢迎苏童的故事,研究的则是他的“意象”:人们喜欢苏童的历史题材,评说的则是其非历史化的写作艺术。耐人寻味的是葛红兵用其“史前史”的人类学角度来对应王德威的“民族志学”,我们感到其中有道难以逾越的裂痕。苏童曾迷恋于塞林格短篇小说中的那个谜语:一面墙对另一面墙说了什么?重要的不是那“墙角见”的谜底,而是苏童是否相信它们迟早会见面。人类学角度虽不是什么新鲜提法,但针对苏童小说创作而言,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提醒。神话批评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少有实践,这也是为什么批评史中的苏童,其面目总不那么明晰的缘由。
戴维·洛奇在其著名的文论《现代主义小说的语言:隐喻和转喻》中说道:“对我来说,雅各布森最有意思的论点是,本质上由连接性所促成的散文往往倾向于转喻而有格律押韵和强调相似性的诗歌则偏向于隐喻,他还提出现实主义作品是转喻性的。”最有意思的是文章结尾处,戴维·洛奇引用了杰勒德·杰内蒂在论述普鲁斯特的论文中的见解,“普鲁斯特说,没有隐喻就根本没有真正的记忆:我们为他和所有的人再补上一句,没有转喻,就没有记忆的联系,没有故事,没有小说。”[13]说到底,什么是小说叙事赖以生存的条件的确是个难缠的问题,何况本质论在很长时期本身也受到了责难。如同有时候不知人生的意义正是人生意义的一部分,说不清楚的纠结之处也许正是本质所在。小说总是依靠着我们难以理解它的根本意义而不断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