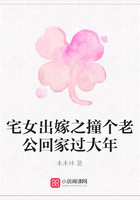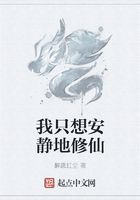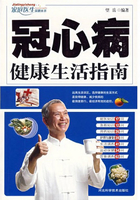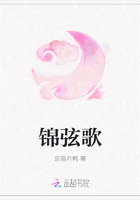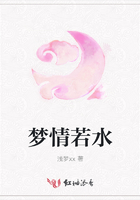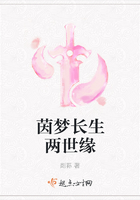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汪政的苏童论,对江苏的作家,汪政是知根知底的。况且这篇总括性的作家论发表于相对比较晚的2006年。题目也很有意义:《苏童:一个人和几组词》。由于苏童小说史的独特性,加上其几十年的创作经历好几个阶段的瓜葛,因此,关于苏童的研究经常会出现一些人们熟知的词语。汪政的几组词总结为:童年/回忆/虚构;历史/现实;南方/女性/唯美/意象。
汪文中最为引人注意的话语是,苏童“用南方美丽的形式来展示南方的无可救药”。“美丽的意象下面是死亡的气息与令人不安的阴谋,它可以视作苏童所有小说的样本。这是苏童作品的秘密,如女巫般带来厄运的美丽舞蹈。”[14]汪政对苏童小说中的童年记忆所作的详尽分析是文章中最具价值的部分,他让我们明白了叙事中的回忆和回忆中的叙事之间的差异性。“总而言之,苏童的回忆不是严格的回忆和真实的回忆,它只能属于虚构。”记忆总是和遗忘联系在一起的。对昆德拉来说,人类对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对苏童而言,记忆既是一种遗忘的方式,也是一种虚构的方式。世界本应是一个整体,个人的记忆总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认识世界的过程,恰恰是一个把整体部分化的过程。苏童把记忆比作索取自身的影子。虽有如影随形的说法,但影子说到底并不等同于身体本身。记忆是可知的,而遗忘是不可知。我们总是穿越不可知而到达可知的王国,但我们能经由可知到达不可知的地界还真是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历史叙事,这在张清华的论文有详细论述,这里不一一展开。叙事语言的指涉问题是个关键,值得一提。苏童小说中的历史叙事是一种虚拟,甚至可以说是去历史化的,这既是苏童的特色,也是其成功之处。“他对一切变化都不感兴趣,他所感兴趣的恰恰相反”,“我们差不多可以说苏童是一个历史退化论者。与这种退化论相联系的是苏童对个体生命,由少年到青年,再到老年的不断提升的认可”。葛红兵的说法有过激之处,但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和苏童在谈到《妻妾成群》时所说的“我不是要写30年代的女人,而是要女人在30年代,这是最大的问题。”相较之下,还是有其相通的地方。
女性形象一直是苏童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也是公认的擅长之处。不知何故,王德威却认为,苏童小说中更吸引人的是那些从未真正成熟的男孩,根本就像张爱玲所谓“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男性的未成熟真正映衬着女性形象的成熟,这也为苏童小说存在着恋姐情结的说法提供了一个微妙的注解。
“唯美”一词经常与虚无一词相伴,几乎可以说是苏童研究中的独门武器,这也是苏童专家张学昕专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用词。我的看法是,唯美主义作为一种美学主张和追求,无可厚非。而作为一种评判性的判断,容易流于极端简单而缺少回旋之余地。
用心理动力学原理来分析苏童的创作发生论,用心理补偿说来求证苏童在虚构世界所获得的自由和满足自有其独到之处。但发生论并非万能,补偿说也不宜简单化。说什么“幼小的童年已经有一种日后补偿的潜意识”;认为“写作是生活的补充,也是内心的延伸”,姑且能自圆其说。但认为现世幸福的苏童,就意味着安逸的生活和自足的内心,就会失去书写苦难的条件,并以托尔斯泰晚年出走为例就难免有牵强附会的离谱。多少年了,文学界对托尔斯泰伟大的理解够机械了。别的不说,晚年的托尔斯泰在回顾《战争与和平》时就说,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叫读者开开心。天才身上总有一种怪癖,即自我主义反过头来最后的一口喘息,有时会使天才贬低自己的杰作。当然,在托尔斯泰身上,我们可以用他的宗教信仰来解释他的反常判断。自从他皈依宗教之后,他把《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看作价值不高的世俗之物。他也说过《战争与和平》描写的是一个民族的漫游。这倒有点“补偿说”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