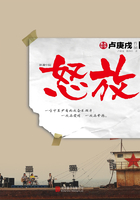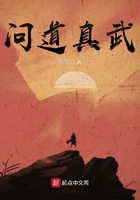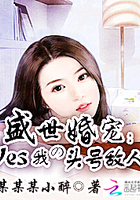票房用的外院南屋是穆先生的书房。平日一般朋友来访,就在这里接待聊天。
夏天热了,票房就挪到里院的葡萄架下。
一张八仙桌子上面,放着细瓷茶壶与八只茶碗。壶里沏的是茉莉白毫,虽然不是上品,北京人惯常喝的茶叶末儿,也是没法儿比的。加上穆太太的茶碗洁净得发亮,来这儿的人品茶都是行家。从倒茶,端碗就看得出来,轻而虔敬。另外的两个小盘子里盛着穆太太亲手做的玫瑰枣和盐栗子。拉琴的与唱戏的都围在桌子四周。
常来这里的人有魏太太,唱老生,顾太太唱青衣,穆先生唱小生,再有就是不怎么常来的李先生唱老旦,唱老生的陈先生。
拉京胡的王先生,是位读了些书的旗人。近四十岁了,却不工作。京胡拉得好,字画也好。穆先生票房里只有王先生这一把胡琴,因此他是每次必来。
票房里唱戏的人,还得先说顾太太。
京剧以四平调为主的戏并不多,因柔婉平和的韵味广受喜爱。
票友不像专业演员那样以戏会多少论高低,票友一般只精通几出戏或几段戏,因此专业演员向票友请教某一段戏是常有的事。
顾太太只唱四平调。而且唱得好。
四平调的戏,有《醉酒》《梅龙镇》《坐楼杀惜》。多是男女情意缠绵,或悲啼或娇嗔。
顾太太唱四平调回回掉眼泪。只见她一只手敲着板眼,另一只手捏着手绢擦眼角。虽说唱得动情,板眼,调门一点不走。王先生的胡琴拉得也好,帮得严丝合缝。看王先生盯着唱主儿的眼神就知道,甚是上心。
从自然灾害时,顾太太就开始唱《贵妃醉酒》了。她的嗓子不亮,却相当柔和。
当唱到“你若是顺了娘娘心,如了娘娘意,我便加封奏当朝……”顾太太便开始擦眼泪了。
这出由杨贵妃一个人唱的戏,说的是皇上本约了她,后来又变了主意,转向梅妃那边儿去了。于是她伤心得要命,就向高,裴二位力士要酒喝,想一醉了事。
一段唱完。王先生连忙把胡琴放在一边,站起来倒了一碗茶送过去。含笑着轻声说,润润嗓子吧。
顾太太接过茶来用嘴抿抿就放下了,再朝王先生微微点头示谢。坐下来后,掏出手绢蘸眼角上的泪。
这时魏太太起身,朝王先生欠了欠身,满面笑容地说,王先生,您先歇歇,喝茶。
王先生没抬头,笑着说,不用,您来段什么?
魏太太赶紧上前凑了几步说,还是《捉放曹》吧。长了点,让您受累。
王先生开始试调门。
这位魏太太四十多岁,烫着满头的大波浪,如一片片玫瑰花瓣扣着。显见,对自己的年龄不怎么甘心。细而长的眼睛,其实很有味道,只因戴着金丝眼镜,平时又不太爱笑,神色显得凝重。
她身上的旗袍裁剪得非常合身,做工也得说相当精致。就因这合身,凸起的小肚子与浑圆的肩膀,自然全显现了出来。到底比顾太太大了十来岁,再要强岁月也是不饶人。
胡琴响起,魏太太挺直了身子,等过门,用手随着胡琴打板眼。
魏太太唱捉放曹,也是家常便饭。因为唱熟了,声情并茂,韵味很足。人们都跟着敲板眼,张着嘴,睁大了眼,小心细听。
“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背转身,自埋怨,我自己做差。这才是花随水,水不能怨花,到此时我只得暂且强忍耐在心下……”
唱着唱着,魏太太的眼睛泛起一层泪光。
她唱的本是陈宫骂曹操不义;曹操落难了,逃到吕伯奢家里,吕家杀猪宰羊地款待,曹操却疑心人家向官府告密,便把吕一家杀尽。曹操的翻脸不认人世人皆知,但魏太太能动情到这份儿上,也似有说不出道不明的话。
魏太太唱完坐下,用手绢轻轻按着脸上的汗。这时,顾太太站了起来,向众人告辞。
每回一到四点,顾太太就急着回家。她先朝穆先生点头道谢后,又转身向魏太太说,您唱着,我先走了。说罢向外走去。
王先生的眼睛舍不得离开顾太太的背影,顾太太消失得看不见了,他的目光也就暗了下来。
听见顾太太道别,魏太太忙把看着王先生的眼睛转向了往外走的顾太太,恰好顾太太正抬腿往门外迈,扭了一下腰,纤细得实在好看。魏太太嘴里边向顾太太说了句“帮我看看火炉子”,手却伸到自己腰间,在旗袍上捏了一把,皱了皱眉,埋怨自己身上的旗袍裁剪得还是肥了。大门外这时传来了顾太太一声”哎”。
顾太太走后,任谁再唱,王先生的胡琴就是自娱自乐了,刚才那卖力气的劲儿全然不见。他这么一来,众人怎能不想,顾太太要是不来,其他人即便唱,情绪也不会高到哪去。
顾太太在众人心里越发有了一层神秘。自然又引出了另一个话题:她的那位顾先生,不知是什么样儿的人物?常常在顾太太走后,有人便想起这个话题。
顾先生不在北京,这里的人都知道。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丈夫不在身边,最让人感兴趣。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对她上心,恨不得把她搁在放大镜底下看着,更有无事者议论起她便有枝有叶,乐此不疲。
终于有一天,在众人正说得起劲时,穆先生按捺不住,朝大门外指了指,压低了嗓子说:以后千万别提这些了,我琢磨着也许在那边儿呢。几年了,咱们眼瞧着她一个人守着瘫在床上的婆婆,那么尽心地伺候,真难得。各位说是不是?
听了穆先生的话,有人点头称是,也有人的脸“刷”地红了。
说“那边”,几岁小孩子都心知肚明,指的是台湾。这是大忌,谁听了也得戛然噤声。
顾太太家搬来最晚,因此,顾家是什么家底,没人知道。
穆先生夫妇对顾太太很知心,说这样的话,是为断了这些无止境的议论。按说也不过是街坊邻居,能对她这般慈祥与体贴,连顾太太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与穆太太相识是在西单菜市场。刚搬来没多少天一个早上,顾太太站在卖肉的柜台前想给婆婆挑块嫩点儿的肉,可是看来看去案子上摆着的都不可心。正犹豫着,旁边有人递过来一块说,您看这块怎么样?顾太太看是块有肥有瘦的五花肉,忙扭过头去说,这多不好意思。抬眼看,是位神态安详五六十岁的太太,看着很眼熟。就说,我看您真眼熟,您是住在……?
是呀,咱们住得不远。穆太太忙说道。
顾太太就此结识了穆太太。她们俩都不爱串门,在街上碰见了,就那么站着也能说半个钟头的话。
可是,顾太太去穆家票房唱戏,是魏太太极力怂恿,又亲自过来和老太太说才去的。
顾太太和穆太太几次来往后,觉着有点儿蹊跷,就和婆婆说,穆太太怎么总是不错眼珠儿地看我呢?婆婆说,许是和她家谁像的缘故。顾太太想了想说,也许吧。我第一次见穆先生,他也是先呆了一下,接着就说,像,像。
婆婆又问,你老去他家唱戏,像谁啊?顾太太又想了想说,在他们家没遇见过谁啊。
虽然不明就里,穆先生夫妇确实对顾太太很上心地关照着。一晃几年过去,顾太太也就习惯了穆家夫妇对她的宽厚。
顾太太周而复始地唱四平调,人们都以为因梅先生的四平调韵味好,顾太太因此爱之极。有时别人再三请她唱一两段新鲜的,她就是唱了,听得出来也是敷衍。
《霸王别姬》,凡唱青衣的都喜欢。里面没有四平调,那是一出必然决绝的戏。
“君王意气尽,妾妃何聊生。”虞姬的哀叹。走上绝路了,再无团圆可指望。这样的情景顾太太似乎忌讳,她从来不唱。
《乌龙院》说的是宋江的妾阎惜姣与他的徒弟张文远私通的事。全本都是四平调。顾太太原本不会,王先生殷勤地怂恿着,说是很活泼的一出戏,唱唱吧。盛情之下顾太太不好意思再推辞。
“宋江啊宋江,你今天要是不休了我……”这是阎惜姣心里装着张文远,与丈夫实在没有耐心了。
只唱了一次,顾太太就说:我怎么不记得梅先生有这出戏呀。从此不肯再唱。
那天顾太太刚一出门,背后的穆先生就说了,看样子这孩子是铁心了。王先生听见打了个愣儿,穆先生这话让他的脸红了一阵子接着又白下来。
王先生琴棋书画是没说的,样样拿得出手。就是懒得出去做事,据说是受不了那份管制。旗人家的少爷,祖上但凡留下点财产,出去工作的人极少。今天有吃有喝,就不想明天怎么着。于是,家里的东西一件件地少,全靠着典当过日子。
王太太是他小学同学,娘家父亲开小修表铺子,是实在过日子的人家。偏偏就喜欢上了游手好闲的王先生。中学一毕业,哭着喊着嫁给了王先生。
按说娶媳妇是自己一辈子的事情,王先生照样懒得操心。没有费一点神,这个家就成了。
生了两个孩子以后,白白胖胖的王太太便出去工作了。按她从小受的家教,王先生就这么坐吃山空地过日子,她沉不住气。两个大人吃了上顿再想下顿的辙还行,孩子饿了可是不等大人现去找钱。好在王太太有点文化,就去了一家商场当了会计,虽然挣得不多,可兜里按月有钱装进来,她心里踏实。
自己在家闲着,太太出去上班,在那个时候并不多见,王先生却依旧很自在。每天早上起来先沏上一壶茶,接着就是画画儿,拉胡琴,睡中午觉。一样也不耽误。
茶叶,由王太太买回来。以前是喝八毛钱一两,现在降到了两毛钱一两,他从不问为什么,心里明白,要是有钱王太太绝不会让他喝贱的。
众人都说王先生命好。尤其是魏太太不止一次当众夸奖,说,王先生吉人天相,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王先生当时就笑了,说,这都是我们老爷子说得好,一个大清朝让个女人几十年就给毁没了,咱们冤得慌不是白耽误工夫吗。我爷爷那辈儿还捡着点儿剩儿,到我们老爷子的时候就差多了,可是他们就是想得开,照旧自在。我琢磨也是应该这么个活法儿,人活一天就得自在一天,要不然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
王先生觉得自己说得很有理,细白的脸上泛起了一层汗,油晃晃地闪着光。
其实,现如今的王先生不过算是个城市贫民。他老祖宗留下的几座院子,早就卖得只剩下一间小南屋,老婆孩子都挤在一块儿住着。可依旧是要面子。鸿宾楼,砂锅居是不太挂在嘴上了,可炒肝儿和麻豆腐是味儿不是味儿,还得常挑挑毛病。
王先生刚来穆先生的票房时,穆太太就迎上去,说,您在旗,我这儿失礼的地方您多担待。
其实王先生在穆太太心里很一般。可是,但凡来这儿唱戏,都为了满足自己这点嗜好,甭管唱得好坏,人人心里先轻松愉悦了。所以穆太太在面子上,始终是客气地应付着他。
王先生这时挑起一个玫瑰枣儿,搁在嘴里,说,您这枣儿做得真地道,煮得够火候儿,玫瑰的味儿正。说着又挑起一个放到嘴里。
八旗子弟王先生真错了。他什么事儿都知道,就是不知道穆太太是燕京女子大学家政系毕业的。
人们不挨饿的日子还没两年,1966年便到了。中国,这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上,又一场生与死的风暴开始了。
到了六七月,多少人开始惶惶不可终日。
一天晚上,穆先生在喝着酒,唱着戏。现在饭间只唱《罗成叫关》,把《白门楼》的吕布也放下不唱有些日子了。
“……三王元吉挂帅印,命俺罗成做先行,黄道日不叫俺出马,黑道之日出了兵,从辰时杀到午时整,午时又杀到黄昏,连杀四门我的力已尽……”
穆先生在为罗成难过。三王元吉一心害罗成死,征战了一天的罗成要收兵回城,元吉下令四城门紧闭,不让返回。罗成只得一次次再杀入敌阵,最终战死。满屋子回绕着罗成临死前的哭泣。一曲终了,穆先生喝干盅里的酒,又斟上了第二盅。
先抿了一口,放下,闭上眼睛,起过门。还是那一段儿,重来一遍。穆先生现在唱《叫关》,没了罗成的悲愤,只有凄惨,字字句句凄惨到怎么想也是没有活路儿。
“银牙一咬,中指破。十指连心痛煞了人,启奏秦王有道君……”
最后的罗成,咬破手指,给皇上修了一封血书,可见罗成当时对皇上还抱着希望。唱罗成的穆先生,没有这份激情了。
这时有人敲门。随之听见穆太太连连地说着,快,快请进。让进来一个人,穆先生睁开蒙目龙的眼睛,定了定睛,昏暗处站着的是顾太太。
票房是早就停了。“各位,咱先看看形势发展再说,别往枪口上撞。过些日子要是没什么动静,我再去登门拜请。谢了。”一向谨慎的穆先生说这话时,满脸的歉意。
自从《海瑞罢官》是大毒草,传统历史戏统统定为四旧,写剧本的和唱戏的死不少人了。保命要紧,争先恐后地砸烂还来不及呢,谁还敢唱?大家连声说是,就赶紧散了。
三个月过去了,来票房的人从未相互走动过,都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是穆先生在暗中关注着,他关注着这一方每个人的命运。今天顾太太夜间来访,必然有事。
穆先生站了起来,请顾太太坐下。
坐下后,低头用手理了理头发,似乎在想如何开口。片刻,哑着嗓子说,穆先生,咱们的票房再唱一回吧。
听了这话,穆先生吃了一惊。
顾太太接着说,您这里高墙大院的,咱们小声点,外面听不见。
穆先生摇头。
顾太太又说,要不,咱们不用胡琴?
穆先生低头沉思。
她又低声说,让您为难了。可是,可是……您看,以后恐怕是再也不能唱了。她滴下泪来。
顾太太的话,像是往穆先生心里塞进了一块铁。再看她面部多少有些扭曲,嘴角颤抖着。穆先生沉思一会,终于狠了狠心说,好,就最后一回吧。
穆先生敢答应这事,也是有原因。穆宅周围的几条街上,有几户被揪斗,抄家,也死了人,至今造反派没有找他。他不知道是大祸临头的前夕,还是像五七年反右运动,他能平安躲过一劫。
他问顾太太,请谁来呢?
顾太太说,都问问吧。
穆先生说,咱往最坏处想,弄不好要赔上身家性命的。说完用眼睛看着顾太太。顾太太的眼圈又红了,低头不语。
片刻,她抬起头说,我看现在还不至于,您心里觉着不踏实?要不然就……
穆先生打断了她,说,一个都不能不问。我去请吧。
顾太太眼神儿又像孩子般散散地发愣,她似没听明白穆先生的意思。穆先生见了又叮嘱她,千万别泄露出去就行了。
顾太太脸上有了喜色,轻轻地推门往外走。穆太太跟出来送,拉着顾太太的手,说,往宽了想吧,闷了就来坐坐。
听了这话,顾太太又落下泪来,使劲儿攥了攥穆太太的手。这样客气的话很久没听见了,她再单纯也明白,这是什么时候?人人自危,草木皆兵。自己身世不清且又单身,谁敢这么招待她?
为了掩人耳目,穆先生把这次票房活动安排在天一擦黑;要是晚饭后开始,又怕夜深了太安静外面听见。
穆先生请人时是这样说的,您要是有工夫,咱们凑一回,唱唱《红灯记》。要是没工夫呢,一点儿也不要紧,以后再说。
没料到,接到邀请的人全来了。既是清唱用不着胡琴,拉胡琴的王先生比谁来得都早。
和以前不一样了,无论男女一律中山装,或灰或蓝。王先生更有乐儿,穿了一身草绿军装。这款式,这颜色穿在他身上,谁见了都忍不住想笑。
此时还没有大乱,穿草绿军装的只有红卫兵造反派。后来,军装与造反,成为这世界的主题时,成分好的与不好的就纷纷穿了起来。或是表示要革他人的命,或是表示要革自己的命,还有的是想蒙混过关,于是,满街满巷便是草绿色军装了。
王先生是出了名儿的公子哥儿,浑身的劲儿总是松懈着,与这草绿色实难相配。像皮影戏里的人儿,假模假式地摇晃着。
顾太太依旧如故。一袭海昌蓝绸旗袍,高跟鞋配了长筒丝袜。还是那么飘逸。一块丝手绢拽在左边衣门上,等着擦眼泪。
让所有的人没有想到,场面比从前还热闹,一段接着一段唱,满得很。按穆先生的安排,两个钟头很快就过去了。
她是挨到最后才唱的,自然还唱四平调。今天她不用着急回家,半个月前,她把婆婆送走了。婆婆临死前,一直攥着她的手不放,人都咽了气还攥着呢。
顾老太太到了火葬场,两只眼睛照旧睁着,真是“不闭眼’。多少人上去抹,就是不闭上。往日,街坊四邻都找她说说家常,她和颜悦色地三言两语,就把人家愁了几天的事情开导了。原来这豁达都是让人看的,心里的悲伤一丝没露出来。如今挺在这儿了,人们才见着她的真相。还是在等儿子。死都不闭上眼!
年轻的顾太太哭得几次背过气去,人们拉着劝着,怕她真跟了老太太去。
现在就剩她一个人了,心里有话和谁说去?唱吧。
“可恨李三郎,狠心把奴撇,让奴挨长夜……”这是杨贵妃在《醉酒》中最后的一句唱儿。
因为是清唱,人们听得清,唱到最后这句时,她号啕了。
她唱的还是四平调,还是《醉酒》,还是爱与恨的话儿。不知为什么今天这么一唱,顾先生显得更遥远了。
大家嘴上劝着:老人家就算是有福了,您节哀吧,别哭坏了身体……其实心里都明镜儿似的,不能再多说就是了。
顾太太的哭声未落,魏太太却走了。走的时候没有和谁打招呼,宽大的中山装穿在她身上,越发不合适,旷旷荡荡的。顾太太哭得这样伤心,魏太太只敷衍地劝了劝就走了。这让众人纳闷儿。也许是跟顾太太熟的缘故?也许是怕动静太大给自己惹事,就先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