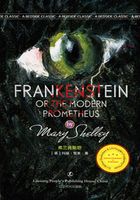如今的孩子,再有想象力,也无法想象到我们小时候竟然经历过那种“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野外生活,真的感受过那种“毡帐秋风迷宿草,穹庐夜月听悲笳”的情景。头伸在外面的时候,吸着凉飕飕细丝丝的田野里的新鲜空气,胸里便填满了一种惬意;头缩进被子里的时候,就能闻到从母亲身上散发出来的温暖如吻的气息。
男人睡在小南山的岗头上,那片岗头事实上是一片坟场,此时坟场的坟茔还不多,只有史家和李家的两座祖坟。一年后,这片坟场全都挤满了,整个后庄以及史仓有一小半的大人、小孩——王三妈、吴秀英、黑头、琼子、枣子、小孬子等,都埋进了这里,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女人睡在田坎下,小孩子们基本上都跟女人睡,除了没有妈妈的癞子。
我们仰面躺在稻草上,盖着从家里带出来的被子,看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想象牛郎织女的样子,想象嫦娥玉兔的样子,吸着凉凉的夜风,感觉在这样的大床上睡觉,真比过大年还要令人激动!
第一天的晚上,我们兴奋得几乎没法入睡。黑头和琼子就睡在他妈妈的身边,他妈妈就睡在我母亲的旁边,本来我们是可以睡到一起的,因为所有女人和孩子们的稻草全都是顺着田埂铺成了一溜条儿的,但母亲们都不让,说如果让孩子们都睡到了一起,那就“炸鼓疱”了,意思是说我们会打闹干轰让她们不好收拾归拢的,于是,各家的孩子都让大人用身子给隔开了。
那天晚上的月亮是那样的圆,那样的亮,在鱼鳞云里急匆匆地往前走着……半夜醒来,累了一天的大人都睡着了,男人们的鼾声若续若断地从小南山的那边传来,女人们的鼻息声虽然杂乱,但夹在数不清的蛐蛐和各类小虫子的叫声中,却又是那么样的好听。
有小便,不敢起来去解,就憋着,憋到实在不行了,钻出被窝就地解决了,很舒服,再也睡不着了,仰面躺着,看天上。我真真实实地听到了从月亮的身上发出了叮叮咚咚的清脆的铃铛声,那响声与姐夫形容“远铃”的声音一样,也与菊子被大红花轿抬走时渐渐远去的唢呐声一样,或许就是穹庐帐外之人意象中的“明月悲笳”吧,它是响在风中的,它是响在人的心里头的……悠悠忽忽,续续断断,似有若无,朦胧诡异……让人着迷,又让人着慌,你没办法去看见它,更没办法去抓住它,可它分明就在你的头上,就在你的身边,就在你的心里头……又在你想象不到的远处飘曵着,忽闪着,流淌着……
想到表姐曾让我和黑头破过的一个谜语:
一个姑娘生得能
十四五岁长成人
算命打卦寿数短
三十坎儿没运程
二十八九命归阴
自我们住到田野里以后,没有吃上一顿熟饭。
按照上面的布置,要把每块田里的表层土连同它的硬板底子,都用锹深挖起来,起出一块块大土碴子,用这些大土碴子垒成一个个空心的土丘,大人们称之为“包子”。将稻草和谷壳之类塞进包子的空心里,点上火再闷上土,任那半着不着的火在“包子”里熰。这样的做法被叫做“烧包子”,说是被烟火烧燎过的田土就有肥性了。
这个“烧包”后来竟然成了乡下人的一个专用名词,用来形容某个说话做事过分、又不着调的人——“呵呵,那家伙啊,烧包一个!”“唉!你这人真是一个活烧包!”它所表达的比“二百五”的意思还要丰富还要复杂。
一时间,在乡下行走的人,所过之处,都能见到一块块田一片片地上垒了一个个这样的大土丘,到处烟雾弥漫,整个世界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土包子,被“烧”了起来。
到了煮饭的时候,将某个包子顶端的土块揭开,把锅坐上去,烧水,煮饭,炒菜……
在那空荡荡的田野里没遮没拦的“包子”上,坐上的锅无法聚热,下面烧火的锅座子又都是从田里才挖出来的湿土块,柴草在里面根本无法烧成像样的明火,大锅里的饭往往是下面糊了,上面还是生米。菜干脆也不炒了,就吃从家中带来的生咸菜。
安徽的二月,基本上还在冬天里,把人都搞到野外去生活,住惯了家园内室的人怎么能受得了!几天下来,连冻带糟蹋,孩子们开始拉肚子,大人们也都开始生病。
我们家的被子够用了,盖得厚实些,情况还好,但像王三妈和小孬子娘俩,都只有一床破得连不成片的被絮,怎么能挡住深夜的寒风!吴秀英一家五口人也只有一床被子,平常在家将三个孩子夹在中间,大人围在外边再盖上棉袄棉裤,冷是冷点,但不至于冻坏,到了外面,没办法焐热自己和三个孩子,而此时的吴秀英和我大姐一样,也怀孕了。
从小就有点挑食的我打死也不愿吃夹生饭。烧锅的王三妈就从锅巴中找些不太糊的地方给我,两天吃下来,我的腮上都起了火泡。
黑头非常能吃,他的饭量几乎比大人还大,一顿三碗饭,囫囵倒咚一会儿就吃完了。我就不明白,那些生饭他怎么能咽得下去。
蹲蹲站,蹲蹲站
一碗锅巴两碗饭
干饱了,干饱了
不给大风刮倒了
半桩子,半桩子
肚里别个饭仓子
食猴子,食猴子
下颏有个嗦楼子。
大雨整整下了两天两夜,大雨过后,田里的“包子”全坍塌了,我们总算可以住在家里了,但大人们为了那些一鼓堆一鼓堆的土丘伤透了脑筋……
记不得我们在田野里究竟住了多少天。开头的日子里我们玩得很开心,但几天下来,孩子们的新鲜劲过去,都闹着要回家,因为在那全是土块和烟火的田地里实在找不到再好玩的东西了。事实上大人们更想回家,他们总是请不了假,想回家拿件东西都不让,听到我母亲和王三妈一边嘀咕一边叹气:“这日子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下雨了,而且一开始就下得那么大,这样的雨在二月里还真不多见。大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向孩子们身边跑,孩子们全都吓傻了,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小孬子离我们不远,看见下雨,赶紧向我们爬过来。他跪到地上把睡在稻草里的远铃和勇子护在了怀里,用后背挡住噼噼啪啪打下来的雨点。小孬子虽然智障,但他的心地比谁都善,关键时候,他首先想到要保护最弱小的孩子。
是枣子的姐姐桃子带头向村里跑去的。村子里只有桃子的父母没有被赶到田里,他们一个是瞎子,一个得了咳嗽吐血的病,都说那病逮人(即传染),让他们留在家里,准许桃子每天晚上回去看看他们。
桃子从田坎下拿了她家的被子,飞块地向村子里跑去。桃子跑了有一箭远的时候,田里所有的人都跟着跑了起来。大姐挑了远铃和勇子,母亲挑了我和家中带去的两床被子。我坐在母亲担土用的竹簊里,双手抓住竹簊的绳系,那种被挑起来悬空的感觉很新奇,田埂的草和田里的水在我们下面呼呼啦啦地穿梭而过,那种类似飞的感觉使我头上冰冷的大雨变得不再那么讨厌和可怕。
大雨整整下了两天两夜。大雨过后,田里的“包子”全坍塌了,我们总算可以住在家里了,但大人们为了那些一鼓堆一鼓堆的土丘伤透了脑筋。要把它们都整平了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那些土块的下面还压了许多没烧尽的柴草。清理这些柴草真比在脏婆娘头上逮虱子、比在草丛里找针还要难,好多柴草都带柘刺,当时是准备全烧掉它们的,如今没被烧完,被压进了土碴下混在了烂泥里,不清理出来,到时候人们光着脚丫下田栽秧割稻,扎了脚板心可不是件小事!然而要完全清理出来又谈何容易,太多了!太乱了!
最要命的是这时上级又有新指令下来,要“深耕细作”。所谓的“深耕”,就是在翻挖田泥地土时,要超过原来翻耕深度的两倍,甚至还要更多;所谓的“细作”,就是把田泥地土碾碎达到“面”的程度。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就是:
沟直如线,地平如镜,土碎如面……
大人们在深耕上面吃尽了苦头,拉犁的牛也吃尽了苦头。想想原来那种翻挖,已足以保证庄稼根部的盘扎和吸收需要了,每年施入的肥料也只能在正常的深度起作用,超过了,那就是板结僵硬的基土,庄稼人称之为“硬板底”——将硬板底翻到上面,把原来适宜庄稼生长的墒土盖到下面,那要费怎样的力气才行,犁头扎得深了,牛拖不动,使牛人就使劲挥动牛鞭打牛,好多老牛就那样被活活累死在田里。烧包子时,就干脆利用人力翻挖。无论是人深挖还是牛犁深挖,都严重地破坏了原来的土壤墒情。
故乡龙穴山地属江淮分水岭上的一个丘陵地带,水田和旱地各半,水田都是梯田,弯弯曲曲的,平面积非常有限,如何能做到沟直如线!江淮地区的田泥和地土多为黄黏土和黑黏土,黑黏土又叫黑码矸,土质非常僵硬,把这些僵硬土块拍成粉末,淋雨后便结成更大的板块,不仅不利于庄稼扎根,也不利于植物根部通风,不利于水分的保存和渗透。庄稼人用尽了所有农具家伙,却怎么也整不出“沟直如线,地平如镜,土碎如面”的效果来。三天两头有工作组下来,有检查团下来,验收不了,队长就要挨批,队长挨批,社员就要倒霉。最后不得不让所有的妇女都带上洗衣服用的棒槌,将男人在前面已经用锹拍碎的土再用棒槌敲成粉尘——那个细作劲,哪里是在种田,简直就是在绣花,在绘画,在作孽!
我有一分钱
骑马上苏联
苏联老大哥
请我听广播
出了一身汗
背回一个原子弹
那天表姐拿了棒槌正要和黑头妈一起去地里干活,刚出村口就被两个城里人堵上了。
来人的脸色非常难看,按我母亲的话说:那脸寒得都能刮下溏鸡屎来。他们说表姐还有好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没向组织交代清楚,她家在美国在台湾的社会关系也没有交代清楚,她必须回去进一步接受审查。
表姐和黑头妈只好回了家中。
表姐进了她睡觉的里屋,一会儿出来了,又像来时一样,穿上了她那好看的大衣,放下长长的辫子,辫梢上又打上了雪白的蝴蝶结。
表姐出门的时候,黑头妈哭了,放声大哭。
表姐反而显得很冷静,甚至还冲黑头妈笑了笑说:“我没事的,表姑,多谢您这两个多月来对我的照顾,我回去把事了了,还要回来的。”
到村口处,看见被吓得躲在大黄栎树上的黑头,表姐仍然是笑着的,向黑头招了招手,让他下来。
黑头下来了,表姐掏了掏自己所有的衣兜,什么也没有找着,最后从头上取下一只发卡——那只黑白双色拧成一个麻花状的塑料发卡,曾让史仓所有女孩子都着迷不透、艳羡不已(不包括我,因为那时我还留着光头,“不是”个女孩子)的塑料发卡递给了黑头。表姐把那只发卡递给黑头时,我们看见表姐的眼圈儿红了。可表姐还是装出笑的样子,凑近黑头的耳边说:“等你长大了,把这只发卡送给你的新娘子——你会成为一个男子汉,成为一个好爸爸,成为一个好爷爷的……”
黑头接过了发卡,愣乎乎地一句话没说,手僵了似的伸在空气中,动也不动,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表姐慢慢地转身,走开,一步一步地,走远了……
表姐走后不到十天,黑头家就接到城里来信,说表姐喝药自杀了。说她吃了满满一大瓶子的安眠药,睡死了。还说表姐吃药前写了一大摞子书信,告诉别人,她不是反革命,不是跟左派作对的右派,更不是什么台湾或美国的特务,她只是一个想好好学习毕业以后报效祖国的大学生,一个对未来充满信心充满希望的女孩子,她说她还没开始处对象,她为自己的不白之冤感到遗憾,感到绝望……表姐临死之前,为自己穿了一身白衭绸的衣裤,辫梢上扎了白色的蝴蝶结,躺在床上死去了。
黑头来告诉我这个消息时,哭得漭漭的,当我知道我们再也见不到表姐的时候,我也哭了。那年表姐18岁。
一个姑娘生得能
十四五岁长成人
算命打卦寿数短
三十坎儿没运程
二十八九命归阴
自此,全部实行军事化管制,村与村、户与户之间掺混打乱……我至今都闹不明白,这个家为什么要那样搬来挪去的,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不知是因为那场大雨,还是上级又有了新的指示,反正“烧包子”没再继续下去。我们回到家中,安静了一些日子。
不多久,大概是午收过后,天气已经热了,那天又开会了。这次开会的地点搞到了大稻场上。来开会的人除了史仓和后庄人之外,还有邻村小郢、中郢、老郢、祠堂、新圩、汤老庄和董楼村的人。大稻场上坐满了数不清的男男女女,这是我童年中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多的人集中在一起,比过年时在戏场上见到的人还要多。
那台子搭得也比戏台大,台子的后面竖了几根长长的杆子,杆子上插了三面旗子,还有一个大牌子,旗子和牌子上面都用黄色的粉写上了字。我不认识那些字,但后来我知道,那三面旗子上写的是: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牌子上写的是: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大会还没开始,黑头、枣子、癞子、如意、云英、大高毛和小高毛还有双喜围着稻场的边沿追逐嬉戏,他们的叫声和笑声把大人们聊天的嗡嗡声都盖住了,枣子嗓眼尖细,叫起来跟吹哨子没什么两样。
那天我有点发烧,萎在母亲身边不肯走开,就在母亲哄我去跟孩子们玩玩的时候,不知是由于发烧引起不适让我出了问题,还是母亲压低嗓门撵我走开的话语给了我特殊感受,或者就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其他原因,突然间,我像掉进了一个没有出口的真空中,从内心里生出一份害怕来,在那黑压压数不清的人头上面,看到了一大片黑色阴影,一种说不清是什么东西但非常令我恐惧的阴影,它像一个巨大的翅膀,黑色的无形的翅膀,将天地打包,我被包在了最中间。就像幼儿时在史家绣楼躲避毛人水鬼时一样,憋屈得几乎不能正常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