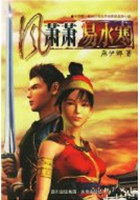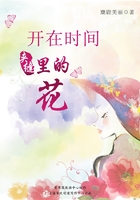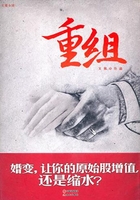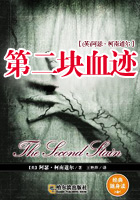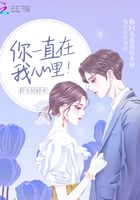苏巧来到陵下那一年,刚好是七岁。在乡下,七岁的女孩一般都知道好歹了,苏巧呢,比别的孩子更多些知道。早上,她爸上工时,跟她妈咕哝一声:“叫她看家!”她妈就过来,短短长长地吩咐了好几分钟,什么不许出去玩儿啦,看着鸡下蛋啦,翻晒那一堆烂草啦,得空捻几根麻绳啦……苏巧其实是不用她吩咐的,该做什么她都知道。她盯着妈妈的眼睛,懂事地应着:“嗯,知道了。嗯,嗯……”
然后,整整一个白天,她不离家门一步。扫地,喂猪,唤鸡,洗衣服,捻麻绳,掏灰,烧水,煮饭……饭煮好的时候,再也找不到事可以做了,她就倚门站着,等她的爸妈回家——忘了说一句,苏巧的这个爸,不是亲生的。她的亲爸,两年前生了水臌病,死掉了。她是跟着妈妈嫁到陵下来的,一个拖油瓶!
苏巧的这个爸呢,是个孤儿,吃百家饭长大的,三十多岁还没结婚,是个老光棍——这是大家的看法,叫苏巧爸自己看,是还没“老好”——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笑话。苏巧爸小时不是吃百家饭吗?自然也跑百家的腿,有回一户人家来了客,是个中年男人,差他下地去叫主人,他就去了,也挺会说的。人问:“来的男客还是女客?”他答:“是男客!”人问:“老头儿还是小伙儿?”他说:“还没老好!”——自然,他这三十多岁的年纪,更是没老好了。娶个寡妇,带个拖油瓶,又风闻那母女俩八字毒,满心的不乐意。
他的不乐意并没有表现在嘴上,而是在眼上。他从来不说苏巧什么,从来不,他只是看。比如说,苏巧扫地,他在院子里走过,回头往那地上看一眼,地上有什么看的呢?不过是一条一条的扫帚痕,苏巧扫得很干净。因了他这一看,苏巧扫得更干净了,草屑、煤渣、头发丝儿、浮土,都不放过,全扫走,人都说苏巧扫的地比新媳妇的脸还干净!
吃饭的时候,苏巧捧着碗,安安静静地吃,肩膀收得窄窄的,嘴抿得紧紧的,只夹自己眼前的菜,吃得一点儿声音也没有,用二十年后的话说,很淑女了。可是没过多久,她爸看了看她,苏巧就咽不下去了:她觉得自己吃得太多,一个小人儿,挣不来工分,吃那么多做什么呢?于是,她推了饭碗,说:“吃饱了。”
苏巧吃得少,做活多。她越来越瘦了,真是瘦!脸上就见一对大眼珠子,脸儿黄黄的,头发也黄黄的,人说:“这是个黄毛丫头啊。”苏巧不响,笑笑。人说:“这丫头太瘦了,叫你妈给你多吃点儿。”苏巧笑笑,也不响——她知道妈妈疼她,可是,哪里顾得上她呢。寄人篱下的日子,都不容易!
“巧,妈现在照顾不了你呢。先委屈些,等以后,咱们扎下了根,有了小弟弟,就好了。”
妈轻轻地拍着自己的肚子,把一根指头粗的红薯递给苏巧——用指甲细细地抠去了皮的。黄黄的小红薯很像妈妈的一截手指。苏巧说:“我不委屈。妈,我好着呢!”她把那指头样的东西咬下一截去,然后,一股泪漫上来。
“乖,我的巧!”
妈一把抱住苏巧,头在她肩上偎来偎去。苏巧知道,她的棉袄一定湿了。
第二年,妈生了,不是弟弟,是个妹妹——把老光棍晦气的!接生婆走后,他蹲在屋角连抽了好几袋烟,三天没抬眼皮。
生了妹妹后,苏巧的声气更小了,手脚更勤快了。一个小丫头,管着一家的茶饭,十几只鸡、一头小黑猪、两只老山羊。地也扫了,线也捻了,还刮了绿肥,拾了草,又拾了那一大堆粪!
左邻右舍的大婶大妈看在眼里,叹一声:“难为这孩子了!”
又说:“长大就好了。”
又说:“有了弟弟就好了。”
苏巧总是笑笑,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