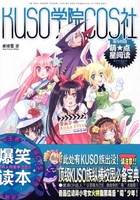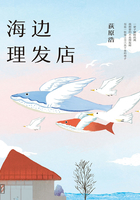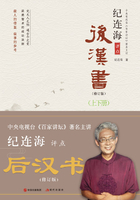面对死亡的困惑
作为天地之间惟一具有自我意识,并创造文明与文化的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关于自身生死问题的思考。正是由于这些无休无止的思考,酝酿出了人死后生命还会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灵魂不死的信仰。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全人类的祖先们几乎都具有朦胧的灵魂不死的观念,而要想知道这一观念产生的原因,只能从人类本性的需求与生存现实的矛盾中寻求答案。构成这个矛盾的主体就是对生的追求和对死亡的恐惧。
贪生怕死几乎是所有动物普遍具有的一种天性,从猪犬被屠宰时那凄厉的嚎叫与挣扎中,不难体会出其对死的畏惧和生的眷恋,即使是动物界较低等的小昆虫,也有逃避伤害、保全生命的本能。动物是否具备思考生死问题的能力不得而知,但情智、意识、思维等诸方面都明显高于动物,同时又具有哺乳动物之躯体的人类,其贪生怕死的动物性本能与发达的意识形态相联结,便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情感和愿望,这种复杂的情感首先表现在既具有超凡的理性和天才创造力,但又是血肉之躯的人,虽然具有认识万物、征服万物的智能,但却无法认识自身生死的玄奥密码,作为生命本身从诞生到死亡,几十年匆匆结束,留下了一串又一串遗憾。因此,从村夫野老到王公贵族,从多愁善感的文人墨客到深沉睿智的哲人智士,面对生从何来、死向何去这一难解的永恒命题,无不苦苦思索,唏嘘感叹。从屈原的《天问》,到“生命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以及“卧龙跃马终黄土”,“死去原知万事空”等诗句,无不表达了人类对生命终极关怀的探寻与反思后的无奈。就连孔老夫子这样积极入世的“至圣先师”,面对流逝不返的河水,也发出了“逝者如斯夫”的感叹。
当然,人类终归是具有理性、感情并能和自然相抗争的高等动物。因此,制造出一种肉体虽死但灵魂不灭的学说,便成为人类心灵和情感中不可缺少的慰藉和寄托,同时也是鼓励人类自身抵抗死亡的一种手段。
灵魂作为一种非物质的产物,是人类在幻想之中寓于人身又主宰人体的一种观念,这个观念的产生,大约起源于原始社会中期。正如恩格斯所言:“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便开始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可是正是这种“思维和感觉”,滋哺了“灵魂不死”的观念的产生和发展。这种观念通俗的解释是:人的肉体虽然离开了纷纭的世界,但是肉体内在的灵魂仍然活着,这个灵魂到另外一个世界中去了。这个不灭的永远活着的灵魂,还能回到人间降临祸福。因此,在这个观念的促使下,人们对死去的祖宗除了存有感情上的怀念之外,还期望他们能够在另一个世界过上美好的生活,并对本族本家的后世子孙有所保佑和庇护。于是,便逐渐形成了一套祭祀崇拜礼仪制度和埋葬制度。他们认为,人死了,只不过是一种迁居,即从一个社会进入另一个社会去生活,故而生者总是按照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来安葬。事死如事生,在冥冥阴间,死者也要居住,于是生者就模仿人间的房屋为死者建造了墓室;死者也要参加劳动,就随葬有工具;死者也要享受,就备足日用器皿、各种衣物及金银玉器等贵重物品;帝王贵族死后,往往要用活人殉葬,以使那些嫔妃爱妾、侍从卫士、奴婢杂役在阴间继续侍奉他们。“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当然,这套制度从萌芽、发展一直到顶峰,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这一点,不仅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从考古发掘的实例中也可得到物证。
据最新的考古资料显示,位于北京房山周口店母系氏族公社早期的山顶洞人埋葬处所,早在距今大约18000年前,就开始出现了具有原始宗教意识的灵魂观念,如果有人死去了,生者便将死者埋于自己居所的下洞,并在死者身上撒上赤铁矿的粉粒,同时随葬一些燧石、石器、石珠和穿孔的兽牙等物质。这些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装饰品的随葬,正是上洞生者实际生活的写照。除此之外,在陕西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村、华县元君庙、洛阳王湾等5000年前的母系氏族公社后期、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中,考古学家曾发现丁大量公共墓地,这些墓地的布局与生时的村落布局极其相似。死者的头颅大都是朝一个方向排列,充分反映了氏族制度血缘关系的牢固性,并幻想死去的灵魂到另一个世界后仍然能过氏族的生活。像这种氏族公墓制度一直延续了很久,早期的文献如《周礼.墓官》上还记载着专门设置的管理公墓的机构和人员,大约从距今5咖年前开始,原始公社逐渐瓦解,私人占有制开始萌芽,以家族为重要单位的丛葬制产生了,这一变化在陕西华阴横阵村龙山文化遗址以及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多处墓葬中均有明显的反映。
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对于墓葬越来越重视,灵魂不灭的观念也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越来越强烈。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人类的活动经常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迁徙。在这诸多情况的限制下,人们还没有把墓葬作为永远祭祀的打算,所以当死者被埋葬之后,地面上没有留下什么特殊的标志。正如《礼记.檀弓》所言:“古也,墓而不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凡墓而不坟,不封不树者,谓之墓。”说明早期的墓葬是既无封土的坟头,也无树木或标志的。这一点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大约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礼记》中有一段孔子寻找父母之墓的故事,为后人研究墓葬的变革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这个故事说,当孔子三岁的时候,父亲叔梁纥就死了。当孔子长大成人后,想祭祀一下他的父亲,却找不到墓葬的处所。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经过很长时间才找到。孔子是个重“礼”之人,他认为子孙祭祀祖宗是必要的礼节,为了便于以后经常前来祭祀而不致迷失方位,他想了一个办法,即在父亲的墓葬处所上培土垒坟,作为下次寻找的标志。关于在墓葬处所培土垒坟的做法,可能在孔子之前就有人做过尝试,但后人大多还是以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作为封土的起源。从文献记载看,春秋战国以后,坟头的封土逐渐高大起来,大者形状好似山丘,因此有人把这类的墓葬处所称之为邱。如当时赵武灵王、燕昭王的墓葬处所,分别称为赵邱、昭邱等等。后来,便出现了帝王将相等封建贵族的陵。
随着奴隶社会制度的形成和生产力的发展,一些产品被少数人所占有,逐渐形成贫富之间的大裂变。由于灵魂不灭的观念的膨胀,人们不惜倾毕生之财富用于殉葬,以追求在另一个世界上生活的舒适与安逸。由此便产生了厚葬之风,这种厚葬之风的形成,使人间几乎所有的精美器物都被埋人地下和死者相伴。而厚葬之风的愈演愈烈又产生了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盗墓。那山环水绕灵境天开的巍巍帝王之陵,那帝王之陵中闪烁不断的磷火蓝光,以及无以数计被盗的陵墓珍宝,再度唤起人们的万千记忆……
种种有关盗墓的故事,从此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