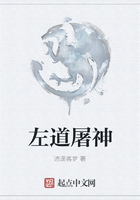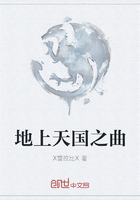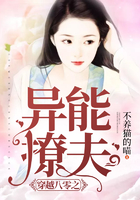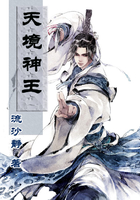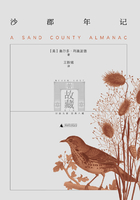现在看样子,听语气,似乎是想要改主意,短时间内能是什么造成了对方心思的改变?
之前张正初从哑口无言,到态度转变之间,只干了一件事,就是看了旁边武人一眼。
对方态度转变的缘由已经很明显了!
他赵文举,有点欺人太甚了!
有普通门客在场,说话咄咄逼人,这么不给人家留面子,自己说着“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却没给张正初留一个台阶,让这位张家的公子,脸面往哪搁?
人家的名望还要不要了?
在门客面前的威望还怎么立?
如果张正初现在不反驳,像个怂货一样,以后还怎么在门客面前说话,还怎么发号施令?
泥人还有三分火气呢,更何况人家张正初,张家的大公子!
所以张正初必须要做点什么,必须要反驳点什么,必须要表现得刚强一点。
然而有些事情,不是他想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
墙壁旁边的女人报不了仇,同样,他张正初现在也硬不起来!
赵文举把剑递回去的意思就是,你要反悔,我们就打一场,在你的门客面前。
我可能是不敢杀你,但是,我能揍你一顿,你是想嘴上硬气,挨一顿揍,还是嘴上服软,好好做你的世家公子呢?
这是赵文举给张正初出的选择题,他想看看,这位世家公子,会怎么接招?
这是一个很难的选择,因为无论向左还是向右,他张正初,都没有好处,都只有坏处!
赵文举在旁边看着,郭志杰同样看着自己公子,之前混了头脑的女人,也在旁边看着。
此时的张正初握着长剑,正用大拇指摩擦着粗糙的剑柄,没有直接回话,也没有看赵文举,而是看着剑脊。
他之前随身的佩剑被赵文举熔断,已经用不了了,这是备用的武器,同样是名剑,豪杰剑!
只不过这柄剑不是真品,而是仿品。虽然是仿品,但同样削铁如泥,能行气血,是把不错的灵兵。
至于仿品与真品的区别,也就是差点时间的痕迹罢了!
张正初看着剑脊,是因为上面有一行字,是与现行字有点差别的古文,但也能看明白,是一句话:
“无故加之而不怒”
把长剑翻过来,背面同样有一句:
“猝然临之而不惊”
张正初是世家公子,享受过良好的教育,自然知道这两句出自哪里。
是三朝以前的一篇文章,《留侯论》,大儒苏轼所作。
他看着剑脊上的自己,虽然剑名“豪杰”,可剑上的字,却中规中矩,没有一点张扬恣意的感觉。
张正初知道赵文举还在等他的答复,现在也不是细品名剑的时候,他抬起头,谁也没看,说道:
“赵大人,我张正初是个言而有信的人,这反悔的事情,是断然做不出来!”
“那就好,我相信张公子的人品。”
郭志杰松了口气,知道一场冲突避免了,他是个比较简单的人,不在意那些面子啊,威望啊,之类的东西,他也用不着那些,能避免冲突,能省些力气,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女人看着面前的三个男人,目光依次划过三人的面门,想要说什么,又不敢说的样子。
赵文举点了点头,没有耻笑张正初的决定,也没有继续这个话题,给张正初难堪不是他的目的,既然对方认怂了,他就不会再激怒对方。
看到女人的动作,赵文举脸上又挂上了微笑,说道:
“现在知道怕了?”
人在愤怒的时候,肾上腺素激增,会做出冷静时不能理解的事情,赵文举理解这种状况,所有被“无明”笼罩的生命,都会犯这种错误。
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幸运的是,赵文举在战场上,替她承担了代价,给了她冷静下来,从新选择的机会。
当然,救下她,压制张正初,赵文举也有自己的考虑在里面。
女人张了张嘴,似乎想回赵文举的问话,但又没有出声,就闭上了。
赵文举看到对方似乎不知道怎么讲话的样子,也就不难为对方,说道:
“回去吧,别在这站着了,这不是你该参与的事情,这里不是你该站着的地方。至于这场战争,你的亲人身不由己,我们同样避不开。你亲眼见到一场血仇诞生,你恨,很正常,你想报仇,也很正常。但有些事情,不是你恨,你想,就能实现的。回去吧!”
听见赵文举的话,女人没有说话,她低着头,手里攥着死去亲人的标枪,转身走了。
没有人知道女人心里的想法,没有人知道她此刻的心情。
人们只知道,当明天太阳照常升起,女人的日子,还将继续。
看着女人远走的背影,郭志杰冲着赵文举说道:
“大人,你刚才说的,您觉得,有用吗?”
“有用?你指什么有用?”
“就是,您觉得,她还会恨我们吗?”
“你说这个啊!”
赵文举说着,动身走出了小巷,又对张正初说道:
“张公子,咱们也走吧。”
“嗯。”
张正初应了一句,依然走到赵文举身边,仿佛之前的冲突,两人的口角都没有发生过。
中原有句老话,叫做“宰相肚里能撑船”,用来说身处高位的人有度量大,像海洋一样,能让船舶在里面航行。
现在张正初深刻地理解了这句话,他与赵文举立场不同,理念不同,关系又不和,对方说话又很不留情面,咄咄逼人。
但他却不得不和此人同行,笑脸相迎,尤其是此时此刻,家族派来给他的最高战力,王玉山受伤,不能参与此次攻城战。
说起王玉山,自家客卿被外人打伤,他眼睁睁地看着,不能发作,也是有够憋气的。
此时,他不仅不能怪罪赵文举,还要仰仗对方的鼻息。
巷战阶段,他们接触到的,都是小兵,虽然给他的部下造成了一些威胁,但不足以放到张正初的心上,他心里最担心的,是还没有出场的,指挥这场战争的指挥官,孔德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