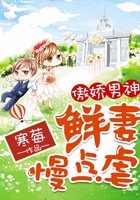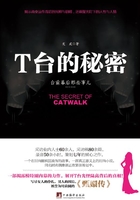这个题目,在写《普通人的病与痛》之前就定下了,我知道自己肯定要写,但那时,却还不知道该写些什么。这个名字为《身边的少年》的空白文章,就这样放在桌面上,哪怕是期间清理过无数个不再打算留存的文件,甚至换过一次电脑,它也仍然倔强而空虚地在那儿。它在提醒我,一看到它,我会想起总归要写的这篇文字,还要一并想起自己那本才写了三分之一就搁笔的《少年与落日》。
少年少年,步入30岁之后,再从口中迸发这样的词语,甚至会觉得词语本身也是那么迷人,充满着青春的无畏与活力。我和我的同龄人,已经不复少年时,亦不复少年的情怀,开始一点点把人生的铁轨,接驳到那条无数人运行的轨道上,一列接着一列,在相似的站台,接上年迈的父母,载上初生的孩子,结识许多或漠然或热烈,上上下下的朋友,就这样往未来开去。但人们总会在某一刻回头,就不免仍要碰见“少年”这两个字。长大成人之后回想,少年的阶段,对一个人的生成竟是如此重要。于是,我带着步入中年的疲沓之心,要写写曾经和正在的少年们,我所见所闻的少年们。
1.
我上班的地方,挨着一所全国最著名的中学,经常中午和同事一起去那儿的食堂吃午饭。每次走进校园里,就会看到一群少年在奔跑着、叫喊着。他们似乎活力无限,冬天只穿不多的衣服,夏天却套着厚厚的校服。同事老龚经常说:看看附中的这些孩子,觉得我们真是些老家伙了,看看他们,蹦蹦跳跳的多好。是啊,只不过跨进校门的一刹那,你就会感到,这儿和外面的世界有了区别。一个少年都意味着年轻,何况成百上千的他们汇聚在一处呢?少年们昂扬而干净的灵魂,甚至漫过学校的围墙,把这充满汽车和人群的枯燥之地,打扮得带有早春的气息。
有一次,中午,我吃过午饭往单位走,路过旁边的中学。我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手里拎着一沓小广告,走几步就贴在地上一张,走几步又贴一张,在他身后,牛皮癣一样的广告延伸到很远。这也实在是司空见惯的场景了,我们走在大街上,不是每一天都会见到好多吗?小广告贴在马路上、天桥上、护栏上、路灯杆上、墙壁上、自行车后座上……而贴它们的,通常都是十几岁的少年。从衣着和相貌上能看出他们来自乡下,不再读书了,到城里来讨一份生活。他们生存的工具就是胶水和印满了办证、刻章之类广告的小纸片,贴得到处都是。他们贴一张,就会赚到一张的钱,完全不会想到,自己的作为在别人眼里是一种破坏,是“非法和可恶”。
我也如所有司空见惯的人一样,看到他们,会自然地想到地上难看的“牛皮癣”,但也仅此而已。直到这一天。那个男孩贴着小广告往前走,突然从旁边冲出来一个十四五岁年纪的女孩,穿着校服,一看就是学校里的中学生。女孩蹲在地上,把他刚贴的小广告一张一张地揭下来扔进垃圾桶。男孩发现了,很吃惊:这大概是第一次除了环卫工人外,有人来揭他的小广告吧。他迟疑了一下,然后斗气似的把手里的小广告往地上、护栏上贴。女孩也生气了,跟在他后面往下揭。可是他贴得很快,她揭得总要慢一些,女孩更生气了,她放弃小广告,开始追那个男孩,嘴里喊着:不要贴了,你不要贴了,难看死了。男孩看着有点儿疯的女孩,这出乎了他的预料,似乎感觉到了某种不安,或者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作为可能并不那么理直气壮,飞快地跑开了。女孩看他跑了,也停住脚,喘着粗气,脸蛋泛红。她有点儿累了。喘了几口气,她又去把刚才男孩贴的小广告都揭掉扔了,走进校门,消失在学校里。
我回到办公室里坐下,脑海里总是闪现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少年在追另一个少年,前一个来自农村,没读书,在打工;后一个生于北京,或许很快就会考上大学,她追着他,揭掉他贴的小广告,而他最终落荒而逃。他们几乎一样的年纪,却成了这样的“对手”,是怎样的生活和命运把本来应该是同类的少年变得如此不同?站在一个生活在北京的成人的角度,我们会多么热爱与欣赏这个女孩子的作为,她把一颗干净纯洁的灵魂献给这个世界;可站在一个来自农村的人的角度,我又明白自己毫无谴责男孩的资格。我深切地知道,如果我当年没有幸运地考上大学,而是出来打工,我很可能就是满大街贴小广告的少年中的一个。这件事,不再是简单的对和错,而成了一个疑问、一个困惑。我们都知道,这些打工仔是无法把城市当作家的,尽管他们无比渴望它是,有多少渴望,就有多少现实告诉他们这是幻想。
我想起,读大学时,经常去金五星百货城,那里是穷学生的天堂,什么都有,还很便宜。于是,就经常在那里看到警察把一些十五六岁的孩子抓起来带走,他们是小偷。被带走的时候,他们并不感到难过或羞愧,只是用一种奇异的眼神看着围观的人们。到现在,我也无法猜透那眼神里都有怎样的意思。找工作那段时间,经常步行换乘各种公交,偶尔会碰到某个少年迎面走来,到你跟前,突然间敞开外套,露出里面一台数码相机或一排手机,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问:大哥,要相机吗?便宜。第一次我有些吃惊,后来便习惯了,摇摇头。他们就又合上衣衫,风一般地从你身边走过了。也许无须猜测,就可以知道这些相机和手机是从哪儿来的。这样的少年一波又一波,我最早遇到的那一些,现在也已经二十几岁了,他们在干什么呢?
在这遥远的异乡都市,永远有少年在流浪,也永远有另一部分坐在课堂里读书。有一些东西,在把他们的过去分开的同时,也把他们的现在和未来分开了。我总感到某种愤愤不平,为人们在少年时,得不到平等的生长的机遇。特别是对农村的孩子来说,很可能一件微小的事情,就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可能是一次学费交不上,可能是冲动地打架……很多细小的可能,渐渐把他们的路推向坎坷和歪斜的方向。没有人会为此负责,而他们只能接受。
因为工作的原因,有好几次,我去印刷厂盯封面的印刷。工作人员带着我参观印刷的流程,一走进他们的大车间,就闻到了刺鼻的味道,各种胶水、工艺材料、纸张等的味儿混合在一起,让人头晕眼花。我看见车间里有近百个比我年纪要小的年轻人,在做着许多机械的工作,粘贴、装订、切割等等,那些平日里在书店的架子上趾高气扬的书本,现在多呈现为残缺的肢体,无言且无趣。我惊讶地注意到,工人们没有一个戴口罩的,在这么浓重的味道里。我问带我们转的工作人员,她说已经习惯了,戴口罩会觉得闷,习惯了就好了。一个人,以及他的呼吸道和肺部,需要多么强大和牺牲,才能习惯这种刺鼻的味道?我不敢细问这种味道对身体是否有损害,因为看起来这是不可选择的。
机械地工作的少年们,见我们来参观,他们只是抬起头,看了一眼,又埋头于自己手里的活计,没有闲谈,没有微笑,他们做得那么娴熟。可这算是一种技艺吗?工作没有贵贱,工作又怎能没有好坏?在回城的地铁上,我有点昏昏欲睡,可头脑里始终是他们的身影和神情,他们是那样的安之若素,在短暂的遭遇中,我看不出不满和无奈,或许有,只是藏在深处。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许多人的影子,那些我曾经的玩伴,十五六岁就开始出去打工、去建筑工地,打石头、挖煤、粉碎矿石,以及各种我还没来得及想象的事情。
他们也是一样的少年,但却有着不一样的青春。我似乎能找到命运区别的原因,但又似乎只是抓住了一缕青烟,在握紧拳头的一瞬,青烟也随之飘散。
2.
老婆是中学老师,每天跟100个这样的少年在一起,因而总会听到她讲他们的故事。有一年的时间,我和老婆住在她们学校的宿舍里,宿舍就在校园中。她们学校有很多流浪猫,我惊奇于这些流浪猫都长得胖胖的,以为是在吃食堂的剩饭,后来才知道,它们的伙食好得很。稍加注意,总是会看见穿着校服的少年们,从商店里买来火腿肠,掰碎了给流浪猫吃。学校里有一个大池塘,池塘里有红色的小金鱼,他们就又买来鱼食喂鱼。这都是很小的事情,很多人都在这么做着,但你看见一群少年这样做时,还是会感到某种感动。
现在住的小区,离地铁不算远,中间隔着另一个小区。附近上班的人们,一般都要绕过这个小区才能到达地铁。这个小区当然有贯通的东西两道门,但管理很严,要刷专门的卡才能打开。上下班赶时间,或者图方便的人,经常会等在门口,见有人刷卡开门,赶紧趁机进出。这一点大概让小区的物业很烦恼,可是又有点无奈。
有一天下班,我拎了些重东西,贪图省力,也走到门口去。我看见一个老太太,带着一个3岁左右的小女孩站在铁门里。小女孩手里拿着门卡,她奶奶把她抱起来,才刷上卡,门开了,我打开门,站到一旁,想让祖孙俩先出来。可是这位奶奶连忙摆手让我先进,僵持了几秒钟,我赶紧进去,还是用手撑着门。小女孩着急地拉了我一下,我有些疑惑。她奶奶笑着说,她让你关上门。我关上。老奶奶说:我们不出去,我们就是来给人开门的。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小女孩就是专门来到门口,看到有进不来的人,她就努力去刷门卡,把门打开让人们进来的。我赶紧说,谢谢你。她说,不客气。后面又来了人,她果然举起了手里的门卡,奶奶把她抱起来,门再次打开。她开心极了。
这样的故事,似乎怎样解读都有歪曲它的嫌疑。但只要一想起她努力去够刷卡器的场景,心里自然就生出非常温馨的感觉。我们曾经也是如此,后来长大了,变得世故圆滑,即便不奢求像小女孩一样毫无私心地为人开门,在其他伸手可及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伸出援手吗?我不知道。因为有太多的事件在证明,许多人不但不会伸手助人的,反而是相反的。
如何面对孩子,似乎成了大人们共有的难题。坐地铁、坐公车,时常会面对让座的困境。老人、孕妇、残疾人,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站起来让座,但遇到孩子,我总会看一看。如果孩子很小,自然也会把座位让给他和家长,但如果孩子已经到了八九岁的样子,且跟着的是父母不是爷爷或奶奶,我一般不会让座。这个年纪的孩子,体力已经不错了,站一站也不会怎样。如果总有人因为他未成年就给他让座,就有可能形成一种“别人通常要让着我”的心理。而且,我们常常见到,你给一个老人让了座位,他很快就让给自己的孙子,他们又常常坐得理所当然,全然不顾祖辈在公交车上摇晃着。一件本来很好的事情,在这个传递中,变成了另外一件事。
2003年的6月到8月,因为一个机缘,我曾跟一个剧组到景德镇去拍戏,帮导演改一点剧本,顺便给他们写新闻稿。在景德镇的时候,有一个场景是在某家烧瓷器的厂子里。有一天上午,剧组去那儿取景,我也跟着参观了上百年的瓷窑和一些烧制瓷器的作坊,还看到七八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女孩,在对着瓷器坯子,一笔一画地画山水花鸟、画人物。我很好奇,便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他们有点儿羞涩地抬起头,看看周围的人,然后又埋下头去仔细地画瓶子罐子。我知道,人们在瓷器上看到的图案,很多都是他们一笔一笔画上去的。但更令我吃惊的是,他们除了吃饭和上厕所,一整天都坐在椅子上画,画得非常慢,因为有一笔出了纰漏,整个瓷器就坏掉了。
景德镇夏日的中午闷热异常,他们浑身都在淌汗。我后来打听到,他们都是景德镇瓷器学校的学生,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都要在作坊里画瓶子罐子,这是一种实践,也是为将来要成为大师的练习。
在此后,无论在哪儿看见瓷器,也不管它们的色泽、质地是怎样的,我都怀着一份感动,因为我不但见过了上千度的熊熊窑火昼夜的淬炼,看见土和着水变成泥,变成形状各异的坯子,更看见了一群少年赋予它们生动和灵气。这当然是幼稚和拙劣的画笔,更无法和流传下来的那些古代珍品相比较,可少年身上的汗水和神情里的认真,总让我觉得这些普普通通的瓷器,内里藏着他们的故事和命运。
3.
事实上,我最了解的少年,或者说曾经的少年,是老弟。在我不停地复读,一定要考取一所理想学校的时候,他只是读了一所中专,他走过的生活之路,就是一个乡村少年艰辛的成长历史。所以,我愿意用更多的篇幅,讲一讲他的故事。
我上初中时,老弟读小学,很贪玩,学校里又新换了毫无经验的女老师,班级成了放羊班,老弟的成绩就很差。对这一点,父亲并不像看到我成绩差时那么愤怒和着急,事实上,大概老弟才出生不久,父亲就打算好了一件事:两个儿子,一个将来出去闯荡,另一个留在家里给自己养老。因为这个想法,他在老弟的学习上并不是很在意。我在读小学期间,因为作业、课文或考试成绩,被父亲打过好几次,但他似乎从来没打过老弟。
乡下开始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老弟搭着这趟顺风车,升到了初中。我们读的中学,离家40多里路,条件极差。因为小学时底子薄,他初中的成绩也就不可能尽如人意,又远离父母管教,老弟爱玩的天性得以自由施展。他开始展露其他方面的天赋,比如省吃俭用地攒下5块钱,从同学手里买下一个破旧的小随身听,然后自己拆开,鼓捣好些天,竟然修好了,又用10块钱的价格,把它卖给另一个同学。他就这样在玩闹中把初中读完了。
老弟中考那一年,已经是我的第二年高考了。父母曾和老弟商量放弃中考,因为他平日的成绩,无论如何也考不到高中,想让他直接停学,回来和老叔学习开车,然后当一个货车司机。老弟说,还是考一考吧,因为报名费早几个月就交上去了,如果连考场都不进,太亏了。于是他就去考了一下,考完之后,随便填了几个中专学校的志愿,便打包行李回家,下地干活,已经做好了当一辈子农民的准备。但是一个月后,就在我收到一所很差的专科学校通知书一周后,邮递员给家里送来一个信封,老弟竟然被呼和浩特的一所中专学校录取了。那时候,还没有网络,也没有其他任何消息来源,全家人都判断不出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学校,担心只不过是一场骗局。而且,家里陷入一种紧张的气氛:父亲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张罗着借钱,他觉得这一年我无论如何也能考上大学了。我却并不想到这个学校去。父亲犹豫着,这笔辛辛苦苦筹措起来的高利钱,究竟是还回去,还是把它作为老弟的学费,送他上学。我们开了一个气氛凝重的家庭会议,结果是,同意老弟去读一读这个一无所知的学校了。
老家去呼市,先从林东坐火车到集宁,然后转车。父亲、老叔一起送老弟到林东坐车。那一年老弟16岁,从没出过比林东还远的门。他们把老弟送到离林东十几里地的小站,看着他孤身一人踏上绿皮火车,再看着古老的内燃机车缓慢地驶出站台,父亲突然脸色雪白。老叔问父亲:“二哥,你没事吧。”“没事。”父亲说,但有气无力。他俩回到镇子,到小饭馆里吃晚饭,要了一瓶白酒,才吃了几口菜,父亲就痛苦地伏在了桌子上,老叔吓了一跳,赶紧过去搀住他。过了好一阵,父亲才缓过来,喝了几口酒,脸上终于有了血色,他说自己在车站那儿就有点儿心脏不舒服。母亲后来跟我和老弟说:“你爸那次太吓人了,想起文泽一个人上学去,担心得犯病了。”事实上,父亲并没有心脏病,但他那次如同心脏病发一样经历了危险,可能是在那一刻,他才突然实实在在意识到,自己这个刚刚成年的、准备留在身边养老的小儿子,孤身去外面那个他一无所知的世界闯荡了。
那时候,村里没有电话,不可能及时获得远方的消息。老弟踏上西去的火车,四五天都没有信儿,全家人都在担心,亲戚们见到父母,也总是问:“文泽去上学咋样了?来信儿了没?”母亲总是故作镇定地说:“男孩子,没多大事,写信至少得半个月才能回来。”又过了一天,在矿上工作的四爷爷家的四姑回来,说老弟给他们打过电话了,已经到学校了,放心吧。爸妈这才放下心来。
这年冬天,我还在复读班的最后一排鏖战,门口的同学喊,说有人找我。我出去,看见老弟笑嘻嘻地站在楼梯拐角处,身上背着简陋的双肩包。我过去,两个人破天荒地拥抱了一下。问他啥时候回来的,他说刚下火车。他长高了,也更强壮些,板寸头发,最重要的是,我看见他嘴唇上有了黑黑的胡楂儿,只不过半年工夫,他已经有了青年的模样。老弟下午坐车回家,他把自己包里在火车上没有吃的面包、橘子和一瓶汽水都给了我,我一边咀嚼吞咽这些食物,一边想象他在拥挤嘈杂的火车上站17个小时的辛苦。
等我也放假,全家团聚时,老弟才细细讲起他上学的路途。他从集宁下车,到窗口买了去呼和浩特的票,就一直不敢离开车站。晚上9点多,他才从呼和浩特下车,可他们学校离市区几十里地,他找了一辆摩托三轮,半夜找到了学校。母亲一边听老弟讲述,一边感叹:“大半夜的,你也不找个地方住下,让人家把你害了怎么办?”老弟说:“找个旅馆住,少说也得二三十块钱呀。”他和我一样懂得,家里每一分钱得来的艰难。
三年后,老弟从那儿毕业,和几个同学被人介绍到刚刚起步不久的一家牛奶制品企业工作。在那儿,他几乎什么活都干过,打零工、收牛奶、做质检员。收牛奶时,因为不愿意收掺了水的奶,还被人追着打。毕业工作的三年,他没回过一次家,因为他自己在心里暗暗发誓,要做出点成绩来再回去。可一个打工仔,要做出一番事业,是何等的艰难。那时候,因为我和老弟都已离家千里,父亲下定决心装了部电话。有一个除夕夜,母亲给老弟打电话,他说他才刚刚加班回来,母亲听完就掉眼泪了。老弟后来告诉我,因为交房租后身无分文,他从同事那儿借了100块,买了一只烧鸡一瓶白酒,回到他们那个阴暗冰冷的出租屋里,吃完烧鸡,喝光白酒,倒头就睡。为了抵御饥饿,他过年的几天,基本上都是在冰冷的床上度过的。
2002年的5月份,我已经在北师大读书了,五一假期决定去呼和浩特看老弟。我住在内蒙古大学高中同学的宿舍里,刚到的那天喝了很多酒。第二天酒醒后,我坐上一辆公交,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到了企业的产业园。下了车,我四处打望了好久,才终于看见在一排小饭馆、小商店下的老弟,头发很乱,脸色也不好,胡子拉碴,嘴里叼着一根烟。这一次,我们没有拥抱,而是说:“我都没看见你。”其实我来之前就已经知道,老弟生活得并不会很好,但看到他的憔悴和颓废,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他带着我在企业的园区转了转,那里贴满了“员工以为企业奉献为荣”一类的洗脑标语。然后去他和一个同事合租的小屋子。小饭店那条街的后面,新建起明亮的大楼,绕过这座楼,再穿过一个布满垃圾和水坑的胡同,是一排破旧、低矮的平房,老弟的住处,就是其中一间。屋子里很暗,大概只有六七平方米,靠西面和北面的墙下,摆着两张床。不,不是摆着,也不是床,不过是地下摞了四摞砖头,砖头上铺了几块木板,木板上铺着一床褥子,褥子上是很薄的被子、枕头和暗绿色的军大衣。这就是老弟抵御黑夜时所能有的一切。靠门口的地方,有一个小炉子,是用铁皮桶自己做的。屋子里很冷,老弟想点着炉子暖和一下,但费了好久的劲儿,只是煤块在半死不活地冒烟,炉火并没能旺起来。老弟说,咱们去吃饭吧,饭馆里热乎,这破炉子总这样,爱冒烟。他的眼睛被烟熏得发红,是一种被迫的流泪状态。
我们到这家附近的小饭馆里,要了砂锅和米饭,闲聊着吃完。我记不清有没有谈到未来两个字,但我们肯定说起了将来的日子。我问他的打算,老弟说,先干着看吧。我又问他今年过年回不回去,他没出声,点起烟,吸进去,吐出来,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到时候看吧。”我发现他右手的小拇指指甲很长,问他留这个干吗。不干什么,好玩,他说。我当时有点难过,他依然封存着自己的内心世界,我知道,他不想让我为此担心,不想把自己现在穷困的生活和迷惘的未来给我看。他努力营造着一种“我很好,至少还行”的氛围,我不能去破坏这个,因为结果会更令人难过。那一刻,我感觉到了兄弟俩彼此的尊重和坚强。饭吃得索然无味,老弟把账结了。本来,我想去结这顿饭钱,但后来忍住了,我知道,抢着掏钱,只会伤害他的自尊心。
然后返程的车就来了,我坐上车,没敢回头看还在挥手的老弟,虽然我极想回头看看,但内心的酸楚让我不敢这么做,怕眼泪掉下来。虽然不曾看见,但之后的若干年,我的脑海里都有一幅画面:透过斑驳的车后窗,我看见老弟单薄而倔强的身影,一手掐着烟,一手向我挥舞;在他身后,是一整片尚未开发的土地,远方的山,在5月份的风中仍旧毫无绿意。他的脸是模糊的,我的也是,我们这一次见面,前后加起来不超过4个小时。
回到北京,我向父母报告了这次行程,只说老弟在那儿还行,挺好的,让他们放心。还能说别的什么呢?如果我说他过得很凄苦,而父母将会惶惶不可终日。年龄渐长,我才发现内心深处的愧疚,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的存在,剥夺了老弟过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比如,如果不是我复读了好几次,用尽了家里的所有收入,老弟本可以在初中复读一年,考高中、读大学的。但事实是,他接受了家庭所给予的命运,甚至想努力靠自己去改变家庭的命运。
第二年,父亲实在不放心,喊上二舅,两个人坐火车去看老弟。老弟想让农村来的父亲和二舅能在呼市好好玩一下,提前借了些钱,带他们下馆子,带他们去呼市的景点,三个人的门票花了100多。出来后,父亲和二舅都忍不住感慨:“啥破玩意儿啊,啥破玩意儿啊,白花了100多块钱。”老弟当然很清楚这些景点并没什么可看的,但他还是要带他们进去,不是为了看,只是作为儿子想让远道而来的父亲有一个值得的旅行。他是多么迫切地向他们展示:我过得很好,不用担心。
老弟那时的收入,一个月1000块左右,除去房租、伙食费,剩下的大部分钱他都花在了网吧,下班之后就玩游戏。因为除了游戏,再没有其他东西能在那种环境下给他宽慰和快乐,即使这宽慰和快乐在本质上虚妄又短暂。他还学会了吸烟,再也没戒掉。我曾问他,为什么要吸烟。他说:“没劲,觉得活着挺没劲的时候,就想抽烟。”他开始思考“活着”这件事。我理解到,烟和酒,是我们生活的道具,也是我们灵魂的驿站,当我们觉得灵魂在躯壳里待得太过难受时,就总想把它拎出来,放在另一个容器里舒服一下。那容器可能是烟、可能是酒,也可能是其他的任何东西。于是,我不再固执地劝他戒烟,因为明白了人的情绪总要有一个释放的渠道。
干了几年,老弟的收入稍微好了点儿,不用再因为没开工资而三天不吃饭了,可他也渐渐明白,在那儿待下去毫无发展。我在网上和他说:“今年回家过年吧,你不知道一家人多想过个团圆年。”老弟后来跟我说,他本来还在坚持自己的誓言,要做出点成绩来才回家,可我的那次话,让他改变了主意。他请假回了家,和家人一起过年。我能想象他心里的挣扎,三四年的坚持,最后像个失败者一样回来,这令他羞愧和难受。年后,他又到呼市去,想把握住一次极好的转岗机会,可惜他不懂向管事的人“表示”,不愿意求人家,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他很失望,也很愤怒,打包了行李,彻底回家来了。
那一年,三爷爷家的三叔也回家过年,父亲去求他帮忙,给老弟介绍个工作。三叔磨不开亲戚的情面,给老弟介绍了一个活,是到吉林的一座矿上工作,老弟又是只身一人去了。干了半个月,他打电话说想回去了,矿区在山上,非常冷,他住在简陋的招待所里,手脚都长了冻疮。父亲总在电话里说,先干两天吧,先干两天吧,开春就好了。老弟不愿再让他们担心和操心,就在那儿干了下来。他告诉我,自己什么活都干,哪个领导安排下来的任务都做。从去那儿到现在的七年时间里,他没有过周末,即便是五一、十一这样的假期,也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
老弟去矿上后,常和我在网上联系,我那时常在北师大文艺学的论坛上混,还做了个版主,发点自己写的文字。忽然有一天,老弟给我发了个邮件,让我去看看,我打开,是他写的小说和诗歌。即使以我当时的阅历和水平,也能看出他文字和思考的稚嫩,但我读着那些东西,还是欣喜不已。我欣喜于他在山沟里,在举目只有石头和树的矿井周围,能培养起这样的爱好,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从自己的体验里深深地知道,他喜欢这个,就不会彻底陷入枯燥的生活和无聊工作的悲苦之中,就会将坚硬的现实的壳,凿开一个小小的孔,透过它呼吸着另一种空气。我鼓励他也发到网上去,他听从了,发上去,从很多网友那儿获得小小的认可。他写的东西越来越成熟时,我想,他的内心也一定越来越强大,再有了迷惑和困难,知道去哪儿寻找答案和力量。
前一段母亲来京,在家里没事上网,无意中翻到了老弟几年前写的QQ日志。母亲上的是我的QQ,我在单位也登录了。单位的QQ突然跳出来,有几句话:儿子,妈妈不知道你原来受了这么多苦,妈妈对不起你。我知道,这是母亲发的。老弟在QQ上回她:晕啊,这都哪辈子的事儿了。我看着他们聊天,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多年的辛劳与坚持,让他终于有了稳定的生活,并且结了婚,现在已经是一双儿女的父亲了。看到他的生活日渐安定,我感到欣慰,更重要的是,虽然经历了无数的摔打,他还是最初那个踏上列车的少年,在复杂的生活中,努力保持着单纯、善良,还多了稳重和成熟。我很清楚,这在如今的世上,是多么的不容易。
4.
好吧,就写到这里,已经很长了。
在大街上,在任何一处,看见少年们风一样地走过,都会多看上一眼,然后提醒自己,不忘当初少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