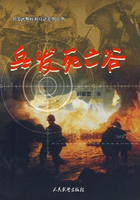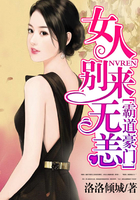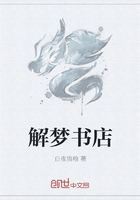回头看《别人的生活》《我们选择的路》《普通人的病与痛》和其他几篇文章,忽然发现,隔开几段文字,大概就会提出些不确定的问题来。有的尝试着给了自己答案,有的也只是作为引子导出更多问题。我于是知道,我写这些文章,更多是源自疑问,而不是发现了结论。但我珍视生活里的疑问甚过答案,答案只能标志着一段经历的终结,而疑问,却总是帮我们开启新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的确只是过程,因为结果来临的时候,一切也就都成为句号,所有的体验——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都必须也只能在过程中感受,最后凝结于心头的无非是对感受的命名罢了。但同时,我们又必须把这个漫长的过程分成大大小小的许多阶段,并为每个阶段设定预想的结果,还为实现这些结果而创造和经历过程。这样一层一层细分下去,活着,就成了一种日常生活的微积分。这一篇,也是这个微积分中的小小数字吧,我于是直接在题目中提出了问题:灵魂是什么东西?
讨论“灵魂”,是一件看起来很“装”的事,好在我写这些,主要是为了解决自己内心的问题,也就不惮于装一下。我也愿意,这些问题给看它的人一点微小的启示,哪怕仅仅是停留几秒钟,从烦琐的工作和生活里走一下神,想想平时我们很少注意的事,也有了存在的必要。
1.
有关灵魂,最有名的故事应该是浮士德博士和魔鬼签订契约,出卖灵魂的那一个吧。但这个故事的背景和文本太过复杂,我无力探讨,只能把它当作一个引发思考的因子。何况,我要写下的这些文字,不是想讨论一个宗教问题,也不是想讨论一个“灵魂有无”的科学问题,我想谈论的,仍然是一个俗得不能再俗的生活问题。或者说,是想问一下,在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里,我们整天挂在嘴边、我们偶尔独自追问、我们或许深入思考、我们可能从未关心的那个所谓的“灵魂”,究竟是什么呢?
我忘记了是高中的历史课还是政治课,有一个老师提到了王阳明,说他的“心外无物”,是纯粹的唯心主义,应该予以批判。老师举的例子就是《传习录》中的一段话: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山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那时候,我们认定物质决定意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自然会觉得王阳明在胡说八道,你看不看山中的花树,它都存在,并不以你王阳明的意志为转移。尽管如此,还是本能地觉得这段话在吸引我,总觉得其中有一种动人的奇妙的东西在。
读硕士时,看了一些书,才明白过来王阳明的冤枉。到现在,我也并未好好地去研读王阳明的著作,但即使从日常的经验角度,也能多少理解他“心外无物”的伟大之处了。我会自己把它解释为:对人的精神世界而言,存在并非是一个东西在事实上的有无,而是在观念上的有无。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并不“存在”的东西,对人来说和存在是同样的。很多时候,一种假设的危险,也就是一种事实的危险,比如出现了禽流感,不论事实上是否每只鸡都有病毒,我们只能假设它们有病毒。同理,许多事实存在的东西,对一些人来说是完全不存在的。比如,美国和非洲,对我老家的人来说是存在的吗?我想是否定的,他们的世界只能通过所见所闻所感来建构,美国和非洲一天不和他们发生具体的联系,也就一天不存在。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后来想,也许是因为人自身也只能围绕着那个精神中的“自我”来生活,世界也只能围绕这一点来建构。对人来说,它并非是实实在在的物质,而是物质在头脑里形成的一个空间。这当然不是问题的终点,而只是一处驿站,我的思考继续往前的时候,我找到了“灵魂”这个词语。困难在于,灵魂,或者和它类似的词语,早已被我们过多地用到了空洞的地步。可除了它,我找不到另一个词来命名那个包裹在最中心的我、你、他。我应该像写某些学术论文一样,给“灵魂”下一个定义,但这又是一个悖论,因为无论我给出的是怎样的定义,在他人眼里都可能是词不达意的。所以,我虽然提出“灵魂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但又不能给出答案是什么,而只能写一些我以为和灵魂有关的事情。或者说,我要写的,不是来证明灵魂是否存在,或者它到底有多少重量,我只是在一定的层面上相信它存在,然后讲一讲这个特别的存在,究竟会是怎样的。
这些年,电视台出了许多选秀节目,有跳舞的、有唱歌的。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某个选手情绪激动地在舞台上说:我用灵魂在唱歌、我用灵魂在跳舞、我用灵魂在画画。是这样吗?灵魂能唱歌、跳舞、画画吗?如果能的话,你怎么能确定自己是在用灵魂,而不是身体,不是情绪,不是无意识的冲动,不是其他支撑你的名誉、地位、金钱和自我实现的欲望?这些轻易号称用灵魂在做什么的人,也是一种回答,可绝大部分都只是一厢情愿的话,因为他们都没有好好想过灵魂是什么东西,也可能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去自己的身体里挖一挖灵魂。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相信“用灵魂在做什么”要比“用身体在做什么”更高级、更有价值、更应该得到认可。事实的确如此,但前提是你真的用“灵魂”在做这件事,而不是只用嘴巴上的“灵魂”。
2.
那句听到耳朵长茧子的话——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现在几乎没有人再认真对待了,但事实上,这句话道出了一个真理,只不过不足够完整,除了教师,所有的他人都可能是别人灵魂的工程师。一个人长成什么样子,确实和周围的一切都息息相关,他所经历的一切,都会如风雨塑造地形一样塑造他。
父亲是小学老师,妻子是中学老师,在他们上课、备课、批作业、完成既定的工作程序之外,有着另外一些不能量化,也几乎是看不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被忽略的,可在本质上却是更重要的。我对他们的工作暗自带着某种艳羡,我偶尔会和妻子说:“你们是真的在影响和塑造灵魂,我就算写一辈子书,可能也不如你们带给人的影响大。”的确是这样,她和她的学生许多次让我感受到了这一点。有一个孩子,父母都是高知,但不懂得教育孩子,也不在乎他的内心需求,使得他在冷酷的家庭长大,心理上出了点儿问题。这个孩子,一开始总是要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或者对其他同学发怒,许多老师都担心这是个潜在的“麻烦”。妻子和班上的孩子,经过初期有些艰难的磨合,容纳了一切,给了他在家里得不到的关注,营造了一个十分舒适的班级氛围,他也就渐渐平静下来。初二时,他已经完全正常了,且显出了很多方面的天分,数理化常考满分,性格也变得开朗且自信。我当然无法去测量,在这个孩子改变的过程中,妻子或者班上的孩子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他们无疑对他有着好的影响。这或许只是一念之别的事情,一个孩子,就此走上了他可预见的正常人生,而不是另一种。
有一次,因为家里老人生病,妻子破天荒地请假,在我们回去的路上,她收到班长的短信,短信说,老师,你不用担心班里,我们仿佛一下子都长大了,我和另一个班长一定会管理好班级的。妻子感动极了,不停地说,我的孩子太好了。他们当然还只是孩子,可哪里仅仅是孩子呢?他们对别人有着本能的同情和爱,我想,这情感正是来源于他们的“灵魂”,而不是具体的知识。尽管我时时怀着恐惧:这么好的一群孩子,将来进入到这个复杂的社会里,会不会变得和现在的成人一样世故、圆滑,天真会不会变成残忍,天性会不会被规训,甚至会不会成为社会中“恶”的一部分?
但我仍然感到内心的喜悦,为着妻子以正确的方式对待了他们,他们以正确的方式度过了这几年。她不过是一个渺小的老师,认真批改每一份作文,写下评语;和每一个情绪低落的孩子谈心,对他们的困惑和焦虑感同身受;凌晨4点起来备课,常常下班回到家一动都不想动。倘若有一个最准确的天平来衡量,应该可以称出,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她微薄的薪水,未必配得上她的辛苦和付出。世上没有这样的天平,有的只是自己心里的一杆小秤。可是不管怎样,她的的确确在影响着这些孩子那不断形成的“自我”,那日渐丰富的“灵魂”。
我们曾谈到,作为一个老师,在现在的中国教育环境下,究竟应该教给孩子们什么。考试要面对,家长们对分数的期待要面对,可在不得不做这些的同时,是否还能多一点点其他东西,哪怕仅仅是一粒种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无论这片土地将来生长出什么,让我们尽可能地先把智和善的种子埋下。
2010年,妻子的单位搞演讲比赛,她作为新人,被推荐去参赛。比赛的前一段时间,妻子有些焦虑,因为她从来没参加过这种活动,不知道该怎么去准备,但又不想随随便便应付一下。她回到家里,问我该怎么演讲——我曾经在上海的某个比赛中,误打误撞地演讲并得了最高分。我给她的建议是,永远不要去喊那些情绪激动的排比句和口号,倒不如讲几个实实在在的故事,她的班级上是有很多好故事的。妻子于是就准备故事,那次演讲,她得了冠军,比赛后很多老师都对她说:你讲得太好了,我听后特别有感触。
回来后,我问她都讲了什么故事,她很兴奋地向我复述演讲中的几个故事,有一个我印象最深,也是我从来没听过的。妻子说的是在杂志上看到的大江健三郎的故事,他在作品自述中提到,小时候很怕死,因病住院时更加恐惧,整天哭闹,不愿意自己待着,他担心自己会死掉。因为死了之后,“他”就没有了。大江的母亲安慰他说:别怕,如果你真的死了,妈妈会把你再生出来一次。于是他安心了。但是不久之后,他又忧心忡忡地问母亲:可是,即使你把我再生出来一次,那个我会把现在的我全都忘掉,我还是没有了啊?大江母亲说,我会把你所讲的话,所做的事,一件一件记下来,叫那个你都记住,这样你就不会消失了。这两次谈话,让大江健三郎获得了永久的内心平静,他终于笃定地相信——我——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是不会彻底消失掉的。
这个故事让我震惊,因为我第一次开始认真地思考,如果身体里有一个“我”,那这个“我”该是什么样子呢?是我对照清晨的镜子看见的形象?是我独自一人时感受到的孤寂?是我在人群里觉得格格不入时的疏离感?是我父母的儿子、妻子的丈夫?是我写作时半癫狂状态的疯子?是我将来临死时回光返照所能想起的自己?我不知道是哪个,也许是这所有的集合体。可是,它究竟是什么呢?最后,我决定——不是认识到,也不是想到,而是决定——它就是人的灵魂。也就是从“我作为我”的第一次意识萌醒开始,通过所有的成长过程,慢慢累积、慢慢磨砺,所形成的那个“内核”,是在几十亿人的地球上让我成为唯一那个“我”的东西。想通了这一点,并笃信了这一点之后,我再也不会对自己的存在有焦灼感了,至少在面对“自我”的问题上,建立了一个稳固的精神根基。
当然,我们并非总是在如此经典而戏剧化的故事里,才能窥到人的灵魂。许许多多日常的细节,一样是灵魂的显影。关键在于,当它出现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眼睛去看,给它怎么样命名,又以何等的心态去对待。
有一年春节,是在妻子的老家过的,因为我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过完年后,不放心父母,我俩还是又回到内蒙古,去陪他们待了几天。坐火车回到北京后,妻子说:妈给我发短信了。我看妻子的手机,果然是母亲发过来的,她只在短信里写:这几天谢谢你们陪我,妈真的开心。而就在前几天,妻子给岳母打电话,她也一样在电话里说:“谢谢你们回来。”我心里一酸,这酸楚固然是因为我们作为儿女不能常在父母膝前尽孝,因为为生活奔波的聚少离多,但与从前老人们给我的感动又多了许多东西。
它是什么呢?
我后来想到,它是一种我以前忽略的东西。母亲、父亲、妻子、兄弟,和所有的亲人朋友,我们从来都只是把他们定位在自己的体系里: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我的兄弟、我的朋友,这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只是人的天然弱点。但这条短信让我忽然觉得,他们不是“我的”,他们在我之外是自己。或者说,母亲和岳母说谢谢我们的陪伴,才让我清楚地感受到她们的身体里,也藏着一个特别的灵魂,而不仅仅是“我的母亲”“我们的母亲”。
3.
2011年,我在一家驾校报考了驾照,同时报考的同事,大概半年后就拿到了驾照,但我因为很多事情,有时候一个月也上不了一次课,拖来拖去,就到了冬天。驾校里有接送学员的班车,但我不太愿意坐,所以一般就是周六或周日的清晨,搭早班的地铁到西二旗,然后在那儿倒一辆公交车到驾校。
这来回的路显得有些漫长,借着这段不需担心终点的短暂旅途,我开始重读《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本科的时候粗粗地读过一遍,除了记住了开头的那两句最著名的话,什么实在的感觉也没留下。那时的我,刚从乡下到北京,盐碱地般的内心,很难栽种下我不熟悉的植物,而“自我”空间的狭窄,也难以容纳那些伟大的文字。可是这一次,或许是路上的颠簸应和了生活的坎坷,或许是灵魂终于敞开了它的呼吸,每一页纸都读得感慨万千。我清醒地记得,那一天天气阴沉,有些冷,我练完车,坐着大巴从驾校回家。我读到安娜纵身跃向铁轨,读到她在无可挽回的一瞬间仍试图继续活下去,顿时感到如重锤击胸,差一点儿在车上哭起来。那么一瞬间,托尔斯泰所写到的这个文学形象真正地活了,我看到也体验到了安娜的灵魂,不是精神,也不是心灵,是更缥缈和深入的灵魂,那个似乎不存在的空气一样游走在肉体中,作为一个人的根本的东西。我感觉到,她的一生,她的所有喜怒哀乐,都进入到我的心里。回家的路刚走了一半,我合上书,脑海里不停地盘旋着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哭,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
在哭我。
此刻有谁在夜里的某处笑,
无缘无故地在夜里笑,
在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走,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
望着我。
它像一个咒语,像一个来自天际和地心的话,不停地重复着,用各种各样的语气和节奏。我感觉到了,在它的重复中,是一个又一个安娜的、我自己的和其他人的灵魂在娓娓诉说。我犹如置身一间昏暗的屋子,窗帘的缝隙透出微细的一点光,身下那张椅子是安静的,眼前的墙是安静的,只有这首诗被诵读的声音在动,而这声音不是我自己,不是我所听过的任何一个人的声音,它仿佛就是里尔克在用中文诵读,仿佛是千百万人共有的声音在读。第一次,我感觉到一首诗触及了灵魂,里尔克通过托尔斯泰的安娜抵达了我,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神奇的旅程了。只有诗歌有这样的伟力,通过简简单单的一百个字,道尽无数人欲说还休或无力诉说的内心生活。
诗有这样的伟力,或者文学有这样的伟力,是因为那些写诗的人、写故事的人,看到了,也袒露了自己的灵魂,它的悲伤与煎熬,它的沉痛与磨难。除此之外,再不能有其他抵达千百万人内心的路途。1849年的12月22日,被判死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绞刑架下获得大赦,经历了濒死逃生。他后来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我请求与你相见。但我被告知,这不允许,只能给你写这封信,望你尽快给我回音。我担心,你大概会知道我们的判决(死刑)。在押解到谢苗诺夫校场去的路上,我只见囚车窗外人山人海,可能消息也传到了你那里,你必然为我感到痛苦。”
在被带到刑场的路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囚车的窗口看到一大群人,他想到这群人一旦将行刑的消息传到哥哥那儿,他该是多么痛苦。终于获得重生之后,他反而彻底理解了生活的本质。“现在你对我可以放心一些了。哥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我不忧伤,也不泄气。生活终究是生活,生活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而不在于外界。以后我身边会有许多人,在他们中间做一个人并永远如此;不管有多么不幸,永不灰心和泄气,这就是生活的意义和它的任务。”
看看吧,死亡在这个人的灵魂里表现为什么,不是恐惧和诅咒,而是爱。每当想一想,这颗伟大的心灵,在自己即将被绞死的路上,看到了车窗外的人群,想到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刑消息可能带给亲人的痛苦,我的心就会颤抖一下。我感觉到,通过这个场景,通过被转译的文字,通过同时作为人的处境,我那懵懂般的灵魂被他的灵魂触摸和抚慰了。不仅仅如此,他在另一段里写:“如果有谁还记得我的坏处,如果我和谁争吵过,如果我对谁产生过不好的印象,那么,要是你能见到他们,就请他们把这一切都忘记吧。我心里没有怨恨和愤怒,此刻我多么渴望能热爱和拥抱任何一位熟人。这是一种欢欣的心情,我今天在死亡边缘与亲人告别的时候体验到了。这时候我想到死刑的消息会使你悲痛万分。现在你可以放心,我还活着,而且以后能拥抱你的想法将支持我活下去。我现在想的就是这件事……”从死亡线上捡回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自己带给亲人的痛苦而痛苦,为了拥抱哥哥和所有熟人而活下去,我想象不出比这更多的悲悯,也想象不出比这更动人的灵魂。
是这封信,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非凡之处,对他的作品的理解,也因此而打开了另一扇洞悉秘密的门。也许,同样是因为这一点,他才能写出那么震撼人心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一如托尔斯泰写出了《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评论家们会证据确凿地指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独一无二,但是不是更应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根本就不是心理,而是灵魂。我在读《罪与罚》的时候,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所有恐惧、焦虑、忧愁,全都能感同身受,他灵魂的煎熬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灵魂的煎熬,然后又传到了我这样的读者这里,它默默地改变了我对自我和人生的许多看法。
如果说,我渐渐找到并看清了自己的灵魂,那也是因为这些灵魂在漫漫人生路上作了指引,仅凭这一点,文学和艺术,怎么会消亡呢?更何况,就算文学到此不再发展,也没有人再写出伟大的作品,仅我们现在拥有的,也足够人类在一片荒芜中重建精神世界了。
4.
拉拉杂杂许多,我自己亦深知这悖论:灵魂既无法准确描述,又难以捉摸,而只能去用带着“自我”的灵魂感受。我想,人与人之间所能达成的终极交流,也不外乎互相承认并尊重彼此的灵魂,哪怕它在绝大多数的场合和时间里,都表现为日常的琐碎和普通的情感。几年前,我的朋友哑巴和我提到一个细节,它来自葡萄牙大作家萨拉马戈的小说《修道院纪事》。那时候,我还没有读过这本书,朋友在向我介绍时,我有一个印象最深的细节。这个细节的大意是,一个人称七个月亮的姑娘,她的母亲要被作为异教徒、巫婆判刑,广场上围满了人,七个月亮也站在人群中。她只能假装不认识自己的母亲,可母亲看得见她。母亲看了看七个月亮后,七个月亮转过头问唯一一个站在她身边的年轻男子:你叫什么名字?这个男人说,我叫巴尔塔萨尔·马特乌斯,人们也叫我七个太阳。他回答时神情自然,仿佛觉得这个女人有权利问这个问题。后来,他们相爱了,七个太阳问七个月亮:你那时候为什么要问我的名字呢?七个月亮说:因为我母亲想知道你的名字,也想让我知道。那,你母亲为什么想知道我的名字呢?因为我母亲想知道,到底是谁站得和我这么近。
“到底是谁站得和我这么近”,我听到这句话时,心里有一种暖暖的灼热感,我在想,它是多么准确而诗意地写出了人和人之间的情感,那种无声的、本能的、温暖的情感。所有人是否都会在某个时候问一问:到底是谁站得和我这么近?就是这句话,让我开始寻找这本书,后来,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到了这本书,还是一本七成新的旧书。我开始阅读它,并对这段话怀着激动的期待。后来,我发现书中所写的情节和记忆中的有些出入,但我并没有去纠正和修改自己的记忆。这些出入,并不妨碍我所记得的版本,作为一个两个人灵魂上进行交流的故事来滋养内心。
那么,灵魂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大概是我以上所描述的一切,又或者是我以下所写的一切,甚至都不是,而是另外一种东西。无论如何,我珍惜这个词语及其所引发的所有思考和情感。我试着用它来回看经历过的三十几年的岁月,我便在更深的层面上感激自己少年时的贫穷,也憎恨自己少年时的贫穷,因为就是这感激和憎恨,帮我找到模糊的自己,它把根同时深埋于现实和精神的土地里,让我这一生都不会丢失基本的方向。
我坚持认为,灵魂不是心灵,不是精神,不是那个所谓有“21克重”的东西,灵魂甚至不会随着你的生长而生长,它只是它,是我们在清醒的意识状态下那个自我的核。如果说人的身体犹如一个微观的宇宙,那灵魂就是身体最最原始的点,我们内心的一切情感都来自它的大爆炸。灵魂的风暴,就是这个核的聚变和裂变,这看不见的能量,引发你一生的遭际,也影响着别人的遭际。可是它又不能被物化,也不能用时间刻度来标示,灵魂就是那清醒或混沌的自我,是认清卑微的本质,但却保有小小的尊严的那个自我。它是基于现在的、此刻的“自我”而具有的,比“自我”更深沉、更缥缈的自我的“自我”。灵魂就是那个我们的身体、意识都纹丝不动,可是它却暗自颤抖的东西,是在最最深且静的黑夜里你内心中突然闪亮的东西,是你在遭遇某件超出绝对意外的事情时自然地从躯壳里跳出来的东西。看到孩子被害的新闻,心里一痛,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所爱之人因爱而快乐,你会自然而然地从最深处生出欣慰感,等等。这些不是理性,甚至也不是感性,这些“不由自主”和“自然而生”可能就是灵魂。
如果这个追问可带来确信——生活中确实有那样一道光,比如灵魂,可照亮立锥之地,可温暖内心,但我们的命运却在于,每到夜晚,所有的光都将隐匿,汇聚一处,第二天醒来之后,你必须重新寻找它。这种不断重复的寻找和确信,如同西西弗斯滚动的那块石头,沉重、粗粝,可又是不可逃避的劳作。它隐藏在白昼的所有光之中,稍纵即逝,稍纵即被吞没,但并非不可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