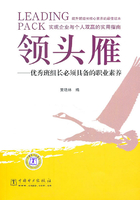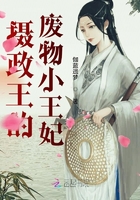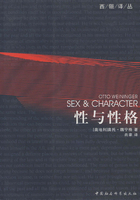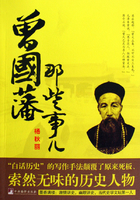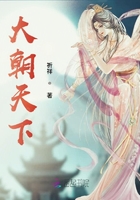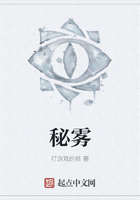25分钟
从家到单位,25分钟。从单位到家,差不多也是25分钟。其中,大约有10分钟用于步行和等车;剩下的15分钟在公交车上度过。所以,虽然每天我也像某些人一样,煞有介事地“在路上”,走过的道路却大都只是咫尺之遥。
我喜欢远行。但是在远行成为传说的情况下,近行变得如此明智而必要。
从家到单位之间的这条路,我走了整整八年了。有时候我怀疑,我与一只在磨道上奔波终生的驴到底有多少不同多少相像——摘掉眼睛上那块聊以自慰的遮眼布,我可能早就被这日复一日的单调烦死了。但是为了终点处那一小匝刚刚覆盖住槽底的青草,我必须安分守己,做一只着眼于当下的好毛驴。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与一件事情磨合得越久,越有可能发现它隐藏在平庸微笑之下的狡黠牙齿。——据说,有一门学问就叫做“公交车原理”:等待的时间越长,越不忍轻易放弃。这个原理也可以用来说明我和我现在这个单位之间的关系。以及我和婚姻的关系。我和爱情的关系。
还有,我和这个叫“沙爽”的女人之间的关系。
圆眼睛
通常,我喜欢选择车厢里中部偏后的地方。我面前是许多人的后脑,和窗外长年不变又日日更新的风景。这样的选择让我感到安全和安静。由于个头偏小,整个学生时代我都不得不坐在教室前排,任由别人欣赏我并不完美的后脑勺。一旦度过因为过分受宠而爱出风头的幼童时代,我开始变得畏缩、寡言、羞怯,在需要表演的种种场合,这些构成了我的致命弱点。幸好,单位并不要求我在会议上踊跃发言。我热爱这个旁观者的身份,像一个自知是异类的火星来客隐身在众人中间。——世界因此变得轻盈而愉快。
这天早晨,车到中亚商场的时候,上来了一个女孩。我远远地看了她一眼,又看了她一眼。我在想这个女孩到底有什么古怪——她甚至不像我这样伪装得十分完好的火星移民。在她找到座位坐下之后,我仍在脑海里对有关她的谜底苦苦追寻。突然我明白了:她的眼睛太大,瞳孔又太圆,这双卡通片里的大眼睛完全不适合出现在现实生活中间。尽管她的举手投足表明她是一个平和内敛的好女孩,这双大眼睛却对温良恭俭的传统风格进行了破坏。某些事物的美在于它可以半遮半掩,如同一堵古典的墙需要为它投下阴影的半角屋檐。当一双眼睛声明了独立立场,它摆脱了上眼睑和下眼睑,也无视乎睫毛的苦苦纠缠,这类似于孩童的任性表现,往好里说,它勇敢、专注、一往无前;往坏里说,它莽撞、呆滞,暗示出主人不够聪明。像一句脱口而出的肺腑之言,往往令当事者悔恨终生。我疑心上帝更希望人类习惯于欣赏有所阻碍的美,所以促使世间的万物相克相生。
为什么我对一双属于别人的眼睛这样介意?为什么我至今不能忘记多年以前的一场噩梦?
在踏进车门的瞬间,我已经隐约地知道,这一场旅程非比寻常。车上的乘客很多,我被堵在靠近车门的地方动弹不得。我只好扭头看向窗外,公交车已经驶过辽河广场,到达人大招待所门前。这是一幢呆板结实的老式建筑,楼口挂着无数个机构的牌子,这些牌子按照自身的自得或自觉定做得大大小小,像一堆胡乱拼在一起的丑陋补丁,其目的就是让来访者眼花缭乱一无所获。我扭回头,发现身旁的女人正在盯住我看,用她那双卡通片人物一样横竖比例失调的圆眼睛。我想对她笑一笑,表情肌却意外僵住。我突然感到一阵心虚——她看向我的眼神分明是在看一个怪物。啊,也不仅仅是她,她身后的所有乘客都齐刷刷对我转过脸来。直到这时候我才发现,无论性别,他们居然长着一模一样的脸!我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瞪视我了,——身为异类,我已经被他们发现。这一双双瞪向我的眼睛越来越大,大过了眼眶,一直大到了脸部之外,大得整张脸除了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我拼尽全身力气尖叫起来:停车!快停车!车并没有停下来,我身后的车门却打开了。我看着车门外飞速掠过的柏油路面,再回头看看满车恶狠狠瞪视我的眼睛,跳吧,只能跳!
赶在跳车身亡之前,我及时惊醒过来。
有些噩梦在醒来后会惹人暗自发笑。但是这一个不。
就好像总有一天,它会真的在现实中出现。
那个女孩下车了。自始至终,我隐藏在众人身后,她没有看我一眼。
一棵树
去年春天我看见了这棵树。虽然它一直都在。但“在”是另外一回事,——有些事物可能永远不被我们看见。
众所周知,去年春天是个奇怪的春天。直到五月,辽河广场上空还飘了一阵雪。我用一只手紧紧抱住自己的肩膀,另一只手咬牙切齿地抓着一把伞,顶住大风去吃午饭。我发现我的手太小,连自己也抱不过来。这些可怕的经验打击了我的生物钟,让我怀疑自己患上了轻度抑郁症。六月将近的时候,我在一场小雨中走下公交车,无意中向右侧扭了扭头。
我一下子看见了这棵树。
它的枝干已经被一夜春雨浸透,像穿了一身让人伤心的湿衣服。但那些还微微带着一点鹅黄的嫩绿色叶片在阴灰的天空下异常娇艳,让我的喉咙仿佛被什么东西突然噎住。那天,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段话:
“在细雨刷新过的大街上,我被街对面一棵高高的大杨树迷得迈不开双腿。它可真美。在雨中,这些新生的叶子的颜色多么让人惊羡,让人从沉重的胸腔里面扑闪出一颗爱慕的心。现在我回过头来,再看一眼它苍褐的枝干,它柔软湿亮的无数枚叶片。它让人哽咽,像一个人面对疾掠而去的无数个春天。”
一整个春天我都在看着它。事实上,我就这样对着它看了一整年。我发现它的节气比它周围的那几棵大杨树——说不定它们还是亲戚呢——要晚上半个月,别的杨树都已经入夏了,它还慢吞吞地穿着春天的衣服。但是到了秋天,它的叶子最早落了下来。它落光叶子的模样还是好看,当别的树还竭尽全力紧紧抓牢最后几枚瑟缩的叶子,它心无挂碍的姿态显得又酷又帅。但是我开始疑心,在对一棵树的审美上,我的主观意识大过了客观——这棵晚熟又早衰的大杨树,无论我是否承认,它真的有点像我。哦不,它更像我的爱人,长了一张越看越让人沉陷的脸。
“这是二月的最后一天,气温骤降,北风劲吹。但是我的树,它最小的枝丫也一动不动。冬日上午的太阳卡在它光秃秃的枝条中间,像一只发出微弱银光的球。旁边是红色的俄式尖顶。”
“这棵树,它与别的树可能并没有什么不同。像旋转餐桌上金色的莲花瓣,这一瓣和那一瓣,几乎肉眼难以分辨。但是你偏偏爱上了这一瓣,它就在那里,慢慢地从你眼前转过去,直到在你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不见。”
对一棵树的关注和想念花掉了我许多时间,让我在某些重要的时刻也会忽然走神,冷落了盛开在眼前的佳肴美馔。这是我以前从未想过的事情:一旦对某事某物萌生关注,它就开始凭空制造出无数悬念。但是问题在于,它真的就在那里,我再也不可能对它视而不见。当014路公交车拖着若有若无的尾气从我身边驶离,我和它同时暴露在彼此的视野之中。或者我看到的只是它的侧影,而它位于我的视线中央;接下来它慢慢转到我的右侧,而我在它的微微俯视下继续滑行。最后我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仍忍不住向着它的方向频频回首。短暂的舞蹈场面接近尾声,我开始想为什么它这样高大,却从未让我卑微于自身的渺小——我确信在这样的相遇中穿插有神迹的闪耀。隔着一条车流澎湃的大街,我和它遥遥相望。这样的时刻其实暗藏惊险:十字路口交通繁忙,在神思恍惚的情境下,我完全有可能与某辆飞速驶过的汽车狭路相撞,我柔软的身体甚至来不及发出折断的声响。
但是有一次我还是穿过马路,来到它的树干旁边,从人行道上捡起一只它刚刚落下来的毛毛狗。我想这是它开败的花,暗红的颜色略显敝旧。这是今年春天发生的事情。就在我仰着头对它新生的嫩叶发呆的时候,经过我身边的一个女人“扑哧”笑出了声。但我到底有了新发现。那是一截断枝,它已经干枯,茬口异常尖利,像隐藏在时光中的一小段疼痛阴影。我猜想那是一场什么样的风,在我认识它之前还是之后——它绝口不言的众多秘密中的一个——它的生命并非我想象的那样平和安宁。
有的时候我会提前一站下车,斜斜穿过小半个辽河广场,去看那些姓名未知的绿化灌木。在前一个漫长的冬天它们死掉了。下班的路上我穿过广场的另一侧,那儿有一小排又瘦又高的钻天杨,一组非常有风骨的诗人或艺术家群像。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我的杨——为了便于称呼,我替它草拟了一个名字:VV·杨。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坏,但不知它自己怎样想。它看起来始终这样安稳、优雅、丰沛、健康,它符合我对完美的苛刻定义,它的一枝一叶都仿佛沿着我内心的画卷生长。
唯一遗憾的是,我无法看到它的背影。它的背后紧挨着高中校园的铁栏杆,隔着栏杆,是那幢美丽的俄罗斯建筑——这个城市最古老的见证者之一。也许,这幢建筑出现的时候,它就在这里,它的年轮里深藏着比大海还深的秘密。在我出生之前许多事情已经发生。谁知道呢?也许我一厢情愿的理解是错的——它其实始终背对着我。它更喜欢这美丽的红屋顶,这古老安静的校园,而内心奔涌的甜美回忆足够它安享一生。
珍珠塔尖
车过楞严禅寺的时候,我刚好从手中的画册上抬起眼。我看见了午后晴空下庄严的楞严塔,忽然明白,为什么摄影——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给人类带来无限惊喜的摄影——永远替代不了绘画。无论未来的科技可以制造出多么惊艳的色彩、光影、层次……它仍然逃脱不了忠实于原物的呆板写生。而用什么样的文字才能描绘出一尊佛塔在瞬息之间的万千种变化,——它宛若一串珍珠垒叠起来的塔尖,它的黑白色调无限匹配于作为背景的蓝灰色晴空……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为自己不是一位画家感到深深的遗憾。
我奇怪为什么没有一位本地画家将我此时看到的景色复活到画纸之上。是这个景物太熟稔了吗?熟稔到滥俗——已经有那么多摄影家从各个角度把它摄进了镜头,配以春花、夏柳、秋月、冬雪;配以暮鼓、晨钟,甚至配以天空中酷似双龙抢珠的祥云背景……它们随时出现在任意一页有关这个城市的宣传画面上,几乎令人熟视无睹。但是——就是此刻——我看见了一座与我往昔所见的完全不一样的塔。
一座没有历史、传说、人文意义、宗教文化,以及诸如此类的任何附加说明的塔。它本身就是宗教。与艺术一样,它只尊崇它自身的美。
没有云彩,天空也不是很蓝。“是高处的风把云彩摊匀了,像一床半透明的花瓣。”夏加尔一定会这样说的。
它理应诞生一幅得以永生的油画。——就像维台普斯克小镇诞生夏加尔一样。这个城市的很多地方也像悠远的维台普斯克小镇,它倾斜的、随意流淌的街道,它藏在深巷里的敝旧但是亲切的老房子,它淡绿色的雾一样溶化在远景里的早春的树林,还有它阴郁的、漫长的冬天,木质窗棂上未及融化的积雪。我在夏加尔的画中看到了我正在消失的世界。
我还看见了窗玻璃上一道原因不明的裂纹——它切割了窗外简陋的栅栏和一株细瘦的花木。我相信它是一棵木槿。在春天里它长出星星一样的绿叶,这儿那儿地开出花蕊金黄的紫色花朵。城市严谨的铝材窗怎么可能有裂纹呢?所以它们只属于小镇,属于童年的某一场梦境。
我生来就不是一个对色彩有着高度敏感的人。或者说,我不是一个长于视觉记忆的人。即使是在视力无敌的孩童时期,也需要非常强烈的对比色,才能在我的大脑中留下鲜明印记。但是近几年,由于朋友们的邀约,我开始频繁出入各种书画展、摄影展、民俗展、文物展、空间艺术展……我相信我有幸看到了近年来这个城市里诞生的每一件艺术作品。其中的一次画展上,我喜爱的一幅油画被收藏家看中,当场以二十万元人民币拍板成交,让我心情复杂难言。也就在这一天,朋友拉着我在另一幅巨幅油画前合影留念。它占据了展厅的一整面墙壁。由于图像过分逼真,直到画展结束后,我才意识到它是一幅画,而非电脑喷绘的印刷品。画面上是位于市中心繁华区域的电子商城北门入口,场景纷繁,包括暂停在斑马线前等候绿灯的小汽车、电子商务广告牌、倚靠在路旁灯柱上的自行车、穿橘黄色工作服的保洁员……每一个细部都活灵活现。我猜测创作者试图借此向公众展示他近乎完美的绘画技艺,——画幅巨大,任意一个微小的疏忽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瑕疵。朋友介绍说,这位画家开了一家私人画院和一个绘画辅导班,收了很多学生,学校地点就在我的单位附近……在他的提示下,我很快回忆起那个高雅的店铺门面。我暗自庆幸,因为我的孩子从未表现出任何绘画方面的天分,我才没有萌生出培养未来著名画家的虚荣心,花费两代人的大量心血和时间,去完成一幅幅日常生活无比精确的复制品。
是的,我怀疑这样的所谓画作的意义。虽然据说达·芬奇的绘画生涯是从无数枚鸡蛋开始。而这样的故事从小就在教育我们,必须经历过无数次重复,才能把某事做好,把画面经营得立体逼真。但是逼真是否就意味着对原物的诚实复制?或者艺术仅仅建设于技术本身?离开了创造和想象力,艺术仍然可以成为艺术?那么当一个人熟谙文字和语法,他是否就足以自封为作家?
我不知道,是早年所受的教育对我构成了错误的指引,还是我个人缺乏颖悟的天分。这样直到我邂逅夏加尔,我感到一阵慌乱,——怎么回事?这是大师的绘画还是天才孩童的涂鸦?我需要克服的,是画家的幼稚还是我自身的幼稚?
——幼稚,或者说,是人到中年以后愈发显得可笑的单纯,它们始终是我试图从自己的性情中删除的部分。奇怪的是,眼下我终于明白,恰恰是它们,让我懂得并爱上了夏加尔。
二〇一一年元旦我在大连。确切地说,我在大连的书店中寻找夏加尔。我一直相信大连是一座与艺术接近的城市。然而还是没有。我看到了梵·高、马蒂斯、莫奈和雷诺阿。但他们都不是我想要的。也有陈逸飞。陈逸飞的画集最是厚重精美,古雅端庄的音乐美人看着也让人心醉。只剩下最后的一本,被无数人翻得几乎卷了边。而且,这样厚重华美的画风,似乎也不适宜只在闲暇时随手翻看。
只有一本夏加尔的小册子。我把它带在身边。这是我深爱的夏加尔,他在绘画时长出了七根手指。他在路上遇见那么多有趣的人,——他们都会飞。
露天舞
天气晴好的上午,辽滨公园的露天舞池里,下饺子一样下满了人。满车的乘客都伸长了脖子,纷纷扭头注目。只有坐在我旁边的老先生不。我注意地看他一眼。他神情严肃,目视前方,表示对窗外的景致不屑一顾。
我笑了。
我不会跳舞。我的朋友中有擅长此道的,他带着我跳,朋友们围坐在四周的沙发上鼓掌叫好。但如果他不在场,我就只会跟着音乐瞎晃悠。
尽管缺乏天赋,但并不影响我迷恋舞蹈。我是说,我热衷于欣赏专业舞蹈表演。不是谁都能幸运地拥有适合舞蹈的肌肉和骨头。这是一门最原始的艺术,需要有超越庸常生活之上的渴望和激情。因此我尤其热爱肚皮舞,尽管它很容易被某些人指为低俗和色情。每个时代都会诞生那么一些心怀异想的女人,她们带着无数个前世的祈求和梦想,渴望用肢体倾诉和歌唱。这是生命的独舞。侥幸地逃脱开专业舞蹈教练的高雅编排,它最精粹华美的部分才得以世代传承。
我看过骨感的俄罗斯美人Natalia的肚皮舞视频,也有幸欣赏了超级明星Ansuya性感狂野的绝世舞姿,甚至还在音像店里找到了双胞胎姊妹花Veena和Neena的教学光盘。我觉得,号称“中国肚皮舞皇后”的温可馨距离Natalia和Ansuya的水准还差得远。毕竟,中国人自幼生长于拘谨国度,某些幅度太大的动作做起来有点困难。
在我的印象里,肚皮舞是适合在露天里跳的。这古老的中东舞蹈,它诞生于世,只是为了向上天祈祷繁衍和生殖。舞者的赤足笃定地踏在大地之上,像希腊神话里的安泰俄斯,来自大地母神的力量让他得以生生不息。
但是在苍茫的天地之间,一个人的舞蹈多么孤单。
还是群舞让人感到妥帖和安全。即使是在无遮无拦的露天地里,人多势众,做什么都觉得理所当然。
可是我又有点不太能接受眼下这个事实——优雅的交谊舞是怎么演变成大众品牌的健身舞的呢,像东北的传统大秧歌一样,铿铿锵锵地踏上熙攘的闹市街头?
有一次是在外省。晚饭过后,我步出宾馆去买水果。街边的小区广场上有一群人正在跳舞,旁观的人则自觉围成一个圆弧。我粗略目测了一下,围观的人和圈中正在跳舞的人数几乎是一样多。这个场景太熟悉了,虽然家乡远在千里之外,我还是恍惚生出了回到自家门口的感觉。我就在这样的感觉中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心头漫过异乡客惊喜交集的散淡温暖。很快我就注意到舞池中央的一对老人,并马上意识到,他们很可能正是这场舞蹈的中心。老先生鬓发已经斑白,腰身笔直,气质儒雅;他的舞伴看起来比他年轻一点。他们配合默契,举手投足彬彬有礼又旁若无人。我想,我的老年生活会不会也纳入这样的场景——但是以我眼下根深蒂固的孤僻秉性,这样的设想未免过分遥远。我的脸上一定在不觉中漾出了迷离的笑容,一曲既终,我仍站在原地未动。第二支舞曲紧接着响起来了,一位男士忽然穿过人群走到我面前,在我反应过来之前,他已经微微躬下腰,向我做出邀请的手势。我吓了一跳。我?怎么会是我呢?我是个全然无关的旁观者啊!我赶紧扔下一句“我不会跳啊”就落荒而逃。走出很远,想起这异乡的狼狈遭遇,忍不住哈哈大笑。
是的,我已经开始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了。每天我坐在公交车上,看到与我身材仿佛的老太太,我都会忍不住向她多看几眼。我猜测着她的面目和生活,与我不远处的未来到底有几分相像。有一次,我看见了一个面庞清瘦的老人,与同龄人相比,她的身体显然太轻灵了,这轻灵的体态让她显得有点儿异样。她的发丝已呈灰白,但皮肤仍然细腻白皙,眉眼酷似我去世多年的外祖母。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呢子大衣,黑色的裤子和皮鞋,鞋擦得很干净,样式是说不清哪年生产的那一种。我注意到她的手,带着无法遮掩的清苦生活的痕迹。我清楚地记得,她是在辽滨公园站点上的车,但是我无法把她与正沸沸扬扬地煮着一大锅饺子的露天舞池联系在一起。她这样安静、严谨,带着过分自尊的人容易受伤的清冷神色。我的心没来由地一阵隐隐作痛。
就在这一瞬间,我忽然记起,我母亲在我现在的这个年龄,曾经有一段时间苦练过交谊舞。她拉着我父亲在客厅里反复练习舞步,但我父亲生性喜静不喜动,勉为其难的态度让她恼怒。我母亲生性要强,连舞技也不甘落于人后,于是常常把我吴叔两口子找来陪练。但我吴叔的表现也差强人意,舞曲一响,他的下巴颏就渐渐抬了起来,越抬越高,一直抬到了九霄云外。他一个人陶醉在那里,完全不记得身边还有一个舞伴。由于我吴叔身高一米八五,我吴婶和我妈都只好把白眼送给了他的喉结。那时候我家日日笙歌,那一整个美妙的时代就这样飞快地一闪而过。
森林,也许吧
一路打听着向它走去的时候,我觉得世界恍如梦中。春天的景致如此美妙,叫不出名字的树木把它的枝条铺展在我的头顶。春风骀荡,唉,我只是想说春风骀荡,我不管这个词的后面牵连着多少种因由。我看见春风透明的绸带轻轻缠绕着路旁的花瓣,花瓣粉白,而未绽开的花蕾色泽嫣红。这时候应该有几只蝴蝶翩翩出场,奇怪的是它们不见踪影。
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说的吧——仿佛梦境,仿佛倒映?
但是它肯定就在那儿,我在走。而它在等。
不记得是在哪一年的哪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每天乘坐的014路公交车站牌上,多出了一个奇怪的站名。我闭了闭眼睛,再睁开。“森林——公园”,“森——林公——园”,好吧,我承认还是前者的正确概率比较大。可是,这个城市的边缘真的存在着一座森林吗?
一座森林从无到有需要多少年?五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就在十几二十年前,这个小小的城市还坐落在一大片湿地中间。许多新楼正是从原来只生长芦苇和菖蒲的地方生长起来,鲁莽的车笛代替了水鸟羞涩的鸣叫。上初二的那一年夏天,我和好友莲香在苇荡旁边的小路上遇到了一只长着一双长腿的水鸟,它被我们这两个突兀现身的庞然大物吓呆了,竟然忘记了逃跑。我把它带回家,每天和弟弟轮流到水塘里捞小鱼小虾喂给它吃。可它后来还是死掉了。难道,在年少时代的一次次骑车游荡中,我的视线被这些连绵无尽的苇荡所遮挡,竟至于不小心漏掉了一座森林?
无数次,我遥想着这片宛若自天而降的森林。它散发着什么样的气味?树与树之间是不是飘荡着梦境一样的茑萝?湿润的树皮上一定长满了苔藓,而枯叶下面总有调皮的胖蘑菇探出脸来。我曾经跑去我朋友家乡的大山里挖野菜,那里的柞树林铺天盖地,绿眼睛的蛇躲在某个洞穴里窥视我,而更深处的丛林里奔跑着野兔和山鸡。但是我认为它仍然算不上一座森林——森林,这个古老的词语,它应该吐纳着现代文明还没有梳理过的亘古苍茫的气味。而作为014路公交车的终点站,我与一座森林的距离只不过半个小时。——如果哪一天我不小心在车上睡着了,一睁眼,发现自己正停留在一片森林的边缘。就像有些人曾经在他们的生活中遭遇的那样。可是,无论怎样疲倦,我从未在公交车上打过瞌睡。我疑心,正是因为多年来近乎顽固的自律和严谨,使得我的生活中始终缺乏惊喜和意外。
是什么阻挡了我奔向一座森林的脚步?我任由它飘浮在天边,像一个巨大的谜底埋伏在我的生活中间。
我不知道那一天是什么促使我上错了车。而且,直到003路车驶近终点,我才蓦然醒悟过来。我望着窗外陌生的街景,一时不知今夕何夕。像这类我以为永远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的轻喜剧,居然也会在我的生活中仓促上演。实际上,003路公交车与014路只在短短的区域内有一小段重合,之后它们就各奔东西,南辕北辙。从此,每次上车之前,我都要下意识地看一眼车门旁边列出的主要站点,看到“森林公园”,我才放心地拿出我的IC卡。对我来说,这四个字代表了提醒和暗示:我必须知道我要去的是这里,而不是那里。
现在,它一点点从城市的地平线上凸显出来,顺着路人手指的方向,我看见了一片迷蒙的苍黄。我停下来,远远地望着它。
——你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不是吗?
——也许吧。
——所以你一再拖延见到它的时间。所以你下意识地选择了步行而来。因为你害怕失望。你一直害怕这个世界会让你失望。
——也许吧。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已经能够承担所有的失望。
这是一群树龄不会超过五年的小白杨。这是一片幼年的森林。但是我怀疑它们是否真的能够长成大树,或者说,我怀疑当初种下它们的人是否真的想要种出一片森林——这些树与树之间的距离,不会超过二米。虽然我不知道一棵大树需要多少营养,但即使是树形非常笔挺的白杨,在这样逼仄的空间里显然也无法舒展开手脚。在这个干燥的春天,林间坚硬的泥土上还罕见青草的踪迹,但是在林木的纵深处,我吃惊地发现了一小片野花。花朵是紫色的,有柔弱纤细的花茎。它们曾经就是这样,疏疏落落地开放在我童年的田野上。可是眼下,我已经叫不出它们的名字了,像一些偶然出现在我生命里的人,轻易地被我遗忘。
接下来我看见了蝴蝶。它们在小小的紫花间穿梭嬉戏。它们在这里。
还有湖泊。湖水呈现幽深的碧绿。钓到鱼了吗?我问一个手执钓竿的人。他戴着一顶红色的旅游帽,看上去比别的钓鱼者温和可亲。
以前钓到过。
多大的呢?
多大的都有。
噢。
我看看脚下的湖水,几只水黾在上面快乐地跑来跑去,它们长长的细脚在水面上划出一圈圈细小的波纹。小时候,有人告诉我,大大小小的水纹下面藏着大大小小的鱼。我又看看那些全副武装设备精良的钓鱼客,他们围绕湖的椭圆形周长近乎完美地均匀排列。我猜测着他们的身份。看得出,他们也在猜测我。我是谁?我跑来这里做什么?我不遛鸟,不钓鱼,不挖野菜,也不像那些闲庭信步的附近居民。
他们在自己的日常中活着。而我跑到了日常的外面。作为一个冒失的闯入者,我显得这样一无所知,又居心叵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