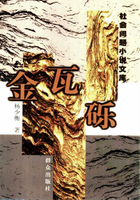“是吗?这么巧就遇到了老爷。”
“是,我去的时候老爷刚回来,看起来累的很。”红豆声音越来越小,“可老爷一听小姐病了,院门都没进去就又出去了,喊着要备轿子去找大夫。出去不大会儿就回来了,原是半路上遇到了刚给人看完病的城东陈大夫,欢欢喜喜迎了进去,这不,小姐就好了。小姐真是有福的人,能得老爷这样爱护。”
林姨娘露出了笑意,“你嘴倒巧。不过你擅作主张,又使得老爷累病了,可不是小罪。我知道你立了小功,救了凌姐儿一命。可你也太不够稳重了,我对你可不放心,那就贬为三等丫鬟罢!”
红豆脸色苍白,声音哽咽道:“姨娘,你不能这样,我是小姐的丫鬟。小姐,小姐她离不开我的。求您了,就算是二等丫鬟也行,只要别是粗使丫头。”
“你倒高看自己,还离不你?我正准备向夫人求个丫鬟呢!比外面挑得毛躁丫鬟好得多。所以你放心,凌姐儿不缺人照顾。”
红豆抹了把眼泪,“您倒很放心白夫人,只怕她末必好心。那天二小姐病了,她为什么凭空送那么贵重的项圈。再说她也有个女儿,就算对凌小姐再好,也终是为自己女儿考虑的。”
林姨娘冷笑一声,“这个不必说,天下有不为自己儿女着想地母亲吗?凌姐儿病的那天,夫人的好我都看在眼里,你不要挑拔离间。再说我在后宅可不求真心,只望人不害我,我不害人。”
“姨娘,我知道些事,我通报小姐病了的那天听到了。那天你走后,白夫人没注意到我。和小夭儿说着什么。大致是说二小姐不大好了,老爷定会迁怒,先准备好什么,压箱地的项圈贵重,白老爷定会愧疚,自己也能避了祸。我不懂意思,但一定是夫人心思不纯。”
林姨娘听着红豆乱七八糟的话,只是冷笑。“你胡言乱语什么?我不想和你多说了,你快出去罢!去小姐院里好好干活。快出去。”
红豆很不可思议,本想说些自己知道的事,能让林姨娘看到自己用处。没想到她这么不开窍,竟听不懂。
她想再说,可林姨娘身边的大丫鬟姣娥来了,她心中带着千万分恨意被姣娥拉了出去。姣娥又赶来给林姨娘捶腿。
“姨娘,那小蹄子话还真多,一心想让您对付白夫人,可得小心了。”
林姨娘伸了个懒腰,只嗯了一声,问道:“姣娥,你觉得她在胡说?”
姣娥想了想,“那项圈我知道来历,说出来怕人。是夫人要送给大小姐作嫁妆的,本来是夫人家里传女不传男的避邪宝物。可一看二小姐重病,就送了去。白夫人确实好心的太过了。”
林姨娘眯着眼,似乎睡着了。长久才接了话。“那天是大年初一,老爷正忙着宴请宾客。出了凌姐的事,白夫人肯定又怕老爷发怒凌姐儿大过年生了晦气,又怕老爷责怪自己没及时通报这事,没管理好后院。她定很为难,不敢做主,又不能不作为。最好下了血本,让老爷心生愧疚,不能发作。”1000字左右
?? “很有可能,那要不要还回去。”
“算了,不要提了,我们就当不知道这事。对了,小厨房的野鸡崽子汤炖好了吗?”
“煨得透透的,和山药粥一起都装提盒里了,我现在就拿过来。”姣娥说着就去了东耳房。
只一会儿,林姨娘就接过她递来的红漆小提盒,心情颇好。她想起红豆的话还是很耐听的,老爷对凌姐儿好,自己也有脸不是。
“姣娥,你退下吧!我一个人去看老爷,老爷的风寒也不知道好了没。”
“姨娘,太太去看老爷了,我们再去……”
林姨娘神情悻悻,突然没了兴致去送温暖,“拿去送给小姐。一场大病下来,凌姐儿的痴症竟也好了,正该大补呢。对了,记得和凌姐儿说项圈别乱扔,贵重的很。”
姣娥接过就去了。
白凌练趴在窗户上,眼往外瞪着。雪还没化,外面的景物都被层白布包住似的,实在没什么看头。远远的只能望到白夫人院子,在十几棵梅花树中半遮半掩。
银耳第十次把白凌练拖了下来,用被子裹紧实放在榻上,“好小姐,你吹不得风,躺好了养几天,想怎么玩怎么玩,现在别乱动。”
“知道了,银耳姐姐。我姐姐怎么不来看我。”
“小姐,柔小姐昨天不是来了吗?”
“哼!那我娘去哪了。红豆又去哪了。”
“姨娘去看望老爷了。你不知道,请来大夫的那一天,老爷也病倒了。红豆嘛。”银耳迟疑了会儿,“贬为了粗使丫鬟,现在小姐只我一个贴身丫鬟了。若是觉得不方便,梗米和糯米您看好谁就升了罢!”
白凌练应了声,只是脸上实在不高兴。
“小姐,把姨娘刚送的野鸡汤喝了罢!这可是姨娘的一番心意。”
炕桌上放着打开地提盒,升起袅袅轻烟,屋里都是诱人地味道。
“你喝了罢!我想睡觉了。”白凌练用被子蒙上头,表示拒绝谈话。
白柔练来时就看见白凌练使小性子,心里好笑,“凌妹儿,这是做什么?觉得自己丑得不能见人?”
“呀!大姐,你来了,我一个人怪闷的。”
白凌练从被窝中跳了出来,白柔练赶忙把她塞进去,“阿弥陀佛!快别闹了,你病要加重了,我可承不住爹爹的责骂。”
“都怪那大夫,说是小病,十来天都不好,总要我躺这被窝里。”
白柔练笑不出来了,找了不少大夫都说是小病,可总是不见好。瞧着小脸黄的。不过发烧能把脑子烧晴明的实在少见。“凌妹儿,你再不好好养着,病更好得慢了。”
白凌练往被子里拱了拱,“哼!我很快就好了。”
白柔练打量了一圈她的屋子,“凌妹儿,我真是羡慕你,去年就分了个院子。我还得和母亲挤在一起,怕是过几年才有独院。”
“有什么好的,父亲是为着我痴病,怕麻烦了夫人。不说了,大姐带什么好玩的来了,怪丑的。”
白柔练手里端着一个黑漆小匣子,看着就阴沉沉的不讨喜。
“这是熙弟的平安镜,熙弟不是天生不足嘛。在达观诗求的镜子,开了光了。就往屋里那么一放,熙弟就养了起来,当时可眼看着就……”白柔练及时住了嘴,“现在送你这个病秧子了。”
白凌练接过打开,哎呀一声,“好漂亮。”里面是小小的菱花镜,嵌金镶银的,煞是美丽。“嘿!镜子,你以后就是我的了。”
“你发白日梦吧!一年后就要还的。这个可是有借期的。”
“什么,好个小气的和尚,是不是爹爹香油钱没给足。连个镜子也不送。”
“这是人家的镇寺之宝,向来只借不给。好了,放在你枕头底下,能避邪,睡个好觉。”
“我这几天还真是睡不好,怎么都不踏实。谢谢大姐。”白凌练心里喜欢,拿着怎么都瞧不够。铜镜里照出了小小的人儿,额上小小的胎记,似一朵粉绒花绽开在雪地间。白凌练竟看呆了。
白柔练看她的傻样,捂着嘴直笑。悄悄得走了,她也没发现。
白凌练看着镜子,心砰砰的跳。她看到了什么?血,好多的血,像莲花花瓣一样炸开。炸到她眼前,并越来越近。她觉得自己要进去了。一缕缕地,如烟如雾地进去,进到那一片红中去。
白凌练身体一抖,回过了神。她惊出一身冷汗,心里很怕,忙把镜子放在枕头下。等情绪稳定后又忍不住拿出看。里面并不见刚才情形,只是一面很普通的镜子,黄澄澄的照出她模样。
白凌练努力的瞪着,妄图瞪出些猫腻,看了会只发困,什么也没见着。她打了个哈欠,想着睡会儿去找熙弟问问。原就是他的镜子。
谁知一觉醒来是第二天早晨,白凌练病情倒加重了,她觉得身体很累很累,暗自猜想是镜子的原因。唤来银耳把镜子收回柜子里。银耳过来见白凌练脸色不好,摸了摸她额头,暗道坏了,让白凌练躺下别起来,急急去禀告了白老爷。
白凌练只能把玩着镜子,又放回枕头底下。她慢慢地睡下,再醒来时头生疼,浑身骨头都在发软。眼前所有景色都像蒙了层灰,隔了层膜。她正想再睡,就听到林姨娘在训着丫鬟,过了一会儿又听到很杂乱地说话声。
白凌强撑着睁眼去看。隔扇门没关,恰好能望见外间情景。林姨娘正坐明间炕上,指着银耳说:“银耳,我不罚你,起来吧!灌了一剂药,我看凌姐儿好多了。”
银耳在地上跪着,“姨娘,我不敢起来,这全是我的错。我没看好小姐,几天内病了两次。我愿意一直跪着,等小姐病好了再起来。”
林姨娘叹了口气,“你总是老好人。不提了,我来不是要怪罪你,是要和你说一声,凌姐儿俩个贴身丫鬟才方便,你一个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