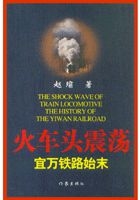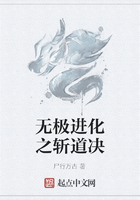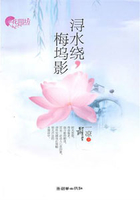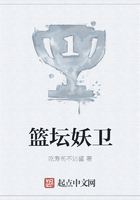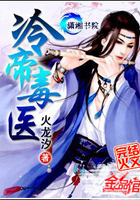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十二月,骑马打天下的朱元璋东征西讨,苦战十六年,先后灭了汉王陈友谅、吴王张士诚,收降方国珍、生俘陈友定,并尽收其地域,已经拥有了江南半壁江山。在手下文臣武将们的拥戴下,于应天府称帝。翌年正月,乙亥,祭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国号曰明,建年号洪武,改元至正二十八年为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立马氏秀英为皇后,立长子朱标为皇太子。封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并改元制定官位以左为大,右次之。开国大典盛况空前,朱元璋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史称明太祖高皇帝。
早在起义之初的滁州,朱元璋即收用了李善长等有文化的将领。从此他对有学问的儒学之士十分崇敬,每占一城都注重纳贤求儒。在太平录用了大儒李习、陶安、汪广洋。在南京设礼贤馆,先后征请到宋濂、叶仪、叶琛、刘基(字伯温)、朱昇、章溢、许元、王天赐、王炜等一大批名儒。受这些名士大儒们的影响,朱元璋深谙武打天下、文治邦国之理。如今天下一统,亟需大量文臣来治理国家。因此,朱元璋在陆续封诸子为王和大封功臣之后,广录天下官吏,遍设管理农桑、学校的机构,并诏示天下建立社学,以培养治国之材。为了解决眼下文职官员奇缺的问题,朱元璋於洪武八年(乙卯,公元1375年)诏示天下曰:“金秋京闱”。意思就是通告全国,今年秋季在京城首开科考,考中者录为举人。
消息一传开,全国各地进京应考的儒生文人齐聚应天府,城中饭店茶肆盈庭,旅店客桟爆满。许多有钱的人家怕届时租不到房子,竟提前一两个月就把客房租了下来。真是让京城的商人们赚了个桶满盆溢,多挣了不少钱。就连京郊的民宅里,也住满了经济拮据的考生。
俗话说:“名师手下出高徒”。在太平名儒梁贞、潘庭坚两位府学教授的悉心教导下,陈迪潜心苦读十几年,如今已是经纶满腹、胸怀天下。好不容易盼到了这次首开京闱,岂能轻易放过。
他和几个同窗学友提前好几天就来到应天府,见繁华之地的客桟已满,便在离西城门不远的一个僻静的小客店里安了身。
虽然有点冷清,却也图个清净,便于做些考试前的准备。待三场严格的考试结束,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阅卷、批卷、审卷、遴选、登记、发榜等程序,一切都在有序地进行着。
在等待发榜的日子里,经历了一连几个彻夜难眠煎熬的考生们,有的终日蒙头大睡,饭也顾不上吃,水也顾不上喝;有的则是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狂吃豪饮,恨不能立马将伤失的元气吃补回来。陈迪则想到要利用这几天闲暇的时间,去拜访马皇后和看望太子朱标。好不容易找到原来的吴王府,却发现高宅大院早已换了主人。
当他按照行人的指点走到新建的守卫森严的皇宫门前,还未及问上几句话,就被那些凶神恶煞般的卫士们驱赶到了远处。
遥看那巍峨雄伟的皇宫和那些全副武装在皇城外不断巡逻的皇家卫队,陈迪总算明白了,此时深居宫墙内的朱元璋已今非昔比,普通百姓想见他一面比登天都难。在他的脑海里曾不断涌现的小朱标在太平城外那远去的身影,被眼前那一堵红墙绿瓦无情地阻挡着,渐渐地模糊起来。当他失望地转身往回走的那一刻,心中忽然涌起一种莫明奇妙的感觉,自己也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儿。归去的路与来时的路一样的远,可不知为什么自己的脚步已不像来时那样轻盈,也记不清楚自己到底走了多久才回到住处的,连衣服也没脱,就浑身无力地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终于等到了发榜的这一天。已连续两天阴雨缠绵的天空,突然放了晴,骄阳似火,天蓝云白。那些在焦虑和期待中苦熬时日的考生们,心情也像天空一样开朗起来。一个个活蹦乱跳,三五成群地涌向国子监大门外,在那贴着皇榜的红墙下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个水泄不通。陈迪也与几个同窗学友来到皇榜前面,见人山人海的一时半会儿也挤不进去,就静静地在一旁等待。自己虽然胸有成竹,但心中也难免有一些忐忑不安。
只见考生们这一拨挤出来,那一批挤进去,真应了一句唱词:“月儿弯弯照九州,有人欢喜有人愁”,那些中举的考生乐的直蹦高,嘴里高喊着:“我中了,我中了!”而那些落榜的考生们则垂头丧气,一声不吭地悄然离去。看着这悲喜参杂的场景,陈迪的自信度在减少,而心中的忐忑在增加。见皇榜前面的人群已经不那么拥挤了,赶忙从人缝中钻到榜前,从前向后,从上到下地仔细搜寻着,当他终于在榜上看见了自己的名字,而且确认了是在前十名之内时,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他长舒了一口气,心中颇感欣慰,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如今终于有了期盼的结果。
他没有在皇榜前多呆,看完了榜上的有关规定,就急忙向吏部衙门快步走去。在吏部文选司签名报到结束时,他听衙门主事说:“签到后,可回家等候录用通知。”便到客桟收拾行李,当天就急匆匆地往家里赶,想把这个好消息早一点告诉家里人。
其实,早已有人把陈迪进京赶考中了举人的喜讯通报给陈家了。待陈迪归来,亲朋好友都来恭喜道贺,计氏也早已准备好了喜庆酒宴,大家边吃边聊,接连热闹了两三天。不久,吏部的行文下达到了太平府,任命陈迪为本府府学训导。接到通知,陈迪便去府衙报到走马上任了。这时原府学教授梁贞已年迈退休,潘庭坚教授升任府学教谕。陈迪与恩师潘庭坚这对师生共事同一府学之事,成了当时太平府广为传谕的一段佳话。
原来在元朝末期,人分十等,最低的四个等级是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人的地位比娼妓还低一等,所以很少有人愿意读书。当年朱元璋占据太平城,选任教授,首办府学,不仅是为了彰显其尊儒重教之意,也是为了改变世风,劝进后人。现在太平府市民亲眼目睹了陈迪人府学求学,进京城应考,中举人当官的全部经过,望子成龙之心勃然兴起,纷纷送自己的孩子前来求学,竟导致太平府学出现了人满为患的状况。
看到有这么多的青少年求学上进,陈迪心中十分高兴,像当年的恩师一样,处处为人师表,日日精心施教,从来不敢懈怠。
晚上回家,还要抽空教自己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读书,写字,虽然又忙又累,却也乐在其中。
转眼间到了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大明朝建国十周年的华诞和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五十大寿的圣诞,碰巧在同一年庆祝,堪称华夏盛事。全国各省司,府郡纷纷进呈《贺万寿表》,成为当时一种风气。其内容大致是:“赞国朝繁荣昌盛,福祉永固;颂高皇圣德普润,万寿无疆。”
太平府知府大人也不甘落后,知道陈迪不仅人品好,文章也写得好,便亲自拜访陈迪,委托他代表本府写一篇《贺万寿表》。
陈迪答应后不敢怠慢,又深感责任重大,苦思多日方悟出其中要旨,这才大笔一挥一气呵成,陈迪是一个忠于职守,勤于职事,办事非常认真的人。《贺表》写完后,又反复诵读,仔细推敲好几遍,直到自己感到心中有底了,才恭恭正正地抄写一份送到府衙,请知府大人指正。知府大人看过之后连连称妙,竟一字未改,将原稿密封好,派专人呈送京中礼部衙门。
可能朱元璋也是个爱听溢美之词的皇帝吧,他对各地呈报上来的《贺万寿表》非常感兴趣,一篇不落地细心阅览。今天读几篇,明天读几篇,一有空就看,还经常作些比较。这一天,当他读完陈迪写的那篇《贺万寿表》之后,惊喜异常,连连夸赞道:“好文章,写得好,这才深合朕意呀!”立即命人速速核查,此贺表出自何人之手笔。掌事人接到皇帝口谕不敢怠慢,急忙核查登记文号,然后立即回报说:“此篇贺表是太平府举人,现任府学训导陈迪所书。”一听到太平府陈迪这个名字,朱元璋猛然想起了当年太平城门夹道欢迎人群中的那个英俊少年,以及“太子标生于太平陈迪家”的往事,不禁抚须大笑,朗声说道:“此子学业有成矣,堪当重任也。”
第二天早朝散朝后,朱元璋便命中书省拟旨传谕吏部和太平府:“以通经荐之,陛调翰林院任编修之职。”以通经荐之,就是以此人精通经史为理由,由县级以上衙门向上一级衙门推荐重用此人的意思。
陈迪的这次举荐升调,经历了近一年的时间。待吏部正式行文下达到太平府衙,已到了洪武十一年的12月份。知府大人亲自到陈宅报喜,并祝贺陈迪连升三级到京城作官。陈迪闻听调令已下,大喜过望。妻子计氏也乐得合不拢嘴,连忙准备一桌好酒好菜,款待知府大人。亲朋好友们闻讯也纷纷前来祝贺并送贺礼,夫妻二人迎来送往,一连忙了好几天。这时离进京复命的日子已不足旬月,又赶上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陈迪夫妻二人便抓紧处理家中诸事,提前打点进京行装,忙得不亦乐乎。
洪武十二年(已末,公元1379年)春正月,刚刚过完春节,陈迪挑了好日子,就带领全家人赶赴京城复命。太平府距京城不足百里,不到两天就到了应天府,先是找了家客桟,临时安顿好妻子儿女,便到吏部衙司签到,吏部按例准其休七天例假。陈迪抓紧时间收拾房子,置办急需的家具用品。待把家安顿下来,又带着妻儿到京城最繁华的秦淮河,夫子庙游玩了一天,这才正式地到翰林院上任,并写了一份谢恩疏,交翰林大学士转呈皇上。
朱元璋看到陈迪的谢恩疏,知其已到京上任了,这才回后宫把此事的前后经过告诉马皇后。马皇后闻听心中甚喜,很想见陈迪夫妇一面,但又虑及自己不便出宫,便请求朱元璋允许她和太子朱标在坤宁宫接见陈迪夫妇。朱元璋应许了此事并派人告知陈迪。陈迪夫妻二人从未进过皇宫,如今能获此殊荣,倍感惊喜。
到了觐见之日,陈迪夫妇来到皇宫,在大内宦官引领下前往坤宁宫。只见甬道两侧高高的红墙绿瓦,墙内那巍峨的宫殿,花园里的奇花异草,琼楼玉阁,真是目不暇接。进了坤宁宫,更是琳琅满目,漆雕闪亮的红木座椅,玲珑剔透的落地隔墙,轻盈飘逸的绉纱幕帘,还有那一盏盏光线和谐的宫灯,都给人一种庄严神奇的感觉,仿佛进人仙境一般。踏在那松软的红地毯上行进,一点声音也没有。直到分别与皇后、太子行过大礼,皇后开始问话时,二人才敢抬起头来。目视皇后的威仪,聆听皇后的话语,二人真是受宠若惊。后来,马皇后单独与计氏说话,陈迪才有了机会与太子朱标当面交谈。
当得知朱标在两年前即已开始参知朝中政事时,陈迪发现当年的小朱标真得长大成人了,心中顿时增加了几分尊敬之意。
当听到朱标对自己讲述了其在宫中的孤独与烦恼时,陈迪又一次感受到了有如兄弟般的亲情。陈迪从朱标那亲切的话语和诚挚的眼神中领悟到了他们之间渊远流长的情谊,那堵红墙绿瓦的高墙和戒备森严的红漆大门是阻隔不断的。
对于这次觐见,陈迪感激涕零,终生难忘。受多年儒学的熏陶,陈迪是一个守本分,重情义的忠义之人。他牢记马皇后的教诲,决心更加勤于政事,以报圣恩。妻子计氏也主动承担家务,管束子女,让丈夫全身心地安心工作,没有后顾之忧。
当时翰林院受命编撰元史,这是一个十分浩繁的大工程,牵涉其中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可计数。陈迪到任不久,就以翰林编修一职,参与到了这一行列之中。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事无巨细,必亲力为之,一干就是好几年,从来不敢有丝毫懈怠。长年累月,日日夜夜的与文字打交道,是一项十分枯燥无味的工作,常人很难领悟其中的滋味儿。然而陈迪却能以苦为乐,持之以恒,常年跋徙于书山之上,遨游于文海之中。这不单是他忠于职守的品格,更是因为他本人对这段历史的钟爱。
早在太平府还是个少年的陈迪,就对太祖高皇帝起兵渡江骑马打天下的故事很感兴趣。当年他去帅府和军营中,以及与沐英、朱文正、李文忠、何文辉、平安等朱元璋收养的义子们的交谈中,就知道了不少这方面的故事。如今他身为编修,亲自参与编写这段历史,他是怀着对太祖朱元璋尊崇挚爱的深情投身于这项工作的。因此对元朝末期的农民起义,尤其对朱元璋征战大江南北的丰功伟绩他更感兴趣。收集资料,填补缺遗,对每一事件的调查处理他都事必躬亲,不厌其烦。常年在历史尘迹中瀚旋,陈迪耳濡目染,对太祖从军到夺取天下的所有事迹不仅耳熟能详,而且对其成败取舍也有了自己的评价和论断。这些不光对当时成书成史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且对陈迪自己以后的从政从教大有裨益。正是这长达六年的编撰元史的辛勤经历,使得他比任何人对太祖朱元璋的了解都更为深刻。从此时起,陈迪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上,做的每一件事,都能深合圣意。这也是他能在太祖后期脱颖而出,后来居上的原因所在。
再说太子朱标生性温和过于仁慈,令朱元璋忧心重重,生怕千辛万苦打下的大明江山被他人夺走。步人晚年的朱元璋神经敏感,疑虑重重,在他的眼中值得信赖之人愈来愈少。自从宋濂致仕病死于谪戍途中,太子师的位置空虚已久。朱元璋急于找一位既合自己心意,又能胜任太子老师的人,却一直没有找到可选之人。
忽然有一天,朱元璋想到了太平陈迪。他知道陈迪少年时就倜傥潇洒有志操,现在已精通经史,才智过人,再加上朱标自小生于其家,两人从来关系亲睦,不仅太子易于接受,而且此人一向忠义可嘉,又年长太子一十三岁,无论人品、素质、年龄、才智,皆堪当此重任。想到此处,主意已定,遂于洪武十八年(乙丑,公元1385年)二月,晋升陈迪为翰林院侍讲(正四品),人东宫任太子师。
从此,陈迪一面辅佐太子预修大典(即《太祖实录》),一面按规定时间为太子讲授四书五经、《资治通鉴》,阐释安邦之本、治国之道。陈迪一改宋濂的教学之法,在方法上变一教一学为双向研讨交流;在内容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善于把自己修撰元史中掌握的事例用来阐述儒家之道。这样一来,就把枯燥无味的教学变成了研究交流式的讨论,不仅生动活拨,趣味横生,而且涉题广泛,无所不谈。令太子耳目一新,受益匪浅。长而久之,太子朱标待陈迪是亦师、亦兄;陈迪待太子是亦臣、亦友。
洪武二十四年(辛末,公元1391年)八月,太子朱标选陈迪伴随其巡抚陕西。一路之上,陈迪陪着太子边走边考察民情。
这次出行历时三个多月。在返回的途中,朱标偶感风寒,虽经治疗,但因长途跋涉,身心俱疲,体力不支,竟经久不愈。待进京回宫后,病情愈加沉重,已到了卧床不起的程度。陈迪与朱标长子朱允炆一起日夜伺候于床前,谁劝也不肯离去。
太祖朱元璋最疼爱这个长子,从小就想把他培养成一个能够守业的接班人。在这方面朱元璋也的确倾注了全部心血。他不仅为儿子请了最有名的老师宋濂,自己也经常对其言传身教。如今看到这个宝贝儿子病成这般模样,真是又心疼,又着急,请遍了所有的名医为其诊治,无奈的是终不见效。到了翌年四月,竟不治而卒,享年三十七岁。当时已年逾六十五岁高龄的太祖朱元璋,突然痛失了太子朱标,悲怆之情难以言表。一想到自己多年培养之心血,已顿时化为乌有;再看到自己落得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凉结局,真是欲哭无泪,悲痛至极。自觉精神恍惚,心衰体虚,四肢无力,接连数日卧床不起,只好宣旨罢朝。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办完已故太子朱标的丧事,才稍有好转。但随之而来的重新立储一事,又令朱元璋烦恼不已,犹豫不决。连日来,关于此事,廷议之争愈演愈烈。
朝中大臣先是分成两派,从各自利益出发,一派是力谏从皇子中遴选新储,一派是力主立皇长孙朱允炆为皇太孙。而坚持从诸皇子中选立太子的大臣们又出现了分歧,其中一部分提议立皇四子燕王朱棣为太子,而另一部分大臣则提出应按长幼之序立皇次子秦王朱楝为太子。此时支持朱棣的大臣又以朱楝行为不轨为由,力主应由朱棣出任新太子。然而大多数朝臣坚持应遵帝制立嫡长孙,绝不可以越过嫡次子,嫡三子而立庶子燕王。
后来,那些支持皇次子与支持其它皇子的人眼见自己的主张无法实现,又不甘让势力强大的燕王成为太子,便转而站到了主张立皇太孙一派。朝中坚持立皇太孙的呼声越来越强,成为了主流派。开始时太祖朱元璋也有立朱棣为新太子之意,因为在朱标之外诸皇子中他最钟爱四皇子朱棣,总感到他神勇威猛,许多方面都像自己,是一个能像他一样刚猛治国的君王。而皇长孙既年轻,又文弱,让这样的人接皇位朱元璋感到很不放心。所以朱元璋一直犹豫不决,难下决心。然而正如“国不可一日无主”一样国亦不可一日无储君储君不立,派系之争不止,长而久之,必然会动摇国本。一直拖到这一年的九月,朱元璋终于决定立太子朱标之世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这场立储的风波才平息下来。
然而连朱元璋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犹豫令朱棣滋长了想当皇帝的野心,他的决定埋下了一场悲剧的祸根。